中国作家网>> 民族文艺 >> 文学评论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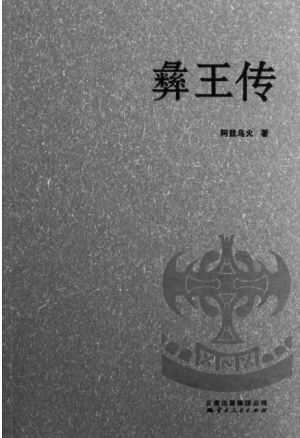 作者:阿兹乌火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作者:阿兹乌火 出版者: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诗言志、诗缘情,一向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主流。到了现代,中国当代诗歌在朦胧诗之后,有了种种新的探索。口语、身体、日常化……这些路向成为重要的诗歌议题,它们总体上显示了当代社会诗意的丧失,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散文时代的到来。诗歌似乎越来越理性化,技术化,琐碎化。
然而,在这些时髦命题的背后却隐藏着一股汹涌的潜流——绝大部分不曾进入主流批评视野的少数民族诗歌依然在保守的面孔下,执着地进行浪漫主义式的抒情。他们或者带着集体狂欢的激情,要为濒临消亡的族群文化留存记忆;或者在想象的幻境中,点燃逝去意象的盛大焰火。来自乌蒙山区的彝族诗人阿兹乌火属于前者,他的汉文名字叫李骞。他是文学教授,属于彝族的文化精英。当他起意为彝族传说中的祖先、王者、英雄、神灵创作一部长诗时,是为了完成心中的情结:既诉说本族群的璀璨往事,歌颂英雄祖先的业绩,又抒发带有共通性的情感。
我们向世人讲述彝王
其实也就是讲述我们自己
这是每一个彝族人神圣的责任
只有这样 即使几万年后
我们的子孙才不会丢失这一段记忆
阿兹乌火在长诗《彝王传》的最后卒章显志,点明自己写作的缘由。这首长诗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横空出世”、“繁殖之神”、“六祖分支”。从内容上看,这首诗是以传说中的彝王阿普笃慕的事迹为线索。然而,恰如阿兹乌火所说:“这首长诗不是以叙事为主,而是一首带有神性色彩的抒情长诗。诗中的彝王只是生命的一种直观体验形式,而非历史中的伟人。应该说,我笔下的彝王更接近彝族民间口头传说中的王者,他是一个无所不能、自由自在的神灵。”
这种抒情与上世纪90年代之后,诗人趋于个体化、肉身化的自我抚摸不同,而是倾向于一个宏观、博大的抽象主体。这是一种“大抒情”,指向的是共同体的同情共感,提倡的是更为广泛的普遍价值——那些在日益平庸、精细、功利、工具理性化时代行将就木的,对于血性、威武、勇猛、豪放、牺牲、苦难、超越的渴望。
少数民族诗人作家的写作,往往带有很强的代言意识,无论自觉或者不自觉,作为一个族群的文化精英,在书写涉及族群历史、文化、社会时,总有一种共同体意识,而很少个人主义式的表述。在现代性冲击中的回归祖灵,可以视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退守性思路。然而,这是站在启蒙式理性规划视角下的审视。如果换个立场,站在彝族的主位,那么这种寻根则具有寻找遗落的价值的意味。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把普遍技术化的“世界时代”,标识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认为处身“世界黑夜”中的人类,总体正在经受“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阿兹乌火笔下的“彝王”,通过自己生生不息的繁殖力、蓬勃有力的播撒力,让暗夜中颓败溃散的人群重新得到光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文化差异的共通。人们遭遇的是同样的命运,在摸黑找寻出路。“彝王”虽然只是一种中国边地族群的信仰和图腾,却具有全人类的价值。
这种大抒情复活的是某种小传统,通过颂歌式的抒情营造出一个超验世界,穿透了世俗和现实,完成对神圣性的复活。在科技、资本、消费主义日益强势的氛围中,弱势个体的自我出现分裂、流散和支离的局面,灵光消逝,大抒情则起到了弥合与修复作用,让自我在对于祖灵代表的共同体中圆满、充实、完整,接续了断裂的历史,重建一个世界。因此,对《彝王传》这部作品不能仅仅从通行的文学审美予以审视,它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档案和文化表达。从文化复兴的角度来看,该书也提供了多样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