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经典作家 >> 作品研究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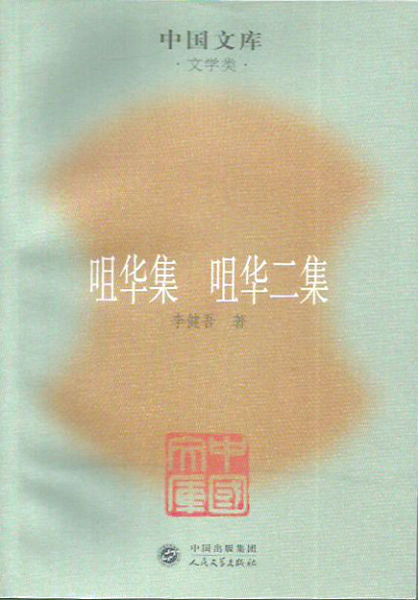
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文章,在肯定父亲李健吾《咀华集》系列作品的同时,把“咀华”之类的书评文章的停笔归结到父亲后来“主动靠拢政治”,写大量歌颂戏剧的作品,我觉得十分不妥。我不是搞文学的,但是想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人和事都需要被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我的观点不一定妥当,就当向有关人士讨教了。
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
《咀华集》是1936年出版的,《咀华二集》是1942年出版的,第二版的《咀华二集》是1947年出版的,而没有收入这两个集子的评论文则远远早于那个年代,譬如1928年在《大公报·戏剧》用6天时间连载的《关于中国戏剧》,1929年1月《认识周报》上发表的《中国近十年的文学翻译》,矛头居然直指鲁迅、周作人等大人物,1930年10月在《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对《诗人的悲剧》公演时的评论,直白地点出了熊佛西写剧的弱点。李健吾用刘西渭的笔名则早在1934年8月发表的《伍译的名家小说选》,刊载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一个27岁的年轻人,矛头直指知名大翻译家伍光健。
收入《咀华集》《咀华二集》的个别批评的文章,除了巴金已然知名外,其他如曹禺和卞之琳都还年轻,他们之间(主要指巴金/刘西渭、卞之琳/刘西渭)在报上对各自的观点来回辩论和维护,但批评和辩论都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巴金和父亲的友谊众人皆知。卞之琳到上海,没有住的地方,还是住在李健吾家,每天还是在争论。后来去外地工作,父亲一直陪送他到车站,一路上一边争论,一边啃着甘蔗,就是一对朋友。李健吾的批评针对作品,而不是人。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没有任何职称,没有派系,纯粹是文学观点上的探讨。
特别要指出的是,《咀华集》《咀华二集》的作用还在于“推出”:推出某些有争议的好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推出大量尚不为大众所了解的作家作品,如李广田的《画廊集》、何其芳的《画梦录》、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陆蠡的散文》等等,后来证明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文学评论不是简单地批评作品的短处,议论作者的是非。李健吾在《咀华二集》中表明了他对书评的观点:“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惟恐他们被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真理如耶稣所云,在显地方也在隐地方存在。他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十九不灵验,但是,有一中焉,他就不算落空。他不计较别人的毁誉,他关切的是不言则已,言必有物。”
之后抗日战争进入胶着和全力以赴的时期。在那期间,一直待在孤岛和沦陷区的李健吾,从书斋中出来,进入戏剧界,从协助于玲的共产党地下活动所需要的抗日宣传起,到苦干剧团的商业演出活动,再到《金小玉》上演,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释放之后携家小化名逃亡。逃亡到安徽的路上被在国民党工作的清华校友认了出来,只好与他们相认,也是后来回到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的吴绍澍邀请他出来工作的起因。那一个月的工作,为他蒙了灰。可是也就是这样的相识,了却他心中的一个愿望,想借用上海戏剧人才济济的条件,办一个戏剧学校,培养戏剧人才,兼有一个演出场地。其实无论是当时的上海市国民党党部,还是当时的上海市左翼联盟,都看不上他,他奔波、上书、陈述,最后只是让他管理一个破剧院,在学校教授戏文课。他竭尽全力,为组织教材,翻译了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诸多独幕剧。
抗战胜利后李健吾回到上海,他又开始使用刘西渭的笔名,写了书评《三本书》《咀华记余·刘西渭我的仇敌》《咀华记余·无题》,谈了抗日战争期间4位女作家,特别是杨绛女士的工作,还是在“推出”。之后,按着过去的习惯,回复了一位读者,名为《答吉父书》。因为熟悉上海时期的文艺戏剧活动,他不断被邀请发表类似《沦陷期间的上海文艺界》之类的文章。但是抗战胜利没有带来和平,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种种胡来,民众生活的艰辛,和谈破裂,内战又起,这让他十分反感。他以战时搞戏剧的热情改编了希腊阿里斯托芬的闹剧《妇女公民大会》,开始起名为《和平颂》,后来改名为《女人与和平》。考虑到上海民众的娱乐情结,再加上国民党严厉的管控,他和导演共同把戏改成闹剧的形式,只是明白人还是听出了“反对内战”的核心。
他深爱着这个国家
李健吾的父亲是为了打倒帝制建立民国而奋斗至死的,是山西运城的河东英烈。他带队伍、在前线作战的热情,传给了他的儿子。李健吾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非常热爱这个国家。
他刚到法国,就听到了“九·一八”事件,他在激愤之余,很快完成了《火线之外》的四幕剧,结尾的《出征歌》充分表明了他火热的心:“华夏健儿,文献吉邦,四万万众,死为国难,国殇国殇,万古芬芳:英明不朽长芬芳!一死报国!一死报国!一生一死报祖国!”
他对他研究的课题,也定性在“现实主义”,他觉得我们的国家不需要“浪漫主义”,“为文艺而文艺”是他给自己扣上的帽子,其实,文艺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他是用文艺来为这个社会服务,为人类服务。他关心这个国家,关心社会。
国难当头,于玲、夏衍委托他办事,他都一一担起,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他自己没有收入来源,可以变卖妻子出嫁带来的一些首饰,把钱用来支持上海剧艺社,捐给《鲁迅全集》的出版;失业,没有经济来源,他拒绝周作人去北京教书的邀请;他写《金小玉》,暗示着日本必败。他在日本人面前决不屈服,不交代任何朋友的名姓,只是喷着血沫子,对着给他上刑的日本人说着给自己儿女的遗嘱:“爸爸……是个……好人,……死的惨!”
他爱国,爱中国的劳苦大众。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是《工人》。那是他10岁时独自在天津良王庄念书时熟识的铁路工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心里热爱基层的文艺演出,他写的歌颂新中国的随笔杂感都是发自真心的。1951年和周小燕他们一起去山东体验生活,回来写的一个个短篇,集合为《山东好》,是从心底里写出来的,这些他并不熟悉,文字不够理想,但不是“靠拢政治”。他希望国家好,写了《社会主义的田园剧》《社会主义的话剧》《独幕剧——时代的尖兵》……在其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感情。他把他在解放以后写的戏剧方面的理论和评析文章合并成《戏剧新天》,这些文章都是他很认可的。就拿散文来说,不管是《游山的脚力》《雨中游泰山》,都可以看到他对新中国是热爱的、满意的。
他说他是小民,并始终这样认为。1982年去世前,有一次他接到聘书,坐在沙发上,拿着那张纸,对着外孙女呵呵地乐:“文学家,翻译家……他们称我这个!”他没有书房,看病不报销,写文章自己掏钱买稿纸和笔,他觉得给自己的工资已经很高了(二级研究员)。他给陈西禾写信:“我对死不害怕,已遗嘱家人:一、不开追悼会。二、不留骨灰。三、不上报。若无此人。”
他从来不诉苦,苦在心里,笑在脸上
李健吾回到清华之后大病近两年,活泼的性格变得孤寂。在沦陷时期,家里没有钱,他在傍晚到上海的小菜摊去买那些已经卖不出去的鱼,高高兴兴地向妻子展示,可是他绝不会不帮助上海剧艺社,并出资帮助《鲁迅全集》出版。
1951年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一起吃午饭,我妈气呼呼地对着我说:“他算什么资产阶级?”我当时在中学是团支部书记,哑然:真是啊!爸在一边低着头吃饭,一句话都没说。
1958年郑振铎被批判,他难受。后来郑振铎意外死亡,他成了“拔白旗”的对象。有年轻人批判他的《十九世纪法兰西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说他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认清自己资产阶级学者的老一套错误,是因为世界观和立场问题。面对年轻人,他沉默。他原来参与编辑的《文艺理论译丛》停办了。他无可奈何,就转而把精力放在戏剧方面。1959年7月,这是“反右倾”的后期,我从苏联回来,看到的父亲绝没有一点点颓丧的面容,他满意,生活安定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到1958年秋冬对自己的批判。写文章是他的生活,他天天趴在书桌上做笔记、写文章!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天中午他突然出现在我们核工业二院大院里的食堂墙边,手里提着一个书兜,我问他怎么来了,他说顺便,吃过饭了,来这儿歇歇。我匆匆买了饭提着,一起回到我住的单元,他说就在我的小床上躺躺。在床上躺了没有多会儿,他起来送我去上班,然后走了,怎么回的家我都不清楚。周末,我回家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101中学的初中学生到家里抄过家了,最糟心的是把他母亲惟一存留的照片给撕了,说她是地主婆,因为她穿的是山西妇女穿的高龄棉袄。14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之后,母亲陪伴他直到25岁,孤儿寡母,这是他惟一的亲人的照片啊!他那么难受,就只是在我的小床上躺了一会儿!可是,周末我见到的他,却是依着煤火炉,呵呵地笑着说:“我每天早上去给办公室生炉子,他们年轻人都赛不过我。”他的苦在哪儿呢?在他内心深处。
他对戏剧的热爱维持到最后
他爱文学,更爱戏剧,当然首先是话剧,是喜剧,国内的、国外的;他同样爱各种各样中国的民间戏剧和戏剧人:山西蒲剧、安徽黄梅戏、河北梆子、梅兰芳、周信芳……“文革”前,只要逮着机会,就会去首都剧场或其他地方看戏;“文革”后,病重了,走不动路了,家里有了一个14吋的电视,每天晚上都看到深夜。1958年受批判,外国文艺理论不让弄了,他就写戏评,写戏剧技巧。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为一些在过去受到错误批判的戏剧和作家平反,他被邀请参加了那次会议,陈毅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不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称,林默涵专门肯定了文学所的古典文艺理论研究;小会上他被要求发言,他做了《漫谈编剧的一些技巧问题》为题的讲话。这次会议之后,他在写戏评方面的积极性就更大了,这就是他在1962年到1965年期间完成大量戏评的时代背景。所以,绝不能把《咀华集》和戏评混为一谈,更何况他写的《同甘共苦》(《看〈同甘共苦〉的演出》)《布谷鸟又叫了》等等还是在广州会议上被平反的。他写的戏剧随笔,也是发自内心的,有当时环境的影响,主要还是由衷的。他想跟上新社会,这是他爱的国家。
1954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先是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后来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成立,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方面的工作上,给他的课题是研究巴尔扎克。他从《人间喜剧》着手,全方位地研究和评价巴尔扎克,共计完成12篇相关论文。他花了许多时间翻译莫里哀的喜剧,写过多篇有关这位伟大喜剧家的文章。他还完成了《十七世纪法国古典文学理论》(约有40万字的资料性译作和评价),所以,在杨绛女士题字的《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后记》(汇集了包括《咀华集》《咀华二集》中的各个篇目,198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他写道:
“这是我读书笔记的果实,好也罢,轻也罢,当时都公开了,不足以言‘评论’。有些很老的朋友,友谊应该发展,由于争论,反而得到了巩固。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是惟一的、正确的,是所谓一家之言。那是欺世之谈。争论是走向真理的道路。读者从争论可以判断是非,而有所收益,有所认识。他们明白我不相信自己的看法正确,所以我才将朋友的辩驳附在自己的高谈阔论之后。
“解放以后,我没有时间‘高谈阔论’了,一则,我用它来长期改造自己,这是一种乐趣,尽管有人把改造看成苦趣,二则,时间大多被本职业务所拘束,一点不是对新中国的文学不感兴趣,实在是由于搞法国古典文学搞多了,没有空余另开一个是非之地。力不从心,只能有欠了。”
总之,《咀华集》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作品,不管是时代、环境、还是作者自己的工作方向、时间,都不容许他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而不是简单地用对“政治的兴趣”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