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勒根那:草原,或草原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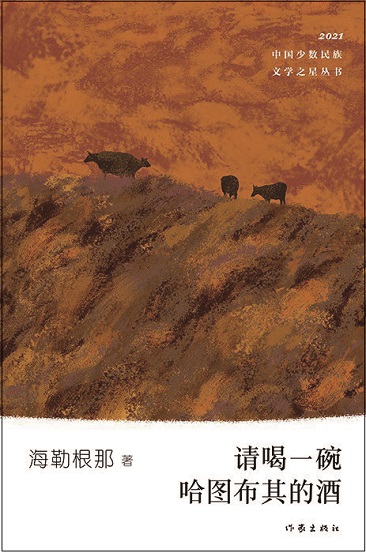
《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一书中的短篇小说,风格各有不同,就像一棵树上结了沙果、沙棘果,又结了苹果、山杏、柿子和梨。这并非是因为我多热衷于嫁接,而是因为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的腔调叙述,不同的腔调需要对应不同的口型。而最终,这些故事对应的是我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因此也决定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同的认知。
书名借用的是内中一个短篇的名字,这是我十分难得的一篇阳光灿烂的小说。在此之前,我的很多作品都充满忧郁、忧患和忧伤。2019年我随内蒙古文艺家团体去兴安盟哈图布其嘎查采风,在那里,我欣喜地看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的成果,看到了牧村红墙蓝瓦、街道硬化,道两旁园艺树整齐茂盛,原来城市才有的“华灯初上”也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农牧民脱贫致富,脸上都挂着乐观的笑容。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我高兴的了。而且不仅仅是民生,还有生态环境,我看到山青水绿,草原植被正在恢复,鸟儿和野生动物正在回归。这多么难能可贵,国家向好,百姓安居乐业,这正是杜甫在诗中所盼望的。当时我想,要是杜甫来到今天的哈图布其,一定会像李白那样“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转念又想,杜甫是中原人,不可能来到塞外。要么就是一个古蒙古人穿越到现在吧,他来到眼前的哈图布其时,会是什么情形呢?当乡亲们说“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时,他一高兴就会痛饮,就会把牧村所有的酒都喝光,那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酒,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的酒。这篇小说为我赢得了一些荣誉,曾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转载,荣登年度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排行榜,获得了《民族文学》年度奖。荣誉都是意外,在写小说的时候从没有想过,我当时只想把今天的牧村现状写出来,让古人看一看。
如果说“哈图布其的酒”是对新时代农村牧区的景色写生,是一颗光鲜亮丽的苹果,那么《放生马》就是一个牧人的内心所在,是一粒熟透落地的沙棘果。老牧人执意要将一匹服役多年的老马放生,其实也是在放生自己辛苦的一生。可让老人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在放生老马时无意中出卖了它,老马惨遭屠刀,灵魂不瞑,它思念主人,转世成了老牧人的孙子。有一天,这个孙子像马儿那样嘶鸣了几声,竟背负起老人一路奔向了崇山峻岭……这个小说是我的偏爱,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它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告诉你,人的心灵是什么样子。虽然万字篇幅远远不能尽述一个人,但读罢却会让你无法忘记这位老牧民,无法忘记他布满硬茧的双手,和他凝望草原、老马以及人生过往的老浊的眼睛。
《第三条河岸》讲述的也是心灵的故事,与巴西作家罗萨的河岸不同,这是草原人的河岸,它不在虚无处,而是在河流上空,那是蒙古人信奉的长生天。长生天对万物的救赎,侵略者对自己罪行的救赎,淳朴的牧民对无辜生命的救赎,都蕴含在这小小的篇幅中。我采撷的草原故事还有《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你们,我要杀人》《白狼马》等,当然还有森林故事《六叉角公鹿》,它描写的依然是人心,是人面对大自然丧失的敬畏之心,不守任何天条和规则的无限贪欲之心。本书中,《蒸汽火车呼啸而过》是个特例,它是我听来的故事,那个叫做“平安”的少年后来并不平安,他随蒸汽火车滚滚而去,也象征着一个年代和纯真的爱情一去不返。
这里,我还要着重提一下《巴桑的大海》,它也是唯一的中篇。主人公巴桑的孤儿命运与我个人有几分相像,只不过我把他写得更悲惨。我写他从小残疾,只身一人,没有双腿却走遍了全世界。这是我由来已久的心结,现实中,童年的我就曾经像巴桑那样孤立无援,后来我18岁出门远行,虽然没有走遍全世界,但我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的艰辛和困苦,走过了人生的低谷和命运多舛,值得庆幸的是,我还能像模像样地活着。因此,巴桑就成为了我不能实现的理想,命运让他“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给他安插了两个翅膀,最后他飞到南太平洋、北太平洋,周游列国,然后魂归大海。这便是文学的魔力,一个人靠自己的双手能走多远,一个人的梦想又能走多远,无所不能的小说给出的答案是,要多远就有多远。
作家陈涛在本书序中,给这13篇小说做了很好的归纳:“它们风格各异,叙述技巧多样,可读性与现实性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些故事背景无非是两处,分别是草原,以及草原之外的世界。”如此说来,我们还没有提到草原之外的世界。那个世界被我放在了书的最后面,就像人们总是把泪水埋藏在心底。
前面曾提到,因为家境,我18岁初中毕业后就辍学离开了沙化的农牧区,去北方的城镇做苦力谋生,《十八岁出门打工》是我当时的真实写照。在此之前,生养我的科尔沁,无论蒙、汉乡村,都民风淳朴,教会我朴实,给予我温暖,这是我最初认识的世界。等我来到陌生的、人情冷漠的城镇,两手空空的我注定在社会最底层。我会看到什么?是的,我会看到阴暗和潮湿,那些不幸的辛酸和苦难,那些不易的生存与挣扎,那些不端的暴力和尔虞我诈。《午夜沉溺》《清白的玉米》《能动嘴就别动刀》就是在底层现实中截取的故事,它们只是大海中的几滴盐水,沙漠里揉进眼睛的几粒沙子。面对纷繁现世,文学也有了自己的局限,那就是,文学永远没有现实多彩,而想象永远大于不了现实。
草原作为文学存在,从来都充满诗情画意,即便苦难也仿佛是孟浪的,就像海子的诗句,一与草原相遇便会温情脉脉。当我25岁之后落脚到中国最北部的一座草原小城,在为生存挣扎奔波之余,一有空闲就会去草原走一走、看一看,而草原就像一片阔大悠长的布幔,轻易抹去我在尘世里的尘土,让我的心变得干净,变得细腻而柔软。
这确是我的世界,一个在草原,一个在草原之外。
- 陈涛:沉静的草原与喧嚣的世界[2022-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