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巴》:当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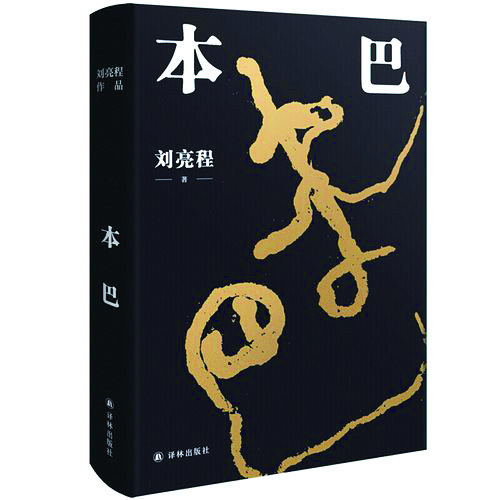
写作者首先是自己虚构世界的信徒,只有宗教般的绝对自信,作家才有勇气和智慧把一个虚构故事讲到底,最终才能被读者接受和相信。
杨庆祥:“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山丘,布河还是小溪流的时候,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25岁,美男子明彦也长到25岁。本巴国所有人约好在25岁相聚,谁也不再往前走半步。”初读《本巴》的时候,仅仅这几句就让我足够惊艳。停留在25岁不老也不死,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是25岁?是来自史诗的启示还是人生的感悟?
刘亮程:“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这是江格尔史诗的创世时间,我喜欢那个还没长大的世界。但我不能挤进这个已有世界中去做文章,史诗故事都太有趣太完美,讲那样的故事,我们是讲不过古人的。
唯一可能的书写,是在史诗之外开启属于我自己的一部小说的时间。
我最初的构想就是借史诗背景,写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文学说到底是时间的艺术。写出时间,而不仅以时间为叙事手段,这是我所追求的。
《江格尔》触动我的,正是史诗中“人人活在25岁青春”这句诗。《本巴》从这句史诗出发,起笔时并没想太清楚。但我知道小说是写出来的,只要我的语言进入,语言主宰了那个世界,奇迹会发生在下一句。
《本巴》故事的外层,是活在25岁青春的本巴国的大人。在那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史诗年代,人的世界有什么没有什么,都取决于想象和说出。想象和说出是一种绝对的能力和权力。我在小说中给江格尔赋予梦中杀人的本领,他在梦中战胜莽古斯,带领族人长大到25岁,决定在这个青春年华永驻。停在25岁是江格尔想到并带领全族实施的一项国策,他的对手莽古斯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他们会衰老。人一旦会衰老,就凭空多出一个致命的敌人:时间。江格尔的父亲乌仲汗就是被衰老打败,江格尔不想步其后尘。
小说的内部是三个孩子的故事。江格尔让时间停住在25岁的权力受到了威胁,首先是躲在母腹不出生的哈日王,他不在时间中,江格尔有梦中杀人的本领,但他的梦追不到时间之外的母腹。后来哈日王被迫出生,借助赫兰的搬家家游戏,让自己国家的人都回到童年。对付本巴国的“人人活在25岁”,哈日王的对策是“他们不长老,我们不长大”。从青年到童年间相距遥远的时间旷野,这使他们获得安全。
杨庆祥:从史诗到小说,这里面确实有一种结构的转换。史诗往往会借助神话的叙述结构,而小说则会借助故事的叙述结构。在“虚构”这个意义上,神话和故事是相通的,不过前者往往讲述神迹或者超凡的经验,而后者则更注重日常和平凡的经验。《本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将这两者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融合。
刘亮程:史诗属于“神构”世界,它不存在合理与否,说出即有,它说太阳从西边升起人们也相信。现代小说属于虚构,需要内部的合理性。写作者首先是自己虚构世界的信徒,只有宗教般的绝对自信,作家才有勇气和智慧把一个虚构故事讲到底,最终才能被读者接受和相信。《本巴》借《江格尔》史诗背景,在神构与虚构间,找到容纳一部小说的时间旷野。
杨庆祥:回到小说本身,这部小说里面的“游戏”设定都非常棒,每一个游戏其实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游戏。比如捉迷藏,比如说玩过家家。关键问题是,你用一种非常有机的方式,把这些具体的游戏,作为工具的游戏,跟人类对自由、对心灵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了。在我看来,《本巴》里面的“游戏”有四个指向,第一是作为工具的游戏,它其实是非技术时代的技术;第二是一个叙述的方法,叙事者用这些游戏来展开叙述,结构故事;第三是它有一个心灵的、自由的、审美的维度,游戏暗示了一种非功利性的生活和价值观。但是最重要的维度是建立在前三者基础之上的本体论的维度,即游戏原来构成了人类生活,甚至是宇宙的一个基本的法则,它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本巴》以一种东方化的方式把游戏高度哲学化了。
刘亮程:不同于《江格尔》中以天地初创为开端,《本巴》的故事时间始于游戏:在“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的人世初年,居住在草原中心的乌仲汗,感到了人世的拥挤,他启动搬家家游戏让人们回到不占多少地方的童年,又用捉迷藏游戏让大地上的一半人藏起来,另一半去寻找。可是,乌仲汗并没有按游戏规则去寻找藏起来的那些人。而是在一半人藏起来后空出来的辽阔草原上,建立起本巴国度。那些藏起来的人,一开始怕被找见而藏得隐蔽深远,后来总是没有人寻找他们便故意从隐藏处显身,让本巴人找到他们。按游戏规则,他们必须被找见才能从游戏中出来。可是,本巴人早已把他们遗忘在游戏中了。于是,隐藏者(莽古斯)和本巴人之间的战争开始了,隐藏者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让本巴人发现并找到自己。游戏倒转过来,本巴人成了躲藏者,游戏发动者乌仲汗躲藏到老年,还是被追赶上。他动用做梦游戏让自己藏在不会醒来的梦中。他的儿子江格尔带领本巴人藏在永远25岁的青年。而本巴国不愿长大的洪古尔独自一人待在童年,他的弟弟赫兰待在母腹中不愿出生。莽古斯一次次向本巴挑衅,洪古尔和赫兰这两个孩子担当起拯救国家的重任。
这个时间开端被我藏在了小说最后,故事一步步地回到开头。
《本巴》让时间变得随性、停顿、可逆,一瞬百年的魔力来自游戏。搬家家、捉迷藏、做梦梦三场游戏,是我带进史诗空间的新故事,游戏的讲述获得了辽阔时间,也将小说从史诗背影中解脱出来,我有了在史诗尽头言说的自由。
《本巴》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但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作家对过去的叙述,里面折射的是我们当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新的理解。
杨庆祥:这个学期我给研究生讲《当代写作与当代批评》,以5个当代写作的关键词为授课主题,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远征”。我引用了《本巴》这个作品,我认为它是用游戏的方式解构了“远征”。远征不仅仅是空间的拓展,同时也是时间的进化论,而《本巴》则用停止生长以及游戏回环的方式将这种扩张性的现代性维度解构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甚至是当代中国写作对世界写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世界文学写作中,菲茨杰拉德的《返老还童》也涉及这个主题,但他的“逆成长”叙事还是过于单线条了,《本巴》显然要复杂一些。
刘亮程:《本巴》是计划之外的写作。本来写土尔扈特东归,那是一个“远征”和回归的故事。历史上土尔扈特人从额尔齐斯河流域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100多年后又回归故土。我为那场十万人和数百万牲畜牺牲在路上的大迁徙撼动,读了许多相关文字,也去过东归回来时经过的辽阔的哈萨克草原,并在土尔扈特东归地之一的新疆和布克赛尔县做过田野调查,故事路线都构思好了,也已经写了好几万字,小说名《东归》,主人公是一位5岁的江格尔齐。部族带着江格尔史诗远走他乡,在驻牧地生活100多年,但又被迫离开,带着年幼的小江格尔齐回返故土。
在写小江格尔齐的过程中,《本巴》故事出现了。之前我写了西域古代信仰之战的《捎话》,一场一场的战争把我写怕了,写到刀砍人时我会疼痛,我在书中每个人的死亡里死了一场。《东归》又是让我不忍面对的战争与死亡。最后我果断割舍,那场太过沉重的迁徙,被我在《本巴》中轻处理了。我舍弃大量故事,只保留了12个青年去救赫兰齐那一章,并让它以史诗的方式讲述出来。这是最省劲的。我没有淹没在故事中。
但《东归》并没因此荒芜,有时回头看没被写出的那些故事,它们在另外的时间里活着,那些曾被我反复想过的人物,再回想时依然活着。或许不久的将来,他们全部地活过来,人、牛羊马匹、山林和草原,都活过来。这一切,有待我为他们创生出一部小说的时间来。
一部小说最先创生的是时间,最后完成的也是时间。
杨庆祥:小说叙事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重要的不是所叙时间,而是叙述时间。《本巴》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故事,但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作家对过去的叙述,里面折射的是我们当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新的理解。那就是我们愿意完全生活在一个被我们的日程表,被我们的手机,被我们的北京时间、纽约时间、伦敦时间所控制的现代生活里。我们试图从这个时间里面解放出来,游戏和梦都成了重要的他者。这是否也暗示了一种当下性的存在之困?小说作为“白日梦”的一种,也许提供了纾解的出口。
刘亮程:我一直在想,梦中的时间是一种怎样的时间。我在《虚土》中写道“梦中的奔跑不磨损鞋子”。如果文学叙述是一场“白日梦”,这场梦中什么东西被磨损了。文学是做梦的艺术。我甚至认为作家是在梦中学会文学表达。做梦方法被一部分人秘密掌握,成为作文手法。我们都是那所黑暗的梦学校的毕业生。梦成为时间的故乡,所有过去的未来的时间,都回到梦中。一部小说也是一处由写作者创造的时间故乡。
杨庆祥:《本巴》对时间的处理是非常独特的。时间在这部作品中不仅仅是一种均质的物理概念,而且是一个可以被赋形的能量场。时间可感,可触,可以改变。这或许与你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你在一些作品中会提到麦子以及现代的农耕生活,我知道你在新疆有一处自己的园地。形象一点说,你吃的麦子是第一手的麦子,我们吃的都是二手或者三手的麦子,你过的时间是第一手的时间,而很多在北京上海生活的人过的可能是二手时间,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阿甘本说的那种剩余时间,它是冗余的,它实际上是不构成意义的——因为无法体验到生命变化的全过程。
刘亮程:我今年60岁,在城市这个年纪的人还算年轻。在村里就是老人了。老是一种生命安排,到这个年纪你就得有老样子、老态度。
其实60岁,对我来说就是田野上的麦子青60次黄60次,每一次我都看见,每一年的麦子我都没有漏吃。
生命有限,往前走是老年。朝左右走,是宽阔的中年。朝梦中走,便是不会衰老的25岁青春。我在60岁时写出“人人活在25岁青春”的《本巴》,这是向时间岁月的致敬之书。
我自小生活在农耕与游牧交接地区,田地边时有游牧转场的羊群经过。我们家养殖过牛羊马驴骡子,我几乎是在这些家畜中长大的,对放牧自然熟悉。
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的不同,在于利用和理解时间的不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农耕社会千古不变的作息时间。因为农民的劳作是面朝土地,夜里分不清草和苗,几乎所有农活只能天亮了去干。而游牧生活中“马不吃夜草不肥”。牧人在广阔的空间内四季转场,游牧者的时间也如草原辽阔。农民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操劳一辈子。农耕时间如田块一样有形,人的岁月深陷于土地。但我们的祖先却是望着日月星辰、斗转星移获得了地上的二十四个节气。
在乡村社会,人有一个时间里的家。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三代同堂,或四代、五代同堂,一百年的时间,都在家里,活生生的。陪伴人的老物件也在。房前屋后有树,树有小树大树,小树是父亲栽的,大树是爷爷太爷甚至更早的祖先栽的,有上百年的岁数。我们在这样的树下乘凉,会想起栽这棵树的祖先,也曾经一样坐在树荫下听着树叶的哗哗声,在夏天午后的凉爽里,他也听着树上的鸟叫,也曾年复一年看到春天树叶发芽,秋天树叶黄落。一棵老树把我们跟久远的祖先联系在一起。在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就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
我们西北树长得慢,儿子出生时,父亲会栽一排白杨树,杨树7年长成椽子,15年到20年长成檩子,这样等到儿子结婚时就有木料盖一院新房子。但更粗大的大梁是爷爷栽的。做家具的木料是长了百年的大树砍伐晾干又存放多年的。一间房子里有祖先的时间。等你也活老,活成后人的祖先时,你会知道有些东西会继续活着,就像那棵树。
农耕社会是慢时间,它快不了。因为陪伴人们的都是缓慢生长的万物。种子播下去,要等待发芽,等待抽枝展叶、开花结果,这个过程是慢的。我们的农耕文明,是在等待稻谷和麦子缓慢成长的时间里发育成熟的。这种文明善于熬时间。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想改变时间速度,虽然禾苗被他拔死了,但他妄图改变作物生长速度的想法,抵抗住了时间,作为一个成语被我们记住。如今所有的使农作物快速生长的科学手段,都早已经实现他的想法。对于时间的应用,我们有了比古人更多的办法,但时间如故。
死去和活着的人,在时间的旷野上,死亡连接起的大地万物,生命延续不息,我们接住祖先断掉的那口气,接住祖先走完的路重新走,多么温暖的厚土呀。
杨庆祥: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都是人类比较早期的文明,也是长时段占据人类历史的文明类型。虽然从15世纪这一文明开始解体,但实际上它的各种影响依然留存下来并构成了人类感知的内在结构。即使在由互联网和虚拟技术为主导的当代生活中,人类依然能够感知到土地、树木、河流、飞鸟和走兽的秘密召唤。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存在,不同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认知实际上是交融在一起的。我们身上既有现代技术文明的时间观,同时也有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时间观。只不过是有时候我们被当下的表象所迷惑,以为可能性都消失了,而通过阅读、旅行和创作,尤其是通过具体的劳动,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感知到那种时间存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哲学里有明显的体现,他对农夫的鞋子的哲学阐释为“劳作”与“神圣时间”建构了必然的联系。
刘亮程:我母亲一直在农历中生活,她跟我们说的日期都是农历。她记得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日子,并依此来指导我们在书院种菜点豆。我们菜籽沟的村民也是按农历节气种植。公历没有用,它是空的,没有内容。
前年立秋日我被村民请去喝酒,庆立秋,在酒桌上听了一句谚语:上午立了秋,下午凉飕飕。下午我果真感受到了立秋日的凉飕飕。节气的微妙变化竟被我切身感受到。
古人在漫长岁月中看着天上的北斗七星,跟着斗转星移的方向痕迹,在一年的时间道路上插了二十四根路标。每当我们走进一个节气,仿佛回到时间中的一处家乡。这一时间刻度从立春开始,到大寒结束,漫长的一年中有二十四个节气的路标。如此,我们才不至于在时间中迷失方向。作为农耕民族,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在哪一个节气该干什么。
每年到了该播种的时候,我母亲都按农历节气来提醒我。我母亲说,晚种一天,迟熟10天。每年立秋之后到了白露那天,我母亲就提醒我们赶快要把菜地里的茄子辣子西红柿摘回来。因为白露一到就要降霜。“喝了白露水,虫子闭了嘴。”这是我母亲说的,虫子的生命时间到头了,闭嘴了。所有作物也关闭了生长,没长饱的果实只能是裨子了。那些遍布天山南北,匆匆忙忙从夏天开始生长,一簇簇地长到立秋,到了白露就已经是生长的尽头。万物奋力生长,果然白露一过,我就看到菜地里的蔬菜不一样了。白露这一天,成了大地上万物经过漫长的生长期,转换到另一个更漫长的、灰色的、失去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节气。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对我们的意义。它让我们从春天往冬天走的时候有一条明晰的、属于时间岁月的道路。有二十四个温暖的或者寒冷的预兆,有二十四个让我们在某一处时间中都仿佛在离去,又仿佛是回到家,那个家是已经被古人一日一日观察过的,被古人在千百年的岁月中摸索清楚。那一天从早到晚气候的变化都摸索得一清二楚。就像到了立秋这一天,我能感觉到上午和下午气候的变化。当你处在这一刻,突然间感觉到1000年前的祖先跟你处在了同一个时空,同一个时间点,更处在同一场骤然而起的凉飕飕的风中。
农历的许多节气是催人回家的,我们农耕民族,田地、父母、祖宗都在家乡。春雨过去是清明,到了回家扫墓的时间。到了墓上,看见几代先人在土中。死去和活着的人,在时间的旷野上,死亡连接起大地万物,生命延续不息,我们接住祖先断掉的那口气,接住祖先走完的路重新走,多么温暖的厚土呀。
中国人创造了千秋万代的生命时间,在家谱、宗祠和祖坟中,属于家族的时间接连不断,我的生命是祖先的千岁我的百岁以及子孙的千万岁。我未出生时已经活在祖先那里,待我过完自己的百岁归入祖先那里时,我既在祖先的行列中又在子孙的血脉中。这样的时间观是我们在缓慢悠长的农耕时光中所建立。在这个千秋万代的生命长河中,消失的生命又一代代生长出来。个体生命加入到祖先和子孙万代的生命长河中,我们获得了一个总体的生命长度。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们,都获得过这样的生命。
不过,这样的生命时间到我们这里将要看不到了。随着几代独生子女的出现,这条属于宗族时间的生命长河,显然正在断流。
杨庆祥:现代人的“回家”已经成了一种迷思,荷尔德林著名的诗歌之一就是《返乡》。这种“回家”当然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而更是指向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心灵的开启。人不仅仅活在此时此刻,同时也活在过去和未来。时间是立体的,生命是互相联系的,而艺术和小说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刘亮程:我作品中的时间书写,既有农耕与游牧时间的共同影响。更多是个人的时间感受。人活在时间中犹如鱼活在水中,不需要知道时间是什么也能活到老。但如果要去知道呢?可能文学写作是一种企图要知道时间是什么的创作。作家一个字一个句子地书写时,每个字和句子都在感知着时间。当然,时间的意义可能在于我们对它没有感知。时间静悄悄地走了。好在有文学,在生长出无穷的时间,从过往、从想象、从土壤一样的语言,生生不息。
杨庆祥:《本巴》这个作品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随便打开其中的一页,都能够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欢腾、跳跃以及反思,这是对生存的一种“本真”状态,仿佛让人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儿童时期,这也是所有艺术和神话的源头。
刘亮程:可能游戏激起了我的玩性,我们小时候玩搬家家、捉迷藏,都是小玩。《本巴》将游戏放置在戈壁草原无边的时空中,那是我从小生活其中奔跑其上的草原,能看见遥远的地平线,有着清晰的白天黑夜,我在那里呼喊,有远山回应。写作者一旦进入自己的领地,便可呼风唤雨。风成了我的呼吸,山野大地成为我的身体,生命焉何不“欢腾、跳跃”。
《本巴》最早的构思中,那些英雄们只跟时间打仗。江格尔每夜带领本巴人在梦中垒筑时间之坝,把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时间挡在本巴国之外,以保证他们醒来后依然年轻。而外围的莽古斯则想方设法破坏本巴国的时间之坝。所有战争都发生在梦中,人们不会用醒来后的珍贵时光去打仗。能在梦中解决的,绝不会放在醒后。因为醒来后打仗人会流血死亡,梦中人死了醒后还会活过来。梦里被敌人砍伤,也不会疼痛到白天。
我为这个梦中的时间之坝写了几万字。后来扔了。我感到靠无休止地垒坝来阻挡时间太累了,江格尔和本巴人累,我也累。后来三场游戏的出现改变了小说的命运。游戏让我回到自己的好玩时光。
《本巴》出版后的某一天,我在电脑中翻到扔了的那几万字,竟觉得我更喜欢这场搬石头垒坝的无休止的虚无劳动,谁都知道石头墙挡不住时间,一个从石头缝里露出的时间能消磨掉人的一辈子,但他们搬石头垒坝的执念却挡住了时间。这个坚定的对虚构的执念,产自作家内心,它必须强大如造物,才能把自己的虚构故事讲到底,在文字中塑造、改变、泯灭和重启着时间。
文学的本质是时间。
写作是用文字徒劳地垒筑终将溃塌的时间之坝。时间不可战胜,但作为个体,我们至少还有时间去徒劳地抵御时间,把自己经心选择的事物留在文字中。我们相信好文字会活下去。那些把时间兜住的文字,总会让我们有片刻的会心与停留。
- 《本巴》:一个摇摆的元现代主义文本[2022-07-04]
- 把重的事往轻里说——刘亮程的《本巴》[2022-06-30]
- 说梦:另一种返乡——刘亮程《本巴》读札[2022-06-30]
- 刘亮程:在对“家乡”的书写中抵达“故乡”[2022-06-08]
- 从刘亮程的耕读生活读懂“文学的日常”[2022-05-17]
- 作家刘亮程的八年“乡居生活”[2022-05-12]
-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正在改变[2022-05-11]
- 以诗性智慧感应生存哲学[2022-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