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2024年第5期|李锦芳:一座精神灯塔(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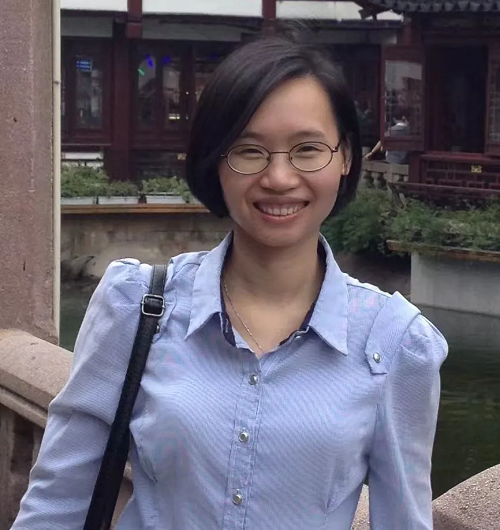
李锦芳生于1988年,常年生活在福建宁德市下辖的一个小村庄。她在谋生之余,勤于笔耕,写散文,也写小说,却未曾有作品公开发表。今《红岩》刊发她的处女作,助其起步,希望她今后越走越远,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编者按
父亲走了,在农历二月初五。这天是新历三月十四日,西方的白色情人节。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生活有时如此玄乎,竟暗暗书写着这样难以辨明的苦涩的隐喻。
在此之前,父亲已经病了整整十三个月零两天。他突发脑溢血的那天,对我们全家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连续两天,他做了两次脑部大手术。手术后,他在神经外科的重症监护室里躺了四十一天,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命。转到普通病房后,术后的并发症依然堪忧。他的肺已经白了一大部分,早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第七天就做了气切手术。此后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他都没办法说话。等到医生终于把那个外置的帮助他呼吸和咳痰的气管拔出他的身体之后,他最先说的话是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而我们作为他最亲近的家人,是多么想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啊!可是,那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大多数时候还是只能住在医院里继续接受治疗。只在中秋节、国庆节和春节才回家了,几趟在家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
在医院治疗了一年多时间之后,父亲终究敌不过病痛的折磨,因肺炎再次病危。“世上总有些无可奈何的事。”在医生对我们家属说了这句劝慰的话之后,父亲终于回家了。
对我来说这次回家的归程,似乎格外漫长。那天晚上,瘦削的父亲躺在医院安排的救护车里。一路上,我们陪伴在侧。家里的长辈们总说,依我们当地的风俗,人不能在外面走掉,一定要让父亲最终能够在家里咽气。于是,当时救护车上的呼吸机便一直开着。父亲的鼻子里还插着气管,无法说话。他的脸色发青,眼窝深陷,虚弱得连手脚也不大动弹,只有他那还在转动的眼珠聊以安慰我们。
不知过了多久,车子抵达了我们村子路口。司机不熟悉村里路况,示意我们带路指明方向。我从有些恍惚的意识里回过神来,透过车窗看到了村口的那棵榕树。春寒料峭的夜晚,夜风吹起它的一根根树须,周身的枝叶也跟着震颤。我也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便下意识地再次望向父亲。我看到他的眼珠还在转动着,才稍微镇定了些。不知是不是因为他感应到了什么,这时,比起先前,我发觉他的眼神似乎倒是有点光彩了。
村口的那棵榕树很快从我们身后疾驰而过,接着,车子驶入了一条笔直的街道。这是进入村里新街区的一条必经之路。此时,已是正月底,沿街挂着的一个个红灯笼依然刺眼地亮着。红色的光晕透过车窗照进来,让父亲的脸色显得更加莫名地异样。
这条路只有百来米,不一会儿,就到了新街区的丁字路口。我家就在路口拐弯处。只是,我们这次要回的家,是在旧街区的老房子。父亲在那里出生,他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也都住在那里。
九年前,父亲向我吐露,他想在老家盖新房。他说,从他爷爷到他父亲,再到他自己,三代都没盖新房,一直都住在旧街的那栋老房子里。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已生活在外。爸妈也到了福州,帮忙照看我哥的小孩。但是,我们都知道,父亲素来不喜欢在城里待着。他时不时地就找理由,自己一个人回到老家。父亲有时固执得很,他要是真较劲起来,谁也拿他没办法。我知道,他对于在老家盖新房的事很执着。要不然,五年前,妈妈让我回老家帮忙盖新房,他是不会轻易答应的。可是,那次他却默许了。他是多要强的一个人啊,尤其作为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在内心深处坚守着一种威严。在他看来,像家里盖房这样的大事,必须由他一个人来操持,而我也是在那时意识到父母已经老了。尤其父亲,他一向性格温和、沉默寡言,前些年却因为无法盖新房而变得格外焦躁,后来突然又变得安静,而且比之前更加沉默了。
其实,我知道父亲想在老家建新房的想法已经很久了。早在二十多年前,爸妈就已经买了村里新街区的那块地。可是,这一计划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一再延宕。这其中的缘由,包括养育孩子,孩子大了要在城里买房等等。说到底,父亲想在老家盖新房,也是想给后代留下点东西。大概十年前,政府在我们村子附近开发工业区。一些外地工人渐渐选择在我们村子里租房落脚。人流的增加让我们村里的新街区慢慢热闹起来,村民们的租金收入也随之渐渐涨起来。那时,村子里兴起了一阵建房热潮。父亲看在眼里,自然更是觉得在老家盖房是理所当然。何况我家在二十多年前买的那块地,还位于如今人潮涌动的新街区。
建房期间,尽管艰辛,父亲却格外兴奋,也格外忙碌。他总喜欢冲在前头,每天都和那些建房的工人一样穿上略旧的、耐脏的衣服,在工人们没到之前就早早开始忙活了。等到工人们回家了,他还在到处收拾、摆弄。我们家人看在眼里,常常劝他,不要当自己现在还是年轻人。那样使劲地干活,要是累坏了身体,划不来。每当听到这样的话,父亲就不高兴。他总说自己心里有数,叫我们少啰嗦。接着,他依旧我行我素地在新房工地上干活。
父亲对于在老家盖新房的热情,直到去年他大病我才真正体会到。父亲脑出血之后,神智已经不大清明。他的记忆常常是混乱的。所幸的是,家里的人,他都认得。有时,他也会主动开口找我们。为了唤醒他的记忆,在医院陪护时,我常常打开他的手机短视频软件,给他播放他以前经常爱看的视频。我发现,他平时最爱看的视频有三类:关于农村盖房子的视频、烹饪的视频,以及赶海的直播。
父亲生病前,已经有些年不再外出干活了。近些年来,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他掌厨。妈妈有时会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总是喜欢往外跑。可是,即使他有时候在外已经有了饭局,也几乎每次都会为家人做好了饭菜才出门。我们小时候,父亲经常外出干活。他跑过船,做过水产养殖。他常常一两月才能回家一趟。每当父亲回家,我们便多了一些吃平时馋嘴的水果和小零食的机会。
父亲在“吃”这件事上,似乎格外上心。这种上心,是朴实的。父亲吃饭总是津津有味,总喜欢把一些鲜脆的菜,比如黄瓜、萝卜等咬得咯咯作响。有好几次我给他水果吃,他都会跟我说,也留一些给我妈妈吃,或是给他疼爱的小孙女吃。这样窝心的话,放在以前,以父亲矜持的性格,是不大会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用行动表达爱意。
或许是与过去的经历有关,长期离家,在外奔波,父亲素喜自由。但是,他在生活上却很自律,把自己打理得十分像样。他身上并没有太多农村里常见的大男子主义习气,经常把自己的衣物扔给另一半洗。到晚年,他的衣服也总是自己洗。他很在意形象,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每隔一个月,他就要去一趟理发店。在穿着上,他很节俭。他不让我们为他多买衣服,他平时就爱穿那么几件衣服。但是,他在穿衣方面是很挑剔的。他不喜欢的衣服,我们再怎么劝他穿,他也不穿。父亲的相貌不俗。他那端正的脸庞,俊秀的眉目和高挺的鼻梁,都相当亮眼。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父亲平时总喜欢穿衬衫,这也让他在人群里显得有些出挑。
妈妈常常对我们说,要是父亲小时候能多读些书,我们家里的日子肯定能过得更好一些。实际上,父亲自己也看重教育。过去,他不让我们儿女在家里多干农话,而是期望我们能把书念好。在他看来,对孩子们来说,读书最重要。就连三年前,我姐姐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外甥高考那天,他一早就打电话过去关切和叮咛。但是,他却并不把我们的功课和学习成绩追得太紧,而是让我们自觉。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学业上,父亲的教育观念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开明。在很多时候,他都让我们体会到身教重于言传。关于这一点,妈妈偶尔会埋怨,父亲在对儿女的管教方面几乎撒手不管,而让她成为了家里啰嗦而讨人厌的“红脸”角色。有时候,妈妈很生气时,会忍不住向我们发牢骚说,父亲十三岁时就没了他的父亲,难怪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好父亲。但是,妈妈还是有分寸的,她不会当着父亲的面说这样的话。
父亲成长于艰难年代。在他九岁时,碰上了六十年代闹饥荒。那时,家里几乎已经揭不开锅了,孩子又多,便只能把他送到住在山区的姨丈家里寄养。两年之后,等到好不容易挨过了大饥荒,他的父亲终于再次来到他姨丈家,打算把他领回家。可是,当时他姨父夫妻结婚好几年了,膝下仍无子,又看父亲十分乖巧、懂事,干活还麻利,便想留下他当自己的儿子。我爷爷碍于欠着他们夫妇养育自己儿子两年的恩情,便只能再次黯然离开。
那个年代,有许多和父亲一样因逃荒而被送养的孩子。父亲那时有好几个那样的小伙伴,他们一起上山赶羊,一起下地干农活。当小伙伴问起父亲,为何不随自己的爹爹回家时,父亲失落地回说,姨丈他们不想让他回家。孩子们大多简单、直接,何况,相同的处境自然让他们更加理解彼此的心情。他的两个小伙伴对他说,山区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是回家好。其中一个小伙伴还对他说,“你多好啊!你看我们到现在还没等到我们爹爹来领我们回家呢!你啊,还是趁你爹爹没走远,赶紧追去,肯定能追上爹爹,跟着回家去。放羊的东西你就放心交给我们,我们下山后会替你还到你姨家里。我们也会帮你跟他们说,你回家了。”
在小伙伴们的一再鼓动下,父亲终于鼓起勇气,辞别了他们,然后就立即一路跑着去追赶他的爹爹。终于,跋涉过几个山头之后,在正午时分,他在一个半山坡上追上了他的爹爹。接着,父子俩便欣慰地一起回家。
这段童年的经历,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妈妈说,父亲过去常常对她提起那个回家的午后。他到晚年都记得,当他追上他的爹爹之后,爹爹给了他一块光饼。父子俩就着一点水,啃着一块光饼,就是一顿午餐。尽管如此,那样的一顿午餐在父亲的描述里,却是格外鲜美的。而那次回家仅仅两年之后,他的爹爹就因病过世了。这样的一种境遇,更加深了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
在父亲最后一次回家的归途里,在救护车上,我心里不时在想,如今父亲的神智如何,他是否还记得我们,他的记忆里是否还有那些他过往印象深刻的片段,他是否还记得那个和他爹爹一起回家的午后呢?还没等我找到这些答案,不久之后,穿过村里旧街区的一条条蜿蜒的小路,车子就抵达了我们家的老房子。
那天晚上,父亲被安顿在了他最初出生时的那间卧室——位于老房子后厅的一侧。为了让父亲在弥留之际好受一点,家里人商量了一番之后,决定在救护车的随行人员离开之前,让他们把父亲鼻子里的气管拔出来。那根管子被拔出来之后,父亲因为虚弱还是只能嘤嘤嗡嗡地说几个单字,并且说得含糊不清。我们不想让他太受累,并没有让他多说话。
第二天早上,父亲看上去比前一天精神了点。在妈妈表示父亲已经对她说了几句稍微清晰的话之后,我也凑近了父亲。我握住了他的手,他呆呆地看着我,叫着我的名字,却问我到哪里去了。那一刻,我只能微抬起头,强忍着不让快要夺眶而出的眼泪流下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对他说了两句含糊的安慰话,就黯然走开了。我只能暗自安慰,至少父亲的记忆里还有我。
父亲回家之后,撑了十天,终是离开了我们。
灵堂设在了老房子的前厅,父亲被安放在后厅中央。本家的亲戚们很快就用黑纱、白布把整个老房子布置了一番。纸糊的奠字白灯被高挂在了大门外。
这栋百年老宅如今真是陈旧了,青砖黛瓦间满是修修补补的痕迹。门匾上,“恩承北阙”的斑驳题字,镌刻着昔日熹微的家门荣光。只是,从我爷爷那辈起,家门就已败落。如今,本家的几十号人丁基本都从这栋老宅搬离出去了,只有两个年逾八十的老伯母还住在这里。我突然又想起,前年,父亲尚未生病时,还曾在我们面前念叨,他想找本家的亲戚们商量,来年大家一起集资再把这栋老房子好好翻修一下。可是,他来不及办这件事就走了。
灵堂布置好之后,亲友们陆陆续续前来吊唁。
与晚年的父亲玩得最好的玉伦哥,望着父亲的遗照不由感叹:“叔怎么这么快就走了?自从他生病后,我就少了一个伴,真是不习惯啊!”
父亲生平一向乐于交友,且待人没有分别心。他身边有好几个像玉伦哥那样比他辈分低的年轻好友。晚年的父亲总喜欢在饭后到村委会楼前或村口的榕树下,跟一班老伙伴唠唠家常,议论一些村里的公共事务和电视里的时事新闻。他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从手机短视频里看到的趣闻。
灵堂上,又一个亲戚感慨:“平时看着挺精神的一个人,怎么突然间就病得那么重,又这么快地就走了? ”实际上,我也常常暗自在心里这样诘问。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是那样坚强。我爷爷在他十三岁时就过世了。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他必须早早干活养家。他不能去上学,只能靠我奶奶在家有限地教他识点字。他小小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再后来,他自己成家了,成为了我们眼中顽强的父亲。他沉默的个性更加深了那种印象,最终却猝不及防地倒下了。
为了成为家里牢固的顶梁柱,父亲一辈子总是那么隐忍,从不轻易把自己的伤痛表露出来。他又是那样正直。他生活里好几次遭遇他人的背刺,却从不与人斤斤计较,更不会以牙还牙,总是一再忍让。现实生活的不适感折磨着他,慢慢刺痛和啃噬着他那敏感的神经和血管,直至最终被刺破了,鲜血淋漓。他脑出血之后,我常常在想,如果他不活得那么隐忍,或许会比现在好得多。
在守灵的最后一日,本家的亲戚们基本都已前来吊唁。外出多日的玉峰哥赶在那天下午,也来了灵堂。他久久地望着父亲的遗照,若有所思地默哀着。
我也忍不住又一次望向那里。只见,父亲正襟危坐,穿着他喜欢的白色衬衫和深蓝色西服,还打上了领带。他那双莹亮又有些忧郁的眼睛也直直地看着我们。父亲生前,拍照不多。这张照片拍摄于大约十年前。那时,有支摄影工作队专门到我们村里给老人拍照。父亲拍了一张,并郑重地选好了相框,放在抽屉里,交代妈妈日后把这张照片作为遗照。
守灵时,我哥正好站在玉峰哥跟前,顺势递给他一根烟。玉峰哥连忙摆手推却:“不用了,我已经戒烟了!”
“什么时候戒了?”我哥说着,继续礼貌性地把烟往前递。
“你爸之前一直劝我戒烟。” 玉峰哥停顿了一会儿,又语气低沉地感慨道:“我应该更早一些听叔的话。”
玉峰哥过去烟瘾很大。后来,我从妈妈口中得知,他去年得了肺结节。这两三年来,我们本家已经有两位亲戚患了严重的肺病。还有一个怀满叔,听说在福州做了好几次化疗,终究还是回天乏术。很可能,父亲的丧事后不久,他也要回到这栋老宅来了。
已经沉寂许久的老宅怎么一下子就要迎来这样密集的丧事?此时,老宅院子墙角边的几棵树在阳光下依然明晃晃地绿着,鸟儿在树梢间叽叽喳喳地忙碌着。生机盎然的春天尚未走远,而父亲却已经先走了。
父亲生病前,曾在老宅院子左侧的一块空地上种着好几种蔬菜。如今,那里已经荒草丛生。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两年前,秋日的一个傍晚,父亲与我在新房天台上收拾他晒的菜干。那时,家里的新房已经盖了三层。那天落日下的晚霞,红得格外绚丽。得空后,父亲难得与我一起驻足观赏。然而,他当时的脸上却依然是一副浓雾未散的表情,似乎再灿烂的风景也无法在他眼中停留太久。不一会儿,他就注目于村子不远处的工厂,那里过去曾是一片茂密的田地。突然,他以一种低沉的语气对我感慨道:“这村庄,早晚是要破败的。”
那一刻,我很惊讶,我从他的那句话里读出了感伤的诗意。与同代的许多农民一样,父亲无法用笔杆子对着田园抒情。他们用锄头,用铁锹,俯身劳作,挥洒汗水,他们与脚下的土地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他们书写田园诗的方式。我们这一代,在他们的期待下,终于拥有了运用笔杆子的能力,却反而无力写出真正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恐怕,我们往后的一代代人,都再也无法写出了。
“这村庄,早晚是要破败的。”当时,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再没有第二句话。而我也失语了,不知如何回应是好。我们都在昏黄的夕阳下沉默着,各自静静看着,沉思着,直至日落而下,天色渐渐暗淡。父亲走后,他当初说的这句话,时常回响在我耳边,持续地震颤、共鸣。
父亲在这世上活了七十三个年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个村庄。即使晚年因帮扶儿孙而短暂迁居城市,也仍眷恋故土。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一辈子沉默寡言的父亲,在他生命的许多时刻,都让我感到他对此欲言又止,最终也只能沉默地躺倒在这片故土。
父亲,您离开了我们,去往一个我们所未知的世界。在这世上,我再也寻不到您的身影了。对我来说,唯有让您化作故乡的一座精神灯塔。但愿,此后无论我身在何处,都能够靠着这灯塔找到回家的方向。
……
(选自《红岩》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