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访谈 >> 资讯 >>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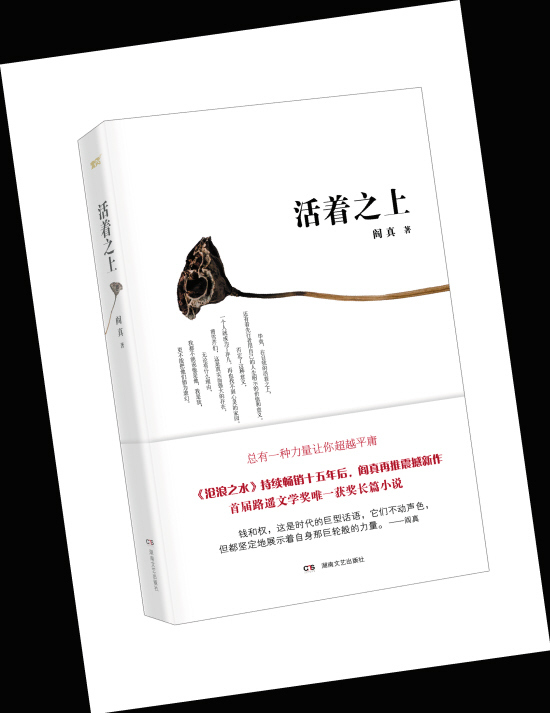

 阎真,1957年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理论著作《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另出版有《阎真文集》五卷。
阎真,1957年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理论著作《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另出版有《阎真文集》五卷。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何淑君
2001年,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出版,时至今日,已经印刷了67版。近日,他推出第四部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同样是书写知识分子的小说,这一次,阎真既是客观观察者,又因自己的高教教师身份而成为被观察的对象。
新书中,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历史学博士聂志远,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找工作、发文章、评职称,处处艰难,婚姻生活也随之举步维艰,在 迷惘和挣扎中,他依然坚守良知。聂志远的同学蒙天舒,学问平平,但因为善于钻营,广织关系网,“借鉴”聂志远的论文最后被评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三十岁已 当上校长助理。不过,也由于这样较单一的人物形象设定,有读者对小说的艺术性产生了质疑,“人性不应当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对此,阎真回应说,这是出于创 作的需要,“我将真实的事例都集中放到了这两个人物身上,这样人物形象也就随之典型化了。”
《活着之上》中有不少直击学术腐败与社会潜规则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大都来自阎真身边的真实事例。“知识分子,除了活着,还应当有‘活着之上’的部分,还是应当坚守某种信念和使命。”阎真说。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通过电话对阎真进行了专访。
A
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从妥协到坚持
羊城晚报:《活着之上》是您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从第一部《曾在天涯》发表至今快20年了,您的写作速度一直很稳定,写作内容也都跟您的现实际遇息息相关。
阎真:我写东西一定是先有想法,这个想法得有创新,而不是重复自己或他人。这个话题也许来自内心冲动的小苗头,是很朦胧的,但这个苗头是否能够成熟,需 要做很多笔记,等到它慢慢长大成熟可以结出果实了,才会开始动笔。我自己本不是快节奏思维的人,思考会经历比较长的时间,真正写作的时间反而短一些。《活 着之上》我做了一千多条笔记,初稿是用笔在纸上写的,写了两年,接下来的一年每月修改一次,总共改了十一次。
至于写作内容,我是写实型的作家,创作想象都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没有凭空捏造和过分夸张,所以我的小说很平实,接地气,非常生活化。小说里几乎每个细节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聂致远的一半素材来自我的一位同事。
羊城晚报:你是如此关注知识分子,但又和戴维·洛奇《小世界》那种学院派小说很不一样,有很强的现实关照。
阎真: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不熟悉的我根本不敢写,没有深刻了解的基础,即使是想象也有可能出错。大学毕业后31年,我一直在大学教书,对知识分子 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都非常熟悉,这一点我心中是很有把握的。《小世界》更拘泥在学术圈,而我的书写对象和社会现实联系得更紧密,批判性和现实感也更强。
羊城晚报: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您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和书写有哪些不同感受?
阎真:《沧浪之水》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生活的关联,由于社会大环境及工作单位小环境等原因,他们不得不向命运、环境妥协。当时我是抱着同情和理解主 人公池大为的态度去写的。我写社会环境对人的改造、同化,这是没办法的,你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环境,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
后来,我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愈演愈烈,有些人甚至不是从责任、良知、人格等方面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原则和态度,而是将世俗利益作为行动原则。某种程 度上,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所以,写到《活着之上》,我的看法变了。可以说,两部小说是从接受放弃信念,到对信念的坚守。
如果每个人都因为生存的需要放弃自己的信念,信念也就不再成为信念。如果知识分子全都屈服于外部力量,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只尽力谋取自己的利益,那么整个群体就崩溃了。知识分子讲求的价值和意义,不应该只是现世的功利。
B
希望自己的小说与生活保持零距离
羊城晚报:社会的功利主义浸染到高校,而您本人也是高校教师,会因此而感到心灰意冷吗?
阎真:功利主义的盛行是社会大环境,学院不能逃脱也在必然性当中,这并不奇怪。但学院是培养人的地方,如果只是培养出技术上很有能力,但精神上很狭隘, 甚至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同样应该培养年轻人的思想和人格,还是应当相信社会的公平、公正,如果完全没有信念,那是很可悲, 也很可怕的。
羊城晚报:《活着之上》写的是您身边发生的事,您有过顾虑吗?您身边的人会对号入座吗?
阎真:之前多 少会有一点,但我毕竟写的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也不太敢凭空想象,如果顾虑所有的事,我就不能写了,后来我索性把顾虑都放下了。除了有的细节太像身边一些 人,那就回避一下,其余部分都是放开写的。其实,越是像小说中的人物,他越不会出来承认,反而更会撇清关系,所以至今也没人因此来找我。
羊城晚报:具体到《活着之上》的主人公,聂志远和蒙天舒这两个人物形象非常鲜明,也因此有读者认为您的人物塑造过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了,因为人性总是很复杂的,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之音?
阎真:写小说是为了传达某种思想和观点,而这种观点需要有鲜明度,因此也要求人物有鲜明度,明确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在这部小说中,很多事情都是在生 活中真实发生的,只不过我把这些事情放在了同一个人物蒙天舒身上,那么他的人物形象就提高了,这些事情也是符合这个人的价值逻辑和思维逻辑的。比如鲁迅的 《阿Q正传》,生活中可能也有阿Q这样的人,但鲁迅在塑造形象时把他的典型度提高了。
至于聂志远,我把他放到一种纠结的状态中,并没有 把他设定为文化英雄。因为在生活中,我也没看到过这样的反抗英雄,那就不能捏造,我希望自己的小说保持与生活的零距离。聂志远也有很多缺点,他不愿意交 际,或者说有独立性,从大环境来讲也属于有信念的人。他这样的状态其实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才有更大的思想价值覆盖的力量。
C
功利主义需要其他价值来平衡
羊城晚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
阎真: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很宽泛的,受过本科教育的大学生也算是知识分子。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知识的传播也要市场来完成,市场的吸引力更大,知识 分子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淡化了。你讲了很多道理,市场不承认也没有用,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了,我们面临社会角色的挑战,完全剥离时代 背景来谈知识分子是不对的。
我始终认为,市场上的功利主义是真实的价值,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价值。功利主义需要其他价值来平衡。所以知识 分子不是要与市场抗衡,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在承认功利主义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同时倡导人道精神、人文情怀、责任意识等等。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平衡功利主 义的社会责任。
羊城晚报:《活着之上》贯穿着对曹雪芹、屈原、陶渊明这些人的敬仰,他们崇尚独立的人格精神,但穷困潦倒一生。
阎真:古代的文化英雄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用自己的血泪证明了现实富贵并不是最高的人生价值。这种状况到现代并没有终结,但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空间更大了,为人格独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尽管这种基础还不足够广泛。
羊城晚报:《活着之上》前不久荣获路遥文学奖,但为什么你在接受采访中时说,相比贾平凹这些作家,自己还是个文学新人?
阎真:应当说,我把写作作为终身使命,多少有点个人功利主义的想法。我不仅要对自己、读者负责,也还是希望争取一定的历史地位。虽然每一部长篇小说我都 精益求精,但远远没达到心中的完美。但我还是希望,当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还能有人看我的书。《沧浪之水》至今已经印了67版,如果能有机会修改,可能 会更好,但是既然出版了,就已经是既定事实了。大框架上没什么遗憾,小的技术处理上可修改的地方还是很多。
D
毕业论文应当允许写小说
羊城晚报:如今高校教师的生存状况,有艰难或尴尬之忧?
阎真:高校年轻教师的成长非常艰难。论文很难发,发篇文章一般需几千块的版面费,一个月工资才多少?获奖不容易,评职称不容易,要得到国家项目更不容易。手上没有资源的,就越没有资源;有资源的,容易出成果,成果越多,越容易形成新一台阶的资源。这就是马太效应。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担任文学院副院长一职吗?在行政和教职工作之外,还有时间写小说吗?
阎真:虽然是副院长,但手里并没有什么资源,就是个具体办事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利用这个位置为自己谋过利益。我负责管科研,事情不太多,所以还有时间写作。不过这也是我写得比较慢的原因,毕竟还要上课和写论文。
羊城晚报:有些大学教授因为写科研论文会放弃文学创作,为什么您能够一直保持创作的热情?
阎真:我不但保持着创作热情,也保持着批评的热情,这是身在教师岗位的需要。我已经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两本理论著作。有人说,文学创作是形象思 维,文学批评是理论思维,似乎会相互干扰。但对我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学理论对我的创作有帮助。如果有矛盾,那也是时间和精力上的,我主要还是往 小说创作这方面发展。
羊城晚报:都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您是否认为在课程设置和专业安排上,应该调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
阎真:现在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已经体系化了,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批评是占绝对主导的。
我还是认为高校应该开明一点,1984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写了五万字的中篇小说作为毕业论文,北大的老师还把这篇小说推荐到文学期刊《春 风》上发表,稿费七百多块,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了。现在如果有学生找我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写小说也是可以的,今年就有位同学是写小说的。我认为高校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他在创作方面有才华,就让这份才华得到展示。
何晶、何淑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