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易丝·格吕克:冷峻而温情的古典主义诗人
一
格吕克是一位怎样的诗人
做一篇露易丝·格吕克文章的召唤,既教人望而却步,又充满着诱惑。毕竟诺奖结果公布之后,太多的诗人专家学者发表了太多的反应见解。读吧,得要有足够多的时间;不读吧,这个时候做这样一篇文章似乎失去了方位感,况且自己此前对她的阅读也很有限。就连她所继承的父姓Glück的汉语译法(甚至在美国本地人口中的读法),至今仍莫衷一是,似乎权威的《世界人名译名大辞典》确定的“格吕克”也成了问题。可是,被时机唤醒的记忆是难缠的,总是在你前方隐隐约约忽明忽暗地闪烁,令人欲罢难能。

露易丝·格吕克
2020年10月8日晚间,如期等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年度获奖者的名字。不是安·卡森?看来梦是靠不住的,卡森是头一晚梦到的得主。带着未定的惊讶从书架上取出《摩罗美国青年诗人诗选》(The Morrow Anthology of Younger American Poets),翻到露易丝·格吕克,一气读完《幸福》(“Happiness”)到《山梅花》(“Mock Orange”)八首诗。这部1985年初版的诗集,收录一百零四位194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诗人,手头这册是1997年在纽约巴诺书店购买的,已是第十二刷,可见该诗集颇受认可和欢迎。初次阅读时,在目录中十位诗人姓名后用空心五角星做了重点关注标记,格吕克也在其中,只是不知为何独独在她的五角星前面多加了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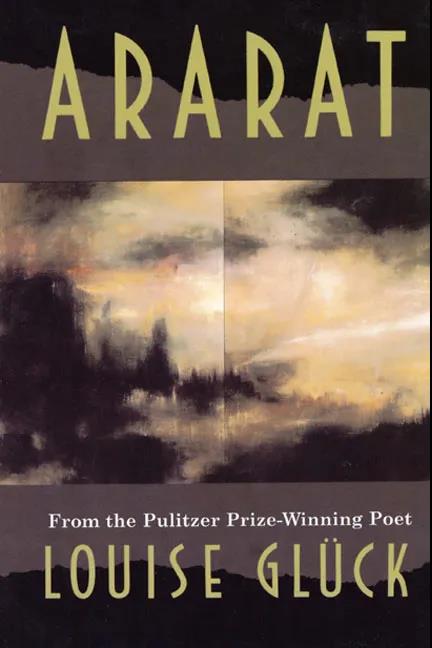
《阿勒山》
最近一两周断断续续的阅读,渐渐在脑海里建立起了一个立体的诗人格吕克形象。像诺贝尔本人一样,格吕克是一个矛盾体。她为人耿直,“举止生硬”(rigidity of behavior),却十分有趣,有时甚至天真得像个孩子;她声称从不在乎读者反应,诗“一旦印到书上便与我无关”,但她又极其渴望知音的认同,常常感叹知音寥落,不过“二十五最多三十人”;她一方面向往拥有广泛读者(实际上也真有:连普利策奖音乐奖得主都为她众多诗作谱了曲子,电影学院将她的诗作为电影题材锤炼新一代艺术家的艺术感受力),另一方面对自己心血之作的珍惜几近变态程度,似乎心爱的诗只该由她个人收藏,读的人一多就泄露了秘密,像被人偷了去似的;她希望自己的诗为大众喜爱,又担心自己成了老少咸宜的流行诗人,不屑做“一个朗费罗”;她对自己的诗艺高度自信,每每言及对过去的作品怎样“自豪”,甚至访谈中不经意流露出某部作品的戏剧性堪与莎士比亚《暴风雨》一比,又常常担心批评家比她懂得更多,看不上她的诗(“逢他们更懂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读我[的诗]。”);她反复宣称从不建议别人该如何读她的诗,但时常抱怨某个作品被人误解了,某部诗集应该如何如何读,甚至对《阿勒山》(Ararat,1990)遭遇评论界普遍“深恶”(deeply disliked)耿耿于怀,说那是自己最喜爱的诗集之一,至今“仍心心恋恋”(still very attached);她一再强调从不读自己的旧作,唯一例外是读《1962—2012年诗合集》(Poems 1962—2012,2012)校样,但谈起旧作来真是如数家珍,直教人无法相信她真的做到了作品发表出来就不曾回头翻阅过。不过,她在《诗人的教育》一文里提到她几乎“一字不差地”(verbatim)背得出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倒可以作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对自己前前后后的矛盾,格吕克本人其实也有所觉察,曾在访谈中自嘲过好像“在撒谎”。这个细节将一个单纯、天真、纯粹的诗人活脱脱呈现在我们面前。格吕克在访谈中还曝光了另一个更有趣的事例:有一回她读到学生彼得·斯特勒克夫斯一首诗,颇为之着迷,后来她发觉自己写的一首诗是偷了这位学生的,警觉之下仔细翻遍学生当年那部获耶鲁奖诗集,没找到,再翻手稿,还是没找到,惊魂未定间给学生打电话道歉,学生听了大喜:太美妙了。作家们都这么干。我们在对话。这个强加给自己的“盗窃罪”真像一段催人泪下的公案。
其实,格吕克是一个极其善良的较真的人,一位诗艺卓越的大诗人,一名具有近乎宗教虔诚般奉献精神和“高质量编辑本能”的诗歌导师。她在斯坦福大学特别是耶鲁大学出色的诗歌教学实践,主持耶鲁青年诗人书系的经历,为这些年饱受争议的创意写作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证明。上述种种矛盾所揭示的格吕克,是一个任真的诗人,一个单纯而复杂的诗人。个性的单纯与复杂,成就了其诗歌的单纯与复杂。
二
格吕克诗歌的主要特色
对格吕克的诗歌成就,除极个别另类批评者(某些先锋网站的专栏作家)和并未深入研读其诗歌作品或有所误读的评论家(如迈克尔·罗宾斯竟然认为“格吕克主要的缺点,这缺点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她所有的作品,就是她往往太放任自己由着情感支配而忘了她还有头脑”,持论公允的读者会发现这显然是无需辩驳的不实之词),英美诗歌界几乎达到了一致共识,连最毒舌、几乎没说过哪个诗人好话的批评家威廉·洛根也称她为“我们伟大的诗人”“我们的半人半女神”。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在诺奖官网亲自撰文,概述格吕克的诗歌成就,指出三个特色反复出现在格吕克的诗里:家庭生活话题,峻朴的智性(austere intelligence),以及标示诗集作为一个整体的精美的构成感(sense of composition),并称赞她的诗“兼备艾略特的迫切语气、济慈的内在倾听艺术和乔治·奥本的自决式沉默……在克己自律与不愿接受简单信条方面比任何别的诗人更像狄金森”。
关于格吕克的诗歌特色,奥尔森的概括还是相当有见地的,大致可理解为涉及三个层面:主题,诗艺(诗歌声音)和结构(谋篇布局)。这是一个应当专文讨论的话题,这里仅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格吕克的诗歌致力于探究人类生存中至关重要的方方面面。爱与分离、死与重生、理性与情感、欲望与创伤、受难与疗愈、开始与终结、失落与自我救赎……她关注的重心往往是这一对对关系中那个在普通人看来负面的因素,姑且暂时用“失去/失落”来界定。她坚称“诗是对失去的报复,它一直被迫屈从于一个新的形式,一个此前根本不存在于世上的东西。失落本身因此成了既是一种加,又是一种减:没有它,就不会有这首诗,这部小说,这件石头作品”。失落的悲伤,死亡的阴影,几乎笼罩了她大部分诗作,她之所以如此迷恋这类主题,是因为她认识到作为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一生中无法回避这些负面因素的伤害和由此带来的痛,除非你愿做花园里的石头动物:“承认像它们那样是多么可怕/不受伤害。”在《花园》一诗的这个结尾,格吕克从反面指出了遭受伤害的必要性——感受痛、悲伤、失落、脆弱,这些都是人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人只有将自己的理性磨砺成一把双刃锋利的刀子,一刃向内解决内在的恐惧,另一刃才能切开伤害的纠缠。按格吕克的理想,最好是以艺术创造的方式接受它、利用它,从而实现自我的救赎性变形,成为一个新的自我。
为了在诗里处理好如此多令人心悸的主题,令人信服地述说种种伤痛,格吕克发展出了一系列高超的技艺,形成了属于她的独特诗歌声音。词汇,语言,言语,节奏,都极富个性。她诗的语言,就像剔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渣屑的骨头,乍一听,质朴无华,散发着丝丝冷气;细细品味,自有一丝暖意悄悄升起,驱散先前的寒凉。这语言,更有一种如银针直刺痛点而不亦舒畅哉的力量。有诚意的读者,几乎没有不喜欢她的语言的。随手译几句简单的:“在我受难的尽头/有一扇门。”(《野鸢尾》)“会失去的你为什么爱?/没什么别的可以爱。”(《源自日语》)“爱冷酷/死更冷酷/冷酷到正义不可及的/(是)死于爱。”(《迦太基女王》)“我将思念的不是大地/我将思念的是你。”(《十字路口》)“死神伤害不了我/只有你能伤我更深/我心爱的生活。”(《十月》)“人生真邪门,无论怎样终结,/总是装满了梦。决不会/我不会忘记你的脸,你狂躁的人眼里/胀满了泪水。”(《人生真邪门》)“我儿子身着防雪服蹲在雪地里。/又一首诗,《幸福》开了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白色的床上。”(《开蒙》)“……暴雪/爹地需要你;爹地的心是空的,/不是因为他要离开妈咪,是因为/他要的那种爱妈咪/没有……”(《可怜的狗狗暴雪》)
值得强调的是,格吕克的诗里常常散落着幽默风趣的桥段,令人泪中带笑。比如:“整个人生/我一直拜错了神/当我注视对岸的/森森木木,/我心头的那支箭/仿佛它们中的一个,/摇曳着,瑟缩着。”(《耻辱》)《人生真邪门》居然这么结尾:“我想我的人生完了,心也碎了。/然后我就搬到了坎布里奇。”
格吕克深知,对情感的言说,不能由一种声音表达,许多微妙的诉说、蕴含在这些诉说里尖锐的思想和残酷的真相,必须借助权威的叙事者之口。于是,她较早就开始尝试采用诗歌人格(persona)的方式,并将这一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圣经》、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等中的人物,甚至自然界的树木花草,都成了格吕克诗歌的言说者,代表诗人诉说着许许多多诗人自己不便言说的真相和真理。她诗中的情感都是真实的,角色和场景都是虚构的,诗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情境剧,正像学者所说,“直面死亡的荒凉现实,将人类生活戏剧置于四季轮回和草木生命背景里,翻造出一个始终在欲望与悔恨间寻求平衡的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吕克诗里个体的情感体验获得了普世的意义,也正是这一类诗作为格吕克赢得了“古典主义诗人”的定位。以《野鸢尾》(The Wild Iris,1992)、《阿佛纳斯》(Averno,2006)等为代表的这类人格角色诗深受读者喜爱。
格吕克的诗歌在谋篇布局上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也是她自己一再吁请读者重视的,就是诗集中诗作的连续性。她坚称自《阿勒山》之后的每一部诗集,应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对待,整部诗集就像一部长篇小说,应作为整体来阅读,而且最好是一气读完。为形成这个特色,格吕克可谓费尽心血,有时就因为这个原因,一部诗集要等上好几年才能等来合适的诗。
三
是什么成就了格吕克的诗歌
成就格吕克有着上述特色诗歌的因素繁多,下面主要根据堪称理解格吕克诗歌艺术的基础文本《诗人的教育》和相关材料做一个粗浅的归纳。
首先,跟她从小的家庭教育和天赋有关。格吕克生于一个“非凡的家庭”,双亲均“景仰智力成就,母亲尤其崇敬创造性天赋”,不仅领着女儿广泛阅读,使得女儿“三岁时便熟谙希腊神话和故事里的人物”,为日后以神话人物构建自己现实生活诗歌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鼓励她进行诗歌和故事写作。格吕克在该文里引用的五岁时写的那首八行小诗,显示出极高的诗歌天赋。童年的阅读和写作锻炼了格吕克的语感,使她认识到诗的语言是“规则的语言,秩序的语言”,并且形成了“对最简单词汇”的偏好,“这样的语言,在几个个体词语内,可能包含着最大最富戏剧性的意义变化”,以及对“词语上下文种种可能性的痴迷”,这到后来发展出“写作是寻找上下文(语境)”的创作观。
其次,青春期因厌食症接受长达七年的心理治疗,这段经历对她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格吕克不属于自白派,也不同于洛厄尔和普拉斯之后的所谓后自白派。倘若没有心理分析师的教导,也许她会走上自白派的诗路。幸运的是,疾病不仅给了拯救她心理和肉身的机会,更带来了升华她诗歌艺术的机遇。她坦承:接受心理治疗前的习作和写作,注重的是单纯的感受,“狭隘,做作,无生气;而且不食人间烟火,神秘兮兮”。当她去责怪医生将她治得“太好了,太完整了”而写不出诗时,医生的话让她沉默了:“世界会给你足够多的悲伤。”这使她意识到“世界存在的事实完全不是由我所决定的,它将不为所有自我中心主义者所动”:
心理分析教会了我思考。教会了我使用我的倾向性去反诘自己想法中已清晰表达出来的想法,教会我使用怀疑,教会我审察自己的言语,找出其中闪躲和删除的东西。它给了我一项能够将麻痹这一自我怀疑的极端形式转化为洞察的智力任务……梦的解析的关键是对客观意象的使用。我培养出了一种研究意象和言语类型的能力,尽可能客观地看它们体现了什么样的想法……我拖延结论的时间越长,我看到的就越多。我想我也是在学习如何写作:写作时,不要将自我投射到意象上。不要一味允许意象……不受头脑阻碍地产生,而是要用头脑去探究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表的与深层的分离开来,选择深层的。
也许可以这么说,格吕克诗歌特色中具有基因分量的诗歌敏感(sensibility),基本上是在这段经历中锻就的。
第三,得益于格吕克的师承,以及她悟性极高、博采众长的学习能力。格吕克因厌食症错过了进入常规大学学习的机会,而是选择进入主要为退伍军人设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众学习学院诗歌研习班深造诗歌创作。如常言所说,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她在这里遇到了两位好老师,莱奥尼·亚当斯和斯坦利·库尼茨,尤其是大诗人斯坦利·库尼茨。后者对格吕克诗歌严格到几近疯狂的审读,将她的诗歌敏感磨砺出了新的精准度,令她终生感激。
格吕克的间接师承是向经典学。莎士比亚、布莱克、济慈、叶芝、艾略特,这些大诗人的诗作,如前所述她自小就熟读。也许因为天资聪颖,她很小就悟到,这些诗人“就是我的语言的传统:我的传统,就像英语是我的语言。我的继承。我的财富。早在经历之前,一个孩子就能感受那伟大的人类主题:孕育失落、欲望、世界之美的时间”。这时的阅读还给这个孩子带来一个强烈的冲动——要和这些大作家说话。后来,格吕克在访谈中谈到,她不仅感受到布莱克、艾略特、叶芝在纸上的声音,更感觉他们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伙伴”,觉得这时“我能够跟他们交谈”了。当格吕克具备了与这些大师对话交谈的能力,她便得心应手地将他们各自的特质融汇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
除了直接间接的师承,格吕克还善于在问中学。她经常就诗歌创作征求同行和友人意见。《野鸢尾》成书之前,格吕克对全书结构不甚自信,便把手稿给一位古典学家朋友看,问她看诗稿有什么得失。朋友说:“哦,你没有忒勒马科斯。”“可我没篇幅给忒勒马科斯了。”忒勒马科斯最终成了全书主要人物。“他拯救了我的书。”前述“偷诗”逸事中,那首诗格吕克在后来的访谈中提到题为《过往》,并坦承“深受彼得的影响”,虽语言是自己的,但那梦境般的质地应该归功于学生。
格吕克还善于接受诗之外的影响,向其他艺术门类(小说,歌剧,绘画等)等借鉴作诗之法。她不仅向卡夫卡学超现实氛围营造,还在其超短篇小说影响下开始了散文诗创作,受到诗歌界盛赞。莫扎特的歌剧《魔笛》《费加罗的婚礼》,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岛》等,都曾给予她启迪和借鉴。她甚至以园艺入诗。《野鸢尾》出版后,不少读者来信向诗人咨询园艺知识,其实她并不精通园艺,只是种种花而已,那些知识是从《白花农场目录》里学来的。
第四,格吕克独特的个性也是成就她独特诗歌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格吕克自小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拒从俗流,某种意义上说厌食症是这一个性的极端反应。她很小就有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而且相当坚定,八九岁上有一回搭同学母亲便车时,在车里朗诵自己的一个习作,同学母亲大加赞赏之后,决定调整一下她最后一行的破格。她愤怒得大吵一架,那个破格是她“蓄意而为”的。
这个性还练就了她非同常人的眼光。早期诗作《芝加哥列车》以“我”凝视着婴儿头发丛里的虱子结尾,引得尼尔·斯坦伯格大为赞赏:一般人只看到婴儿的怜爱,诗人格吕克的目光却深入婴儿发间。难怪她的诗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穿透力。
格吕克还是一个创新意识极强的诗人,不仅不重复她的师承(艾略特,济慈,狄金森等),也不重复自己,每一部诗集之后都要寻求新的突破,句法上的,结构上的,时态上的,一首诗结尾的方式,诗的气息、声音,甚至名词在一部诗集中的地位……统统都是创新的切口,可谓呕心沥血。这正是她甚至得以比狄金森还走得远了一步的原因。
四
格吕克诗歌的现实意义
瑞典学院给出的授奖理由——“以其峻朴的美赋予个体生存以普世意义那明白无误的诗歌声音”,表明诺奖评委们真正通读也读通了格吕克,并且受到了感动。安德斯·奥尔森在前面提及的专文中指出,格吕克“全部作品都以追求明晰为特点”,她的诗中“自我倾听它的梦想与妄想最终剩下什么”,“在直面自身妄念时无人比她更为刚毅”;她“不仅热衷于(探究)人生的离格脱轨与飘忽不定”,更讴歌“剧烈的变化和从深深的失落感飞跃而起的重生”。格吕克的获奖实至名归,她的诗符合诺贝尔遗嘱对文学奖的规定。作为肉身凡胎,我们面对的现世困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不得不遭受一些最丑陋的东西,比如背叛,失去,贪婪,而这些格吕克在诗中做了无畏的审视,并以诗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忍受和超越的洞察。她的诗以强烈的情感和智性力量慰藉着我们,改变着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
因此,不难理解诺贝尔文学奖授给格吕克何以受到诗歌界、文学界、主流媒体和诗歌读者相当广泛的欢迎和赞许。不少论者注意到了格吕克诗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以及诺奖委员会肯定这种价值的意义。媒体以他们的标题表达各自的立场:《何以露易丝·格吕克是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的得主》(《新政治家》),《诺奖提醒我们露易丝·格吕克在当下为什么重要》(CNN),《何以露易丝·格吕克令人振奋的敏感的诗该得诺奖》(纽约《观察家》);《卫报》发表著名作家托宾赞贺文章时,用的标题是《露易丝·格吕克:科尔姆·托宾谈一位无畏而坦诚的诺奖得主》……海伦·霍尔姆斯援引诗人布伦达·肖尼斯“推特”言论,称格吕克获诺奖“提醒我们,语言与情感的内在世界——有关惊奇、狂热、苦楚、矢忠和精准的——在一片生硬愚昧的专横声中仍然有人听到,读到,懂得”,进而指出“通过转化和嬗变自身的痛楚,格吕克向读者展示了借助自己的艺术作品得以幸存的办法”。
诗歌评论家斯蒂芬妮·伯特指出,“格吕克的诗直面大多数人,直面大多数诗人拒绝的真相:走运的话,老年是怎样地咄咄逼近;我们怎样做出无法信守的承诺;失望怎样渗透进甚至最幸运的成年人的时间表”,作为“一位智慧诗人”,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诗篇“既发自肺腑,又深具智性……后期作品超越美国诗歌,直抵契诃夫忧郁的宏博”;尽管“没有一个诗人可为所有人代言”,但“格吕克朴素的诗行和宏阔的视野诉诸许许多多人共同的体验:感到被忽视,感到太年轻或太年老,以及——有时候——爱着我们发现的生活”。也许这也是瑞典学院授奖理由所说的普世意义的一个方面吧。
笔者一直在想,也许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是促成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格吕克的一个偶然但重要的因素。每当遭遇灾难,人们首先向诗歌寻求慰藉。“九·一一”等突发灾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代诗歌复兴。人们发现抚慰心灵的良药,还是诗。就抚慰心灵而言,格吕克的诗不同于奥登等人的,奥登诗的直接性可能更适合抚慰“九·一一”这类突发灾难中惊魂未定的心灵,而格吕克的诗“在一个持续播报、快速新闻循环和不知羞耻的自我推销时代,守护着亲密性、私密性、内在性……在我们需要她的教诲之时——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都不确定,隔离着,恐惧着——露易丝·格吕克一直是这样的诗人,她教导我们受难、湮灭,甚至死,都不是我们的终结……(因此)在悲伤和隔离的时候,我就求助于格吕克的诗集为我指一指向前的路”。要从格吕克的诗里寻找慰藉的力量,需要细细体味,抚慰被此起彼伏、欲去还留的Covid-19这类瘟疫折磨的人类,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