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新诗学:论苏联“科学艺术文学”的建立
20世纪60年代,瓦拉姆·沙拉莫夫(长篇小说《科利玛故事》的作者)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古拉格最著名的文学见证者),一再坚持地提出,必须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在他看来,需要一种新的“纪实”文学来书写大屠杀和古拉格的重要经历1。如今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是,大约30年前,在他1929年至1931年第一次入狱后、1937年第二次被捕前的极短时期内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沙拉莫夫曾自认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文体”的热情支持者:所谓的 nochno-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这个词来自俄语的“小说”术语(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可译为 “科学虚构文学”, 也可译为“科学艺术文学”(中文语境下的“科学文艺”)。因此,包括沙拉莫夫在内的所有该术语的倡导者都强调,不仅要坚持“虚构性”(khudozhestvennost'),而且要把“技巧” 或“艺术”(iskusstvo)——“艺术” 品质——作为新文体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要素,新文体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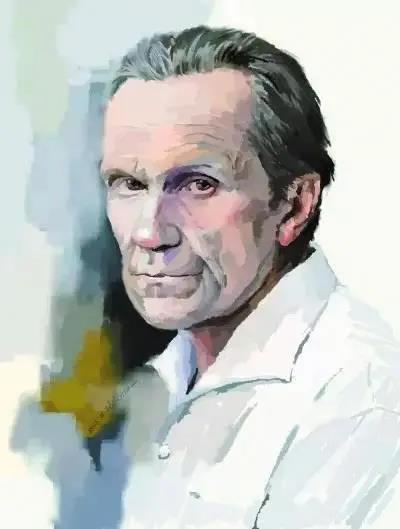
瓦拉姆· 沙拉莫夫 ▲
1934年12月第一届全联盟作家大会结束后,沙拉莫夫立即在《阵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与小说》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创造这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文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章要求:
想象一下,你自己是一名作家和科学家的集合体(当每一位文学家都是“专属于”一个特定的科学领域时),正在创作一部关于我国未来、世界未来的巨著。每名作家和科学家都为这个项目贡献了自己的幻想和自己的知识,构建了他的那部分共同的不朽建筑。多么宏伟的建筑啊!多么耐人寻味的精心栽培之作。创作一部科学小说作品,塑造读者的科学世界观,这是多么超前的规划啊!……在我们国家,科学和艺术不是目的,也不仅是知识的工具,而且是改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苏联小说的任务是改造人,也即改造读者2。
沙拉莫夫没有预料到自己将来会被监禁,他显然从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中看到了重新进入苏联文学界的机会,并协调他个人经历和职业兴趣,以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斯大林社会的新社会要求,正如斯大林曾经说过的那样,号召作家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3。

Esse o poezii i proze,收录《科学与小说》一文 ▲
但是,沙拉莫夫所寄予厚望的这种现在几乎被遗忘的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类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重构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条件,促使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当时著名的儿童读物作家萨缪尔·马沙克在第一届全苏作家大会召开前夕,推出了这个复合词——nochno-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并创造了一种位于文学小说和科学报道交叉处的新文学类型。在强调围绕这一文类的主要论点时,我将阐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确立为文学创作的唯一美学理论的过程中,它的构成是多么困难和有争议,以及为什么直到战后才成功地确立自己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流派。在最后一节中,我将分析这一文学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的特点,然后再简单地回到一个比较概括性的结论,并对解冻时期以来这一文体的稍稍复生进行考察。
战时:反对“趣味科学” 和“科学幻想”
大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通常被描述为苏联历史上的乌托邦时期,当时众多的政治活动家、艺术家和作家建立了实验性的“梦想实验室”,以新人类、多样化的前卫艺术和科学创新来发展创造美好世界的乌托邦思想和科学构想4。相比之下,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则被描绘成一个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规模恐怖和压制一切乌托邦方式下的审美统一的时代5,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战争间歇期科学发展和文学想象的相互关系,情况就开始显得有些矛盾和复杂。
一方面,在1920年代,在广泛的科普写作领域,许多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在受到一些限制的情况下,继续着革命前时代的“文明使命”,即通过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教育来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富裕、更公正的社会6。雅科夫·别莱利曼可能是这一领域最著名的作家。他以记者的身份在《自然与人》(1890-1918)等大众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最早报道火箭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人之一。别莱利曼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小册子《星际旅行》于1915年首次出版,并被证明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随后的几年里重印了十次7。佩雷尔曼于1919年创办了苏联第一份大众科学杂志《在大自然的实验室里》,并继续撰写各种科学主题的“趣味性”教育书籍。在他的畅销书《趣味物理学》于1913年问世后,又有10种类似书名的出版物问世,如《趣味几何学》(1925)或《趣味天文学》(1929),印数达数百万册8。这套丛书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激发了无数的模仿者,例如由地球化学家、矿物学家和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弗斯曼撰写的《趣味矿物学》(1928),到1953年已经重印了24次9。这些小册子和类似的小册子、文章和教育作品试图以“简单而激动人心”的方式介绍科学,并以历史轶事、奇怪事件、悖论、谜语和笑话来吸引读者10。
与这一广泛的大众科学话语领域密切相关,事实上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是所有不知疲倦的实验者和科学创新者,他们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之后,试图在自己的学科中实现革命性的突破,他们渴望世间的长生不老、行星间的太空旅行或自我延续的生命力11。这种科学热情弥漫着强烈的乌托邦主义,使19世纪乐观的进步信念得以延续,这种精神与新经济政策时期(1922-28)苏联社会各个层面所面临的日常问题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涉及现代性和工业技术进步的破坏性后果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普遍恐惧的冒险小说体裁,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12。《世界探路者》《知识就是力量》和《冒险世界》刊载了无数的故事和连载小说,内容涉及疯狂的科学家、畸形的发明和技术革新。这些发明和技术革新非但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引发了战争冲突、无情的剥削或残酷的镇压。今天,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的小说《世界主宰》(1926)、《空中之战》(1928)和《卖空气的人》(1929)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小说作品,讲述了技术科学进步的迷人和可怕之处,这些作品大多以荒诞的方式实现13。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股广泛的大众写作中,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观点即使有,也只是在情节的最后展现,而不是作为科学进步原本固有的东西出现14。

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 ▲
但是,在这两种主流倾向——一方面是相当乌托邦的通俗科学文学,另一方面是相当荒诞的虚构冒险文学——之间的某个地方,来自“相对较小的知识分子圈子”的少量前卫艺术家宣称,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机械化的最新成就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至上顶峰”15。形式主义者将进化论的思想融入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未来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受科学公式的启发,梦想着人与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提出了关于如何彻底重塑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领域的革命思想;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倡导者在1917年组织了Proletkult,宣称流水线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准16。这些前卫的艺术家和活动家希望对艺术和生活进行革命,虽然他们获得了国际声誉,但无论是在工厂工作的人还是在科学领域工作的人,都没有给予他们多少鼓励。
在1927年12月党的十五大之后,所有这些异质性的倾向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联合反对派”在这次大会上有效地终结,旨在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32)也得到了批准。首先,在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中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Proletkult)的支持者赢得了对反对派团体的暂时胜利,其后果是一个极富论战性和政治性的时期,在解释和出版的特权方面出现了严厉的批评、严格的审查和文化摩擦。

Proletkult(无产阶级文化)▲
这种所谓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娱乐性科学”的大众化,因与社会主义建设工地的日常工作相去甚远而受到严厉的抨击。但冒险小说也完全被当作“反革命违禁品”而被抛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幻想”(nauchaia fantastika)(在此之前主要由商业界而非文学界使用)被一些评论家和作家引入,作为冒险文学或纯幻想的替代。它是一个有用的术语,用来强调该文体在科学概率意义上“现实地”处理科技创新和社会主义进步的未来结果的倾向。虽然这个词受到了极大的争议,但这个词就这样被确立为苏联形式的“科幻小说”的体裁描述17。
然而,随着经济和农业部门的强行重建所带来的第一个灾难性后果变得明显,而且RAPP的努力也明显地打击了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而不是激励他们承受五年计划的巨大负担。因此,在1930年代初,党再次改变了文化政策。它解散了RAPP和许多其他组织、私人出版社和期刊,以期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控制的文学和新闻生产领域。新政策在1934年秋达到了高潮,召开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届全苏作家大会。
我们不去详细复述这次文学政策的重新调整所产生的不同的、部分是破坏性的后果,但在大会召开前的生动辩论的结果之一是,高尔基与马沙克一起提出了“科学艺术文学”(nochno-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一词。两人预示着这个词是对一种新的文学的描述,这种文学可以把低级科幻小说的娱乐性因素、科学普及的教育性优点以及为社会建立新的“科学”世界观的艺术和思想任务融为一体18。在《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高尔基和马沙克提出了关于大众新文学的想法——特别是针对儿童的,但成年人也感兴趣的新文学19。马沙克在作家大会上关于儿童文学的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这些公开辩论的结果,他把这种方法定义为对现实的“新认识”。
他们没有把自然、人类和道德表现为一成不变,而是努力向读者展示各种现象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系,并对世界进行充满激情和明确的描述,使人们感到有必要去抗争,去重组生活和自然。20
就写作本身而言,作者要避免抽象的、“娱乐性”的智力游戏或“不切实际”的冒险情节,而要回到“真实生活的轨道上”,然后作为参与观察者,在生活的实验室里有所发现21。马沙克只称赞了他的弟弟、高尔基个人最喜欢的伊利亚·马沙克(笔名米·伊林),认为他正是这种新文体中最有才华、最成功的宣传家。如今,他的名字大多已被遗忘,甚至在苏联文学和科普文学专家中也是如此22。但伊林生前是苏联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共出版了269本俄文版和译文版图书。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鲍里斯·利亚普诺夫(Boris Liapunov)指出,他的作品以大约40种语言发行,总发行量达到近5亿册23。他以1930年出版的《伟大计划的故事》赢得了声誉,该书第一年就多次印刷。该书叙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声称的和预期的成功,并突出地描述了它的光辉前景24,甚至连书名在“科学艺术”文学意义上说都是程式化的:叙事方式不叫作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文论或素描集,而叫 rasskaz,意思是虚构的“传说”或“故事”,甚至都不被认为是报道“实际的”现实25。
因此,在作家代表大会上,马沙克提出了一个概念,即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以替代以前的“娱乐性”科学文学,以及替代冒险写作和科幻小说(科学幻想)。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可怕的消极后果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而未来则被描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科学家与艺术家、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人类与机器、工作与休闲、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具有高度生产力的集体。
同时,这一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邀请前卫派和前“无产阶级文化”作家把他们的一些核心方法和艺术主张转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美学中来。这种类型的典型情节并不是围绕着杰出的科学家或独具匠心的发明家展开,而是围绕着为实现科学突破而设计的可选创意和实验环境。当谢尔盖·特雷蒂亚科夫这样的前卫作家要求写一部“事物传记”时,科学文艺作家们就以《发明历险记》这样的作品来回应,这是该类型最典型的图书之一。该书由亚历山大·伊维奇(Ignatii Bernshtein 的笔名)撰写,1930年出版,到1939年又修订版重印了两次,它的开篇“乌托邦与真理”以埃德加·爱伦·坡的《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1845)的缩写版开始。在这个故事中,山鲁佐德讲述了水手辛巴达又一次不平凡的旅程,他先是遇到了一艘蒸汽船,然后是热气球、一台铁路发动机、一部电话、一台电报机和一台打字机。但山鲁佐德的故事讲得越多,哈里发就越不相信她,在厌倦了她的“荒唐的”、“荒谬的”、“荒谬无稽的”“胡言乱语”之后,他在第二天早上判处她死刑26。伊维奇解释说,一个充斥着十九世纪发明的故事对古代的听众来说是不可信的,因为人们只能想象他们从已知想象得到的东西。然后,他们把他们能够从自己的时代想象出来的东西,在数量上加以放大,并把它们作为“拙劣的预想”(plokhye predvideniia)投射到未来:根据伊维奇的说法,他们无法设想任何根本上、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伊维奇接着认为,与哈里发一样,即使是“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H.G.威尔斯在1922年称列宁为“克里姆林宫的梦想家”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中,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变革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伊维奇指出,即使是“最杰出的奇幻作家埃德加·坡”,尽管他有着丰富的幻想能力,但他也彻底错了,因为他没有向前看一千年,而是常常落后于自己的时代27。
在科学文艺流派的倡导者看来,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这种以前难以想象的对未来的质的飞跃已经在发生,文学的任务就是要赋予这些伟大的乌托邦以想象的形态,不是作为可怕的“科学幻想”,而是作为令人信服的、真实的“科学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希望全国各地的大工地能把中亚的沙漠变成繁华的绿洲,把西伯利亚的荒原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和农产品。但是,这些乌托邦式的“发明冒险”就好比易于运输、极其耐用、由太阳充电的强大电池的憧憬,或者是远距离心灵感应的梦想28。
在审美集中化和同质化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政治中,1934年和1935年的文学和文化活动家们抓住了这一文体,并将其视为典范。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会阅读,他们积极向书籍和杂志的出版商推销这种文学作品29。在作家大会之前、期间和之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作家都表示支持这一新的文体,正如著名的电子专家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拉皮罗夫·斯科布洛所希望的那样,它应该激发“对科学和技术的热爱”30。因此,不仅瓦尔拉莫夫,而且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瓦伦丁·卡塔耶夫、费多尔·格拉德科夫等作家也在杂志特刊上提倡这种新类型的小说31。
这种新的类型只有一个真正的缺点——它不能吸引读者。相反,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人,包括在校学生,更愿意继续阅读娱乐性的科普读物,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阅读老式的悬疑科幻小说。此外,几乎没有作家愿意写这种类型的作品32。少数愿意写这种类型的作家有康斯坦丁·鲍斯托夫斯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和前面提到的米·伊林,他们在整个30年代都在不懈地试图建立这种新的类型33。然而,来自教师、图书馆员和出版商,还有科学家和学者的抱怨源源不断,他们希望有一些不那么枯燥的东西可读。因此,在1936年高尔基去世后不久,有关方面就决定取消“科学文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典中所宣称的核心作用34。
战后时期:纯文艺文体的幻象
1939年秋,著名的科学教育刊物编辑和作家列夫-古米列夫斯基对他的批评家们感到失望,他把正在进行的对传统科普作品的争论总结为一种“坚不可摧的幻象”的争夺。
尤其是科普文学,和其他所有形式的文学一样,都有自己特定的幻象。在这些幻象中,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幻象脱颖而出,即宣称必须将一本教育书塑造成一种纯文艺的形式,以保证其情感上的吸引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术语——“纯文艺化”。35
这种“纯文艺化的幻觉”与新“科学文艺”的追随者就如何写出高尔基在十年初所倡导的科普作品所提出的主张密切相关36。虽然在高尔基去世后它被推到了幕后,但这一文体从未真正消亡。“纯文艺化”一直与琐碎的科普作品能够转化为成熟的文学小说的希望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这一文体在战后时期获得了惊人的回升。早在1945年3月,这种希望就已经实现了,苏联作协决定成立自己的“科学文艺委员会”,将科普和科幻小说的作者都纳入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奥布鲁切夫、亚历山大-奥巴林以及地理学家、斯大林奖获得者尼古拉-尼-米哈伊洛夫在内的著名学者积极支持,伊尔因成为创始成员。作家和电影导演,如谢尔盖-埃曾施泰因、亚历山大-卡赞采夫、什克洛夫斯基、鲍斯托夫斯基、列昂尼德-特劳贝格等人积极参加了委员会组织的公开和内部讨论。
但是,出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新诗学的最终确立而激发的欣喜很快就消失了。相反,委员会获得了“一个相互狂欢和隐瞒失败与错误的党派”的可疑名声37。这是由于委员会试图在其成员以及科普领域内树立权威时存在巨大的问题,因为不仅科学家们自己,而且老一代作家和批评家都赞成更“娱乐化”的科普观念。这些老一辈作家从年轻时就喜欢儒勒·凡尔纳或 H·G·威尔斯这样的作家,因此他们也支持出版冒险题材的科幻作品。有一个事实对于科学文艺委员会的发展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那就是,在战后不久的几年里,每一个科学学科都缺乏任何既定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框架。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科学经历了一些学者所称的“科学战争”,或“斯大林主义民主的游戏”。当时每个学科都进行了长期的、旷日持久的内部和公开辩论,以便协商出一个在政治上适时的、在科学上有前途的研究框架,并作为党的路线予以颁布38。这些争论的典型特征是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这些争论是在苏联与其前西方盟友之间迅速发展的冷战背景下进行的。对可疑的西方权威的“顺从”,不加批判地接受据称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或不加辩证的“唯心主义”或自愿主义的研究概念,是科学家可能面临的最严重的指控。遗传学和控制论作为伪科学被禁止,以及特罗菲姆-李森科臭名昭著的拉马克主义的确立,都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这些关于如何将科学概念化的外部冲突,加上内部关于审美形式的分歧,导致了长期的冲突和误解。这种情况是如此极端,以至于文化部长安德烈-日丹诺夫在1946年8月对作家安娜-阿赫玛托娃和米哈伊尔-佐夫琴科进行镇压,并封禁《列宁格勒》和《兹韦茨达》杂志(从而启动了“日丹诺夫时代”,这是一个在文化领域施加极端政治压力的时期)。这并没有改变基本的问题,而只是加剧了“纯文艺化幻象”所面临的“失败和错误”。结果,半年前还被赞誉为具有开创性并被提名为斯大林奖的小说或故事,往往突然被批判为“顺从”资产阶级的科学观念,“客观上是反革命的”39。
但渐渐的,持续不断的内部争执导致了一小批年轻作家和记者的崛起,他们在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文艺政客的支持下,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 vydvizhentsy——在斯大林技术情报统治下的“成就者”——在193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往往有在科研实验室和机构的工作经验。战后,他们不仅加入了作协,而且开始逐步为《文学报》或《共青团员报》等有影响的报纸、《星火》等流行的插图期刊,以及《环球》或《知识就是力量》等大众科学期刊工作。尼古拉-托曼、瓦迪姆-奥霍特尼科夫、维克多-萨帕林、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维克多-西廷、奥列格-皮萨尔热夫斯基和亚历山大-卡赞采夫等都是这样的作者,他们都出生于1905年至1916年之间。
1947年底,在作协秘书处的帮助下,这个小组通过了委员会的新章程,旨在将各种科普作品以及科幻作品归入“富有诗意”的“科幻文艺”概念之下。新章程宣称,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为提高不同文学体裁作品的思想内容、教育价值和艺术水平而斗争。”40因此,根据这一教育目标,传统的科普以及苏联科学幻想(nochnaia fantastika)受到了攻击,因为它们忽视了科学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助长了科学的“庸俗化”41。正如该流派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娱乐性和悬念性的手段常常作为一种“危险的偏离”,旨在掩盖意识形态的无知和“非科学的方法”,而作家们必须认真考虑他们“以谁的名义”写作42。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读者被视为被动的顾客,他们不加批判地认同文字,并有可能模仿所提供的一切。因此,如果向他们提供“一流的”纯文艺作品,“每一个苏联人,无论是知识分子、工人、民工、年轻人、成年人还是老年人”,都会阅读这些文学作品,这是理所当然的43。
新章程的思想内容对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具有核心意义,因为它把矛头指向了各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和把科学说成是聪明的“怪人”或疯狂科学家的创造物44。这种新的思路使亚历山大-波波夫斯基的《受启发的探索者》(1945)和《以人的名义》(1948)、列夫-古米列夫斯基的《俄国工程师》(1947)和《技术大师》(1949)以及亚历山大-多甫仁科的“愚蠢”电影《米丘林:盛开的大地》(1948)等传记专著受到严厉批评45。在冷战开始的背景下,科学领域“俄罗斯优先”(russkoe pervenstvo)的主张加剧了“思想之战”。这种爱国-民族的话语在所有学科中占主导地位,是战后出版物与30年代战前类似出版物的主要区别。战前一般不存在这类话语,但现在甚至建立了新的书系,如关于革命前探险家的“俄罗斯旅行者”,或像《俄罗斯科学的灵魂》(1948)和《俄罗斯优先的故事》(1950 年)这样的集合书系46。这种话语旨在发明一种专属俄罗斯的科学传统,并与俄罗斯成就的永久“纯文艺化”齐头并进,同时降低了所有自然或可能的科学障碍。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面对反动的沙皇帝国,在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热情支持下,为科学进步而奋斗。但面对帝国官僚机构束缚的学术代表,他们却无能为力。他们的斗争在1917年以后才得到正式承认,他们斗争的遗产终于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在得到了实现。
新章程中最不明确的部分是它要求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起初,一些评论家提议将科学工业题材的小说纳入这一类型,如瓦西里-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1946-48)。但人们逐渐同意,一部作品的“艺术主宰”(khodzhestvennoe masterstvo)应该包括虚构元素和科普元素的融合47。传统上,科普的目的是展示科学进步如何改变我们对自然和人类的理解,相比之下,科学文艺将揭示俄罗斯科学不变的“灵魂”,从而揭开自然规律的神秘面纱,并使之发生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不再包含任何未解的秘密或非凡的发现,而只是一个被人类无所不能的殖民对象。伊维奇在1930年代将科学文艺定义为“发明的冒险”,因此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典型的科学“预测”(predvidenie)的俄罗斯能力48。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人们可以把这种转变概括为以下几点。旧有的“娱乐化”科普被指责为“庸俗化”,主要是在修辞上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而科学文艺则大体上否定了科学研究的所有复杂性和实验性,而强调其远见卓识的成分和思想上的“真实性”。这样一来,这一文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与虚构(或艺术)的关系:以往强调普及科学的权威性被抛弃,转而强调虚构的艺术性,借助于科学活动的“纯文艺化”,虚构将传达出科学努力的简单伟大和可以理解的真实性49。
到了40年代末,根据科学文艺委员会新章程的要求,随着斯大林主义后期“科学战争”的结束,这一文体终于可以宣布它的第一次成功。1948年秋,斯大林宣布了“重建自然的计划”,促进了对按照委员会章程写作文学作品的政治要求的加强。于是,从1948年起,非虚构类图书开始获得国家小说界的最高奖(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斯大林奖,将这类作品归入“科学文艺”体裁的范畴,使这一举措成为可能。有一次,连续有三篇“科学文艺”作品获奖。尼古拉-米哈伊尔沃斯的《在祖国的地图上》(1948)、瓦迪姆-萨福诺夫的《盛开的大地》(1949)和玛丽埃塔-沙吉尼安的《苏联亚美尼亚旅行记》(1950)。
从此,科学文艺被正式确认为严肃的、一流的文学作品,连《新世界》和《红星》这样“厚重”的文学期刊也开始刊载这类文学作品50。然而,这些作家越是成功地将科学文艺文本确立为关于科学与社会、未来技术发展和俄罗斯科学大师的专属写作方式,最初的前卫的、革命的、创造实质上新的“虚构性”科学诗学的冲动就越是消退。
可行性的幻象:斯大林主义晚期的科学小说
由于斯大林主义后期的紧张气氛,科学文艺类型的作品没有由受过科学教育的参与者、观察者写出想象人类未来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的“激动人心”的新故事,而是顽固地坚持教条式地粉饰二战后试图重建的灾难性国家所面临的灾难性问题。这一文体没有形成对现实的“新认知”,而是变成了(斯大林主义)当下的逃避主义梦工厂。众多的小说、故事和文学素描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的田野”,描述了一个被毁坏得无法辨认的“新地球”,描述了科学集体利用新发明的研究仪器开辟新的“通往深处的道路”,揭示自然界最后的秘密51,正如维克多-萨帕林所写的短篇小说《柔娅-维诺格拉多娃的一天》(1948)中的女主人公热情洋溢地说道:
他们来了,苏联技术的代表,新一代的工程师!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行的。一切都是技术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把几十个自来水厂的控制系统自动化,强迫汽车听从人类的声音——只要目的明确,能把人类从机械的劳累中解放出来,把他们解放出来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一切都可以做到。52
这种对技术和科学进步的无限可能性的热情,就是这种俄罗斯优先的新科学文艺诗学以及为共产主义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下真实的科学活动的核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任何一丝明确的对战后饥荒,对被破坏的工农业基础设施,或对因战争和古拉格而遭受创伤的人民的现实性的提法,都被扑灭了。
这种斯大林主义的科学诗学,在解冻时期被定性为对现实的“虚饰”,最典型的、影响极大的代表是弗拉基米尔-涅姆佐夫。涅姆佐夫是专业的无线电技术工程师,他在1920年代成为无产阶级文化诗人,然后成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热心追随者,之后他开始在阿列克谢-加斯特夫著名的中央劳动研究所工作53。在30年代和战争期间,他注册了大约20项无线技术专利,1946年他进入作协。在斯大林时代后期,他每年至少出版两本书,发行量非常大。但斯大林去世后,在解冻时期,涅姆佐夫的大量科幻小说被认为写得太差,太无聊,以至于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只有一个人真正读完了他的小说,那就是在科幻小说领域以读过所有东西而闻名的人——根里奇·阿奇舒勒,他以根里奇·阿尔托夫的笔名发表小说。因而在解冻时期,涅姆佐夫也就作为当时所谓的“眼前目标的幻想”(fantastika blizhnego pritsela)的典型例子而闻名,这是专门描述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科幻小说,其中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梦幻前景。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小说,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小说确实读起来很累——一般来说,所有晚期斯大林主义的小说都是如此——涅姆佐夫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给虚构的科学现实涂上装饰的。例如,他的小说《仪器“SL-1”》在1947年至1951年期间出版了四版54。小说以乌拉尔山为背景,描写了年轻的工程师们正在建造一种“嗅觉增强器”,可以远距离“闻到”稀有金属的味道55。虽然他们未能在山下发现任何抢手的金属,但他们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个叫奥梅金的孤独科学家,他用塑料材料做实验,并用塑料给自己盖了一整栋房子56。奥梅金自称是“塑料时代”(vek plastmassy)的“发烧友”,他坚信这个时代将取代现在的“钢铁时代”57。他盛赞塑料材料,因为它们可以随意成型、提炼、固化、变得有弹性。他向惊奇的年轻工程师们展示了他的塑料房子,它没有尖锐的边缘,稳定、不锈、完全透明。但它的墙壁可以随意变色,温度可以任意调节58。同时,这位科学家还在用超声波进行实验,以改变不锈钢的分子结构,或改变房子墙壁的物质和颜色,使它们不再漂白和老化。以这样的方式,他把当地的文化馆改造成了一间名副其实的奇迹之室59。
这段简短的情节概括已经暗示了涅姆佐夫作品中具体的“科学文艺”特征。首先,孤独的科学家奥梅金这个姓氏在俄语中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一下子让人联想到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高尔基认为,这个文学英雄代表了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典型现象——“多余的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对他来说,生活似乎是狭窄的,他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是多余的,他在其中为自己寻找一个舒适的位置,但没有找到,于是受苦、死亡,或与对他充满敌意的社会和解,或沉沦于醉酒或自杀。”60同时,“奥梅金”这个姓氏暗指希腊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欧米茄”。因此,如果这篇短篇小说也在形象意义上涉及斯大林政权的阿尔法和欧米茄,那么,奥梅金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科学文艺”诗学的某种死胡同,或者至少是与它的美好未来相去甚远。

《叶甫盖尼·奥涅金》▲
而且,发明即将到来的“塑料时代”的所有奇迹的不是热情洋溢的青年工程师集体,而是孤立无援的科学家,而科学家又反过来激励着青年。此外,小说将背景设置在西伯利亚乌拉尔的森林地区,也可能暗示了古拉格制度的遗址,被流放的科学家的形象也是如此,他过着孤僻的生活,不喜欢谈论过去,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乐观精神。
主人不想回忆过去, 我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向我提到了一个最大的研究机构的名字, 在那里进行着复杂的新型建筑和内衬材料的研究,我们的经济需要这些材料。
“唉,我们的年轻人啊!” 奥梅金叹息着说,“我真羡慕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乐观精神。生活是美好的,科学是光明磊落的,看到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俗话说:‘你还没被油炸的公鸡啄过呢’。”他打了个寒颤,好像不想记起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但他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他继续说下去,笨重地坐在一张细长的椅子上。61
奥梅金的主要科学激情——一个新的塑料时代的开始,它将取代现在的钢铁时代——也可以被解释为对要克服的“斯大林时代”的直接暗示,而同时他的透明塑料房子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主义科学”的矛盾隐喻,这一概念在“科学战争”中已经形成、完善、固化、变得有弹性,并根据需要改变颜色62。
但塑料不仅是一种可塑性极强的材料,如透明房子的形状所示,它可以随意变色和调温。“塑料时代”还暗指斯大林主义后期试图完全观察、控制和监视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奥梅金本人——以他个人的挫败感和职业热情——让人联想到所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古拉格的科学家。而在暗指普希金的《奥涅金》时,他也暗示了所有以前热心于社会主义计划的作家和支持者,他们在大恐怖中被谋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尽管他们常常试图按照当前的政治路线来调整或“塑造”自己。其中包括如瓦尔拉莫夫这样的作家。
在涅姆佐夫的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到的,正是这种矛盾的隐喻底色,即使是最守成的作品也贯穿其中。换句话说,他们强调的透明性、可行性和集体性到最后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文艺概念的根本失败。
结论
1930年代初,随着RAPP和1920年代所有其他文艺运动的解散,人们开始使用科学艺术文学一词。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高尔基和马沙克等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家普及了“科学文艺”的概念,认为这是调和现代主义、前卫主义的科学革命梦想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梦工厂”设想的最全面的方法63。“科学文艺”这个词承诺不仅容纳前卫运动的内容,而且容纳它们的几种艺术形式和文学手段。但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都没有真正接受这一流派,所以它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既定的、有效的普及科学或普及科幻小说的方式,它最终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从1934年底到1936年初。
但在战后时期,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这个词却得到了惊人的复兴。特别是在1948年到1953年之间,人们试图用这个词语形成一种新的自力更生的文学流派,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奠定了斯大林主义晚期关于一个没有冲突、以俄罗斯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的完美愿景。但正如涅姆佐夫的《仪器“SL-1”》所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一时期最终实现了官方科学话语的基本统一,但即便是这一文体,也透露出斯大林主义晚期科学文化内部深深的矛盾不安。尤其是主人公的形象和他的科学发明,暗示了在光鲜的科学文艺表面下潜藏的暴力和压抑的现实。
所有关于科学新诗学的讨论,所有关于它的概念,以及所有归于它的著作,在后斯大林时代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所谓的解冻迎来了一种基于控制论、宇宙论和系统论的新的科学热情。在这个据称“医生受到尊重”而“词人受到忽视”的新时代,科幻小说这一类型经历了惊人的复兴。又或者“科学文艺”干脆就被丢弃了,许多以前支持那种“科学新诗学”的人们仍然积极地参与大众科学和小说的出版工作64。但是,当 C.P.斯诺宣称西方的《两种文化》(1959)——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时,苏联却在进行跨学科的努力,以期振兴“科学艺术文学”这一文体,使之成为一种“思想的戏剧”,一 种“对知识的科学追求,一种缺乏历史和个性的无人区”65。达尼尔-达宁是这一短暂重生的最著名的倡导者。1960年,他出版了关于现代物理学的纲领性畅销书《陌生世界的必然性》, 并在同年发起出版了年鉴《通往未知世界的道路》66。尽管该期刊能够持续四十年,但其24卷的内容从未在不同学科之间或科学爱好者圈子之外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的讨论论坛。相反,它往往只是复制了斯大林主义前辈们的许多“纯文艺化的幻想”而已67。
注释及参考文献
1.Varlam Shalamov, “O moei proze” (1971), in his Vse ili nichego: Esse o poezii i proze (St. Petersburg, 2015), 115–42.
2.Varlam Shalamov, “Nauka i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Front nauki i tekhniki, 1934, no. 12:84–91), reprinted in his Vse i nichego: Esse o poezii i proze (St. Petersburg 2015), 51–84.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translations are by the author.
3.遗憾的是,从 1930 年代开始,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传记资料,也没有关于他从事科幻文学的思想和动机。即使是几十年后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少数自传性声明,也没有提到这个话题。这就更令人遗憾了,因为这种所谓进步的 "新文体",也可以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大工地和古拉格集中营中强迫劳动的残酷现实的一种隐瞒和粉饰。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在 1934 年编辑的《别洛莫尔运河》集体卷,许多以前的前卫作家都参加了这一卷。追溯“科学小说文学”与古拉格之间的这种奇特关系,需要单独写一篇文章。关于沙拉莫夫,见Franziska Thun-Hohenstein, “Remembering the Gulag: Varlam Shalamov’s Poetics of Speaking and Being Silent,” in Filologia, Memoria e Esquecimento, ed.Fernando Mota Alvas et al. (Braga, Portugal, 2010), 71–95. On Gorky’s collective volume see Cynthia A. Ruder, Making History for Stalin: The Story of the Belomor Canal (Gainesville, 2003).
4.See, for example,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9); and John E. Bowlt and Olga Matich, eds., Laboratory of Dreams: The Russian Avant-Garde and Cultural Experiment (Stanford 1990).
5.鲍里斯·葛罗斯从根本上挑战了这种解读,将斯大林主义描述为所有前卫梦想的实现。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颠倒了常见的概念,却没有对复杂的转变给出更深入的见解。See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Avant-Garde, Aesthetic Dictatorship, and Beyond (London 2011).
6.Catriona Kelly, “New Boundaries for the Common Good: Science, Philanthropy, and Objectivity in Soviet Russia,” in Constructing Russi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880–1940, ed. Catriona Kelly et al. (Oxford 1998), 238. See also James T. Andrews, Science for the Masses: The Bolshevik State, Public Science, 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4 (College Station, 2003).
7.See Grigorii Mishkevich, Doktor zanimatel'nych nauk: Zhizn' i tvorchestvo Iakova Isidorovicha Perel'mana (Moscow 1986); and Boris Liapunov, “‘Zavtrak v nevesomoi kuchne’: Posleslovie,” Iskatel', 1962, no. 3:157.
8.See Boris Liapunov, V mire fantastiki: Obzor nauchno-fantasticheskoi i fantasticheskoi literatury, 2nd ed. (Moscow 1975), 49–50; and Andrews: Science for the Masses, 86–87.
9.Matthias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Sowjetische Abenteuerliteratur und Science Fiction von der Oktoberrevolution bis zum Ende der Stalinzeit (Cologne, 2014), 242.
10.Eleonora A. Lazarevich, Iskusstvo populiarizatsii: Akademiki S. I. Vavilov, V. A. Obruchev, A. E. Fersman
– Populiarizatory nauki (Moscow 1960), 62–109.
11.See Nikolai Krementsov, Revolutionary Experiments: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in Bolshevik Science and Fiction (New York, 2014); James T. Andrews, Red Cosmos: K. E. Tsiolkovskii, Grandfather of Soviet Rocketry (College Station, 2009); Michael Hagemeister, “Konstantin Tsiolkovskii and the Occult Roots of Soviet Space Travel,” in The New Age of Russia: Occult and Esoteric Dimensions, ed. Birgit Menzel et al. (Munich, 2012), 135–50; and Igor J. Polianski, “Das Unbehagen der Natur: Sowjetische Populärwissenschaft als semiotische Lektüre,” in Laien, Lektüren, Laboratorien: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 in Russland 1860– 1960, ed. Matthias Schwartz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2008), 71–113.
12.Joseph Bristow, Empire Boys: Adventures in a Man’s World (London 1991); Martin Green, The Adventurous Mal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hite Male Mind (University Park, PA, 1993); John Rieder, Colon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2008).
13.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i)或叶夫根尼·扎米蒂(Evgenii Zamiatin)在 1920 年代的早期讽刺和反乌托邦作品,也必须局限于这种常见的冒险科幻小说和娱乐性科普作品,并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处理。See Yvonne Howell, “Eugenics, Rejuvenation, and Bulgakov’s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Dogness,” Slavic Review 65:3 (2006): 544–562; and Matthias Schwartz, “Das Ende von Petersburg: Utopie und Apokalypse in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des Fin de Siècl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1 (2015): 982–1000.
14.最著名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写的一部革命前小说《红星》(Krasnaia zvezda,1908)。这部小说被布尔什维克赞誉为典范,只是在 1920 年代末,由于作者在普罗列特库尔特组织中的作用和他与尼古拉-布哈林的关系密切,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才沦为耻辱和遗忘。其他部分乌托邦小说,如Iakov Okunev 经常被引用的小说《即将到来的世界》(Griadushchii mir,1923)或Vadim Nikol'skii 的《一千年》(Chereztysiachi let,1927)从未在大的科学大众杂志上发表,几乎没有任何公众影响。关于波格丹诺夫小说的矛盾性,见 Phillip Wegner, Imaginary Communities: Utopia, the Nation, and the Spat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 (Berkeley 2002);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182–85; an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167–89.
15.Polianski: “Das Unbehagen der Natur,” 79.
16.See Margarete Vöhringer, Avantgarde und Psychotechnik: Wissenschaft, Kunst und Technik der Wahrnehmungsexperimente in der frühen Sowjetunion (Gottingen 2007); Boris Gasparov, “Development or Rebuilding: Views of Academician T. D. Lysenko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 Avant-Garde,” Laboratory of Dreams, 133–50; Barbara Wurm, “Factory,” in Revoliutsiia! Demonstratsiia! Soviet Art Put to the Test, ed. Matthew S. Witkovsky and Devin Fore (Chicago 2017), 218–25; an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145–64.
17.Schwartz: “How ‘Nauchnaya fantastika’ Was Made: The Debates About the Genre of Science Fiction from NEP to High Stalinism,” Slavic Review 72:2 (2013): 224–46.
18.据此,高尔基在《关于主题》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形象化的科学文艺思维”的新方式,这在 1933 年 10 月就已经开始了。See Vsevolod A. Revich, “Nauchno-khu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vol. 17 (Moscow 1974), 203–4. At first, Gorky and Marshak still used the attributes “scientific-fictional” or “fictional-scientific” randomly (Schwartz, Expeditionen, 292–303).
19.因此,马沙克和高尔基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多年前针对传统儿童文学,特别是针对童话类型的论点,指责童话不世故,使年轻读者远离现实。现在,两位作家又重复了这样的指责,反对科普中的发明世界和科幻小说中的梦幻逃避主义(nauchnaia fantastika)。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围绕儿童文学的争论,见 Marina Balina and Larissa Rudova, “Introduction (Special Forum Issue. Russ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Changing Paradigms),”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49:2 (2005): 186–98.
20.Samuil Marshak, “Sodoklad S. Ia. Marshaka o detskoi literature,” Pervyi vsesoiuznyi s''ezd sovetskikh pisatelei 1934: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1934), 31.
21.更多细节见 Schwartz, Expeditionen, 292–303.
22.Marshak, “Sodoklad S. Ia. Marshaka o detskoi literature,” 20–38.
23.Boris Liapunov, M. Il'in: Kritiko-biograficheskii ocherk (Moscow, 1955), 74.
24.马利克出版社在 1932 年出版了约翰-赫特菲尔德设计的该书版本,书名为 Fünf Jahre, die die Welt verändern[《震撼世界的五年》],显然是对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畅销书《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的戏仿。见 M.伊尔金[Il'in],Fünf Jahre, die Welt verändern:Erzählung vom großen Plan(柏林,1932)。英译本以《新俄国的初级阶段:五年计划的故事》(波士顿,1931)出版。
25.据此,他以下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有类似的书名。《山与人:改造自然的故事》(Gory i liudi:Rasskazy o perestroike prirody, 1935);《物的故事》(Rasskazy o veshchakh,1936),是一本早期小册子的修订集;《机器的故事》(Rasskazy o mashinakh, 1949);《你周围的故事》(Rasskazy o tom,chhto tebia okruzhaet,1953);《作为建设者的人民: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故事》(Narod-stroitel': Rasskazy o piatom piatiletii,1955,遗作)。关于伊尔英的文学生涯,详见Matthias Schwartz, "Factory of the Future: On M. Il'in's 'Scientific- Fictional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103-5 (January-April 2019): 259-81.
26.Aleksandr Ivich, Prikliucheniia izobretenii, 2nd rev. ed. (Leningrad, 1935), 111–16.
27.Ibid., 117–26.
28.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402–16.
29.Marshak, “Sodoklad S. Ia. Marshaka o detskoi literature,” 34.
30.Mikhail Ia. Lapirov-Skoblo, “Rech' prof. M. Ia. Lapirov-Skoblo,” Pervyi vsesoiuznyi s''ezd sovetskikh pisatelei 1934, 435.
31.See Aleksei Tolstoi, Fedor Gladkov, Valentin Kataev, Nikolai Aseev, Ianka Kupala, Ivan Evdokimov, Panteleimon Romanov, Vladimir Bill'-Belotserkovskii, Mykola Bazhan, and M. Il'in, “Otvetnoe slovo pisatelei nashei strany (anketa ‘bor'by za tekhniku’),” Bor'ba za techniku 17–18 (1934): 9–15.
32.造成这种不感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科学文艺”这个名词按理说应该把以前低端的、二流的科普文体提升到真正的高端文学的高度,但大多数作家还是认为它不值一提。除此之外,因有关其任务和形式的激烈论争,以及对“一五计划”期间围绕科幻和科普的争论的回忆,都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33.Lev Gumilevskii, “Spiski knig vmesto izdatel'skikh planov,” and M. Il'in, “Zamechaniia k planu Detizdata,” both in Detskaia literatura 2 (1939): 53–59 and 51–53, respectively; Aleksandr Ivich, “Viktor Shklovskii v detskoi literature, “ Detskaia literatura 3 (1939): 54–58.
34.For more detail see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331–40.
35.Lev Gumilevskii, “Neumiraiushchaia fantazma,” Detskaia literatura 8 (1939): 22.
36.Ibid.
37.在 1951 年 3 月的一次内部辩论中,作家格奥尔基-图什坎是这样描述该委员会的(Schwartz,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567)。
38.See Alexei Kojevnikov, “Games of Stalinist Democracy: Ideological Discussions in Soviet Sciences, 1947– 52,” in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 ed. Sheila Fitzpatrick (London, 2000), 142–75; and Ethan Pollock, Stalin and the Soviet Science Wars (Princeton, 2007).
39.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518–28.
40.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literatury i isskustva (RGALI), f. 631, op. 15, ed. khr. 816, l. 86.
41.Vasilii Zacharchenko, “Za vysokoe kachestvo knig po istorii nauki i tekhniki,” Pravda, July 11, 1951, 2.
42.Ibid. 另见奥列格-皮萨尔热夫斯基在关于科学文艺委员会方向的内部报告, RGALI, f. 631, op. 15, ed. khr. 787, l. 5.
43.根据瓦季姆-萨福诺夫在他的 "苏联科学-小说文学 "概念化中的说法,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23, l. 26.
44.Viktor Sytin at an internal discussion in May 1949, 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23, l. 61.
45.See Zakharchenko, “Za vysokoe kachestvo,” 2; 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18, ll. 5–6; Ibid., f. 631, op. 22, ed. khr. 43, ll. 1–108.
46.这套丛书由地理文学出版社 Geografizdat 于 1947 年建立,收录了N.N.Mikliulkho-Maklai(1948 年)和俄罗斯人类学家I.I.Babkov 的Po Afrike(1949 年)等科学旅行家和环球旅行者的传记。See also I. V. Kuznetsov, ed., Liudi russkoi nauki: Ocherki o vydaiushchikhsia deiateliakh estestvoznaniia i tekhniki, 2 vols. (Moscow, 1948); and V. Bolkhovitinov et al., eds., Rasskazy o russkom pervenstve (Moscow, 1950).
47.见 1951 年 4 月关于该流派进一步发展的内部讨论,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42, ll. 92–98.
48.在战后的文章中,伊维奇仍然保持着对“发明”艺术的兴趣,但现在他把它重新解释为心灵预测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能力。See Aleksandr Ivich, “Predvidenie,” Znanie – sila 7 (1948): 1–4.
49.关于这些复杂的、部分矛盾的转变,详见 Polianski,"Das Unbehagen der Natur",92.
50.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23, ll. 19–23, 35–36.
51.See Aleksandr Kazantsev, “Na poliakh Kommunizma,” in his Mashiny polei Kommunizma: Rasskazy o mashinakh, ikh sozdateliakh i komandirakh (Moscow, 1953), 192–208; Viktor Saparin, “Novaia planeta” (1949), in his Novaia planeta: Nauchno-fantasticheskie rasskazy i ocherki (Moscow, 1950), 3–17; Vadim Okhotnikov, Dorogi v glub' (Moscow, 1950); and idem, V mire iskanii: Nauchno-fantasticheskie povesti i rasskazy (Moscow/ Leningrad, 1952).
52.Saparin, “Den' Zoi Vinogradovoi,” in Novaia planeta, 18–70, esp. 69.
53.有关Nemtsov 的传记请参见 Genadii Prashkevich, Krasnyi sfinks: Istoriia russkoi fantastiki ot V. F. Odoevskogo do Boris Shterna (Novosibirsk, 2007), 391–407. See also 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5, l. 50.
54.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593–608.
55.Vladimir Nemtsov, “Apparat ‘SL-1’” (1947), in his Nauchno-fantasticheskie povesti (Moscow, 1951), 427–565.
56.Ibid., 446–65.
57.Ibid., 465.
58.Ibid., 465–79.
59.Ibid., 541–53.
60.Maksim Gorky, “Soviet Literature,” in Problems of Soviet Literature (by Andrei Zhdanov and others at the Soviet Writers’ Congress 1934), (Leningrad, 1935), 25–69,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orky-
maxim/1934/soviet-literature.htm.
61.Nemtsov, “Apparat ‘SL-1,’” 471. "ne kleval vas zharenyi petuch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 "你至今没有任何不便"。
62.埃拉娜-戈梅尔曾对阿卡迪和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在六七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中类似的文学策略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某种“审查的诗学”,其中寓言和文字的解读交织在一起,不无问题。毫无疑问,它的一些特征已经出现在斯大林后期的作品中,比如涅姆佐夫的文本。参见Gomel, “The Poetics of Censorship: Allegory as Form and Ideology in the Novels of 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2 (1995): 87–105. 当然,透明的塑料房子也包含着对水晶宫的暗示, 如在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出现的薇拉-帕夫洛夫娜的第四梦。关于俄罗斯思想史上的这一符号, 也 可 参 见 Natalia V. Kovtun, “On the Ruins of the ‘Crystal Palace’ or the Fate of Russian Utopia in the Classical Era (N. G. Chernyshevsky, F. M. Dostoevsky, M. E. Saltykov-Shchedrin),” Journal of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7:4 (2011), 1045–57, available at journal.sfu- kras.ru/en/number/2433.
63.在这个意义上,伊尔因可以作为鲍里斯-格罗伊斯关于 "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艺术 "的论述的一个完美例子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Avant-Garde, Aesthetic Dictatorship, and Beyond [London, 2011].
64.Boris Slutskii, “Fiziki i liriki,” Literaturnaia gazeta, October 13, 1959. See also Loren R. Graham, Moscow Stories (Bloomington 2006); Matthias Schwartz, “A Dream Come True: Close Encounters with Outer Space in Soviet Popular Scientific Journal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in Soviet Space Culture: Cosmic Enthusiam in Socialist Societies, ed. Carmen Scheide et al. (New York, 2011), 232–50; and Slava Gerovitch, 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 (Cambridge, MA, 2002).
65."思想的戏剧性 "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个特征,被达尼埃尔-达宁引用为一个定义性的说法。参见Mark Kuchment, "Bridging the Two Cultures: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Prose,"in Science and Soviet Social Order,ed. Loren R. Graham(Cambridge,MA,1990),327。没有个性和历史(叙事)的科学散文的观念,直接指涉没有情节的散文的前卫观念和对事物传记的呼唤 (Schwartz, “Factory of the Future”)。
66.许多长期支持科学文艺的人都积极参加了年鉴。除达宁外,该刊编辑部还列出了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活动家维克托-西廷和斯大林奖获得者尼古拉-米哈伊洛夫,还包括奥列格-皮萨尔热夫斯基和古生物学家、畅销科幻小说作家伊万-叶夫雷莫夫。关于该期刊的出现和建立,详见库奇门:《弥合两种文化》,329-34。
67.因此,库奇门特提到了这一文体的三个显著特点:首先,它带有“苏联社会等级结构的印记”;其次,它关心的是“以有利的角度介绍科学”,而不是“批判性地评价科学现象”;最后,它“是苏联文化机构的一部分”,没有遇到任何“严肃的公众批评”。所有这些特点都已经是斯大林后期的特点(同上,339-40)。
作者:MATTHIAS SCHWARTZ 翻译:三丰(基于 DeepL 修订)原刊于The Russian Review 79 (July 2020): 4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