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裂痕 ——从《质数的孤独》和《我的天才女友》谈起

绿逸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意大利当代文学的魏怡副教授指导,高如老师协助修改文稿,参加者是意大利语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旨在利用语言优势在中国推介、研究意大利现当代文学作品,并鼓励更多的读者在阅读中了解意大利的历史传统和当今生活。
《质数的孤独》和《我的天才女友》是两部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广受年轻人青睐的意大利当代叙事文学作品。它们从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的视角,剖析了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磨炼、创痛对于人物成长的影响,而人物的命运也折射出当代社会各种隐形的伤口。参加本次读书会的都是大学生,书中人物的经历引起了他们不同层面上的共鸣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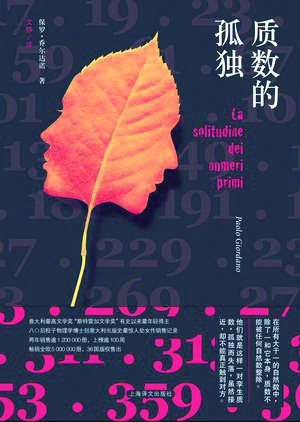
《质数的孤独》:“质数”式的孤独
@周卓靖:身体规训与无声反抗
正如福柯所言,身体的支配和使用方式与个人所在的权力关系息息相关,而传统哲学中追求塑造 “统一化”和“规范化”的人的思想大都会涉及对身体的规训。
爱丽丝和马蒂亚都生活在相似的亲子权力关系之中。儿童的话语、生命力、对身体的掌控、探索自我的欲望都被家长的专制和强权阉割。
爱丽丝的父亲每天强迫乳糖不耐受的她喝滚烫的热牛奶,让她学习滑雪,干预她的社交,训练她为自己打领带,反对她问问文身;马蒂亚的父母将他与天生智力缺陷的妹妹绑在一起,将他的身体囚禁在妹妹所在的时空之中。父权不假思索地试图规训弱者的身体。因滑雪事故而终身跛足的爱丽丝无法再实现父亲强迫她背负的期望,试图重新夺回对身体的掌控、文身、厌食、终身不孕。她的身体拒绝成为生殖的工具,也不愿意背负道德宣判的罪恶。马蒂亚弄丢了自己的双胞胎妹妹,切割掉了从在母亲子宫中就与自己共生的另一半,并不断地通过自残来抵抗回忆,宣示对自我的绝对控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摧毁身体为代价,在孤独中挣扎着夺回对身体的掌控权,在沉默中反抗父母的规训。
@黄兆梓:崩溃前的裂纹
“创伤”,是谈论这部作品时绕不开的概念,也是爱丽丝和马蒂亚走向“孤独”的原因。
若说“创伤”发生的那一刻,是一种彻底的崩坏,在此之前必定会有不断积攒的丝丝裂纹。书中爱丽丝的“裂纹”是为了获取认可而不断被动屈从,他人的期待支配着爱丽丝的所有行动。无论是在事故前或是事故后,她的成长一直都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她不断地吞下自己的不甘与厌恶,直到忍耐力达到极限的那一刻,一切轰然倒塌。马蒂亚的“裂纹”却是一种对自己的厌恶。在妹妹走失前,他厌恶的是“智障妹妹的哥哥”这个身份,而在亲手导致妹妹走失后,马蒂亚从对某个身份的厌恶发展为对整个自我的否定。这种厌恶感如影随形地贯穿着他的生活,迫使他推开所有人,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并在频繁的自我伤害中寻求解脱。
“创伤”作为“裂痕”的外在表现,往往贯穿着人的成长过程,与其说那瞬间的破裂导致了生活的不幸,倒不如说是隐秘的“裂痕”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成长的每时每刻。
@徐辰依:找寻自己与世界的距离
爱丽丝因腿部残疾而自卑敏感,因此尽力迎合他人的想法和标准。她想要奋力缩短自己与世界的距离,但乞求式的贴近带来了巨大的孤独感。对于自身之外的事物的过分关注,挤占了她认识自我的空间,也导致了她一次次的求而不得。
相反,马蒂亚由于童年妹妹的事故而封闭自己,对自我的陌生和恐惧使他一直与世界保持着过远的距离,他以切断一切情感诉求的方式使自己免受伤害,也使自己不再伤害他人。孤独恰恰是他为自己建造的牢笼,也是他为自己设定的惟一存在方式。
这两位孤独者相遇的结局虽称不上圆满,但也算得上是一种成全。他们的互相交错使他们最终找到了与世界相处的方式:马蒂亚不再一味拒绝世界,他在萦绕心头的无数亏欠和谅解之间选择了一种温情的疏离,一种柔和的我行我素;爱丽丝不再一味仰赖他人,她在不断地聚散离合之后意识到了自我的价值,学会了在孤独中获得圆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成长在最后一刻才完成。
@谭钰薇:孪生质数的孤独宿命
无穷无尽的数列上,两个孪生质数被两边无穷的数裹挟着,他们享受着自己孤独的舒适区,同时也在孤独的窒息中挣扎,二者被微妙的联系牵绊着,以免滑向失落数轴的尽头。他们特殊到与其他数字格格不入,特殊到没有别的因数能融入自己。
相似的不幸、相反的孤独牵住两线命运,在同样的自我折磨中打了一个无奈的结,亲密也以回避告终。两个主人公就像各自地平线上远远的恒星,遥望、爱慕的光亮到达彼此,却无法聚集能量,温暖孤独星球千疮百孔的地表,融化童年阴影与青年疼痛的秘密。
初读小说,常为二人的结局而惋惜,但后来觉得相比其间“爱情”联系,或怜惜之情,两个质数本身更重要。小说结尾留白很多,“爱丽丝躺在马蒂亚梦魇中的河里,心中不再有任何期待,只稍稍一使劲就自己站了起来”。我理解为这是女主人公对于孤独释然,不再期望其他因数参与自己的生命,也不再因孤独而惶惑不安。在此,焦点已不在于二人之间重新瓦解的联结,而在于个体的自我认识。“孤独”一词其实千差万别,“质数”的归宿无非是踏入属于自己的那一处孤独泥沼,在接受自己中自渡。
@喻儒辰:孤独的答案——因数“1”从何而来?
质数只有“1”和它本身两个因数。对于马蒂亚和爱丽丝而言,生活是植根于童年创伤的孤独乘以成长中的自我。
孤独是他们的公因数“1”,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沉淀发酵。爱丽丝的父亲对她有着极高的期望,尽管因为身体的伤残她终能抵抗父亲的权威,不再滑雪。但是父亲往日对她的苛责仿佛已经被她内化,她对自己伤残的身体执行下一轮的苛责:被认可的纤瘦身材,紧致的皮肤。马蒂亚沉迷于理性的数学计算和对秩序的追求,抗拒外部的世界,一切情绪化的、直白的、混乱的、不掩藏的、颜色鲜亮的都像他的“智障妹妹”一样,被他从童年开始就剔除出自己的生活。令人失望的世界,使得“1”的孤独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束缚,但也是心中惟一的绿洲。
然而遭遇相似的二人,却始终没能心灵相通。或许质数就是答案——因为孤独而特立独行,又因以孤独为底色在社会中成长而难以相聚。共有的童年创伤或许让刚刚相识的两人成为孪生质数,但当他们开启自己的人生,与不同的人、事、物交互,成为成长后的质数,如小说极具特色的质数编码一样,即使相邻也只能在若即若离中渐行渐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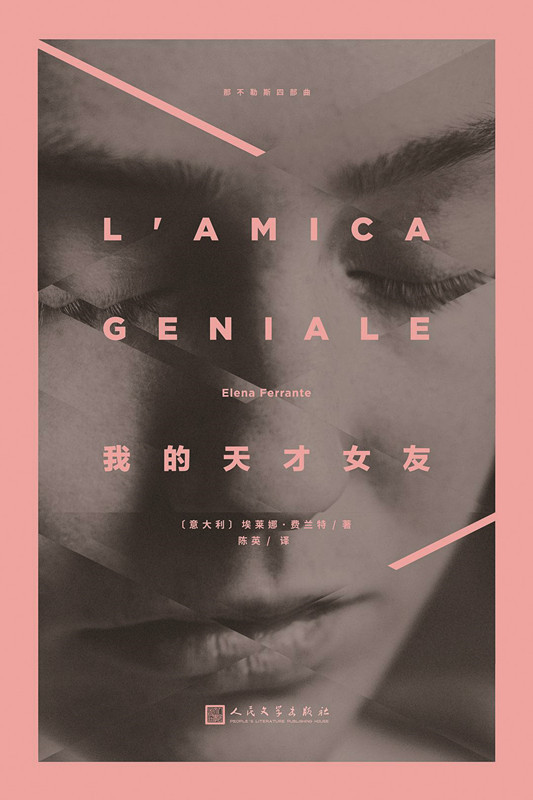
《我的天才女友》:那不勒斯平民女孩
@李李冰清:混乱与激情
美国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将“那不勒斯四部曲”誉为“一部恢弘的史诗,从最凄凉的环境中汲取出狂放的美”。其中作为开篇之作的《我的天才女友》讲述的绝不仅是两个女人的故事,而是如同一个大熔炉,汇聚了亚平宁半岛上近半个世纪的混乱、动荡与激情,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家庭暴力,接二连三的离奇谋杀,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另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风行一时的新现实主义,而这一切喧哗与骚动又反复诉说着这个时代的斗志与激情。
面对一幅纷乱而残酷的现实图景,两位出生在那不勒斯平民街区里的女性倔强地成长。她们的命运在传统束缚和时代变革的夹缝中几经沉浮。尽管意大利民众对自由、民主、进步的追求仍未实现,但包括女主人公在内的所有人,仍旧倔强地在一条未知的救赎道路上摸索前行。由此,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碰撞、纠缠。
@潘晨:“界限”的消失与形成
莉拉用“界限消失”来定义从童年过渡到青春期后对世界感知的变化。面对现实的伤害,童年的她呈现出一种接近“钝感”的抵抗力。个人与世界之间那种近乎自我保护机制的“界限”,保护了她的锋芒与理想。然而,面对哥哥的疯狂和丑陋,羞愧、厌恶、反感等情绪侵入莉拉的内心,界限彻底消失了,她身上那种无法用聪慧与天才遮掩的贫穷、虚荣与不堪也毕露无遗。这一切恰如戏剧舞台上的“第四面墙”,当它消融之时,原本在欣赏悲剧艺术的观众意识到人物的悲惨命运正在自己身上上演。无助与悲观的莉拉最终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
对于埃莱娜来说,界限是随着她接受教育而逐渐形成的。她和莉拉都渴望走出那个暴力的城区,出生的环境同样推动她去突破这个界限。她虽难以脱离自己所属的阶层,但能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冷静克制地描述 “庶民”的人生。作者在记叙时并未多费笔墨描述界限的产生与消失,却又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刘斯璇:亦敌亦友
如果说在《我的天才女友》中,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与方言都不得不让位于那些烦琐、真实的日常场景、并变成一种回音,那么那不勒斯更像是一位与埃莱娜和莉拉同等重要的主角。它是令人恐惧的:充斥着各种粗俗、肮脏和暴力;它也是混沌模糊的:美好与邪恶、理性与冲动、合法与非法交织,无数的碎片拼凑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中野蛮生长,形成一种混乱的美感。这种混乱将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滋生在其中的情感裹挟,而埃莱娜和莉拉则是稀有的觉醒者和行动者,试图实现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逃离。
然而,那不勒斯就像是两个女孩随身携带的一面镜子,她们借助它不断丈量自己、更新自己,但却永远无法遗弃它,因为这座城市的气息存留在她们的动作、语言甚至是每一段亲密关系里。很多年后,她们重新审视这里,选择接纳它、书写它。
那不勒斯,亦敌亦友,是想要抹去的出身,也是力量之源。就像费兰特在采访中提到的“那不勒斯是我的城市,即使我非常痛恨这座城市,我也无法撇开它”。
@张羽扬:成长中的“私人事件”与“公共事件”
《质数的孤独》精雕细刻了小说主人公成长中的“私人事件”。爱丽丝与马蒂亚如同“质数”所隐喻的那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寻求融入却难偿所愿,或封闭自我拒绝融入世界。共有的“孤独”让他们尝试走进,却也因拒斥沟通而无法一路同行。而《我的天才女友》则将意大利历史作为背景,展现了埃莱娜与莉拉如何“与世界一同成长”。以埃莱娜为例,她从那不勒斯的闭塞小镇出发,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成长历程中思考友谊、接受教育、经历恋爱、体味婚姻、组建家庭、反思人生。
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社会造成的。而埃莱娜在成长中不断寻找、模仿并以之为参照建构自我的对象往往是身边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天赋异禀、惊才绝艳的莉拉,她因父亲的“读书无用论”于小学辍学,却始终在反抗男权和父权的压制;还有时常令埃莱娜惊恐不已的母亲,以及文质彬彬的老师等。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方兴未艾,社会历史作为“公共事件”参与到小说人物的个人成长,也在每一个成长的故事中显现。在脱离这些形象以及所谓社会创造的“女性角色”标准的束缚之后,埃莱娜真正获得了自我,完成了主体身份建构。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21年2月26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