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与太阳》:人类社会的观察实验
“你相信有‘人心’这回事吗?我不仅仅是指那个器官,当然喽。我说的是这个词的文学意义。人心。你相信有这样东西吗?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
——《克拉拉与太阳》
《克拉拉与太阳》是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推出的首部长篇小说,近日在全球同步首发。小说以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视角切入,讲述在一个近未来的现代社会中爱与友谊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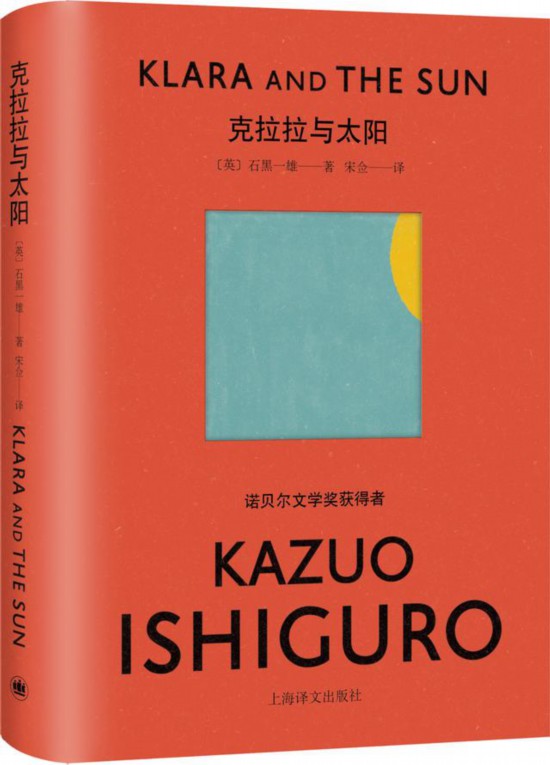
《克拉拉与太阳》中文版书影
什么是“人心”?
《克拉拉与太阳》一个重要主题是探讨什么是“人心”,即反思人类与机器人的真正区别。人类与机器人的差异仅仅是“人有情感,而机器人没有”这般简单吗?石黑一雄显然不认同这个观点。小说里的克拉拉在情绪感受与表达上,不仅与人类无异,而且有着比人类更为灵敏的辨析情绪的能力。那么,到底什么是“人心”?
小说在开始设置了一个疑团,让读者以为克拉拉到乔西家是来陪伴和照顾乔西的。但随着阅读的推进,这个目的变得越来越不纯粹。我们先是发现乔西身患一种极易致死的疾病,她的姐姐萨尔正是死于同一种病症;然后发现母亲为了不再失去乔西,秘密地委托卡帕尔迪先生制作乔西的仿真机器人。原来,克拉拉来到乔西家的真正作用是一旦乔西病亡,她将作为乔西的延续,满足家人的情感寄托。故事最后,乔西痊愈。克拉拉因此失去本应行使的功用,被丢弃在堆场。
克拉拉在堆场遇到了久别的经理,这是小说的结尾。克拉拉谈起自己被购买“延续乔西”的经历,同时指出卡帕尔迪先生的错误之处在于,“人内心中无法在机器人身上延续的地方不是在人的心里面,而是在那些爱她的人的心里面”。克拉拉最终认识到,她再怎么精确地复刻乔西,依然只是一台机器,她无法触及“母亲、里克、梅拉尼娅管家、父亲这些人在内心对乔西的感情”。乔西的家人或许可以把克拉拉当作乔西看待(他们也愿意这么做),但他们对乔西的独特感情不会重现在克拉拉身上。这是克拉拉无法取代乔西的根本原因。
“人心”是一种爱,他人的爱让我们变得独特。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观点,将人的存在放置到社会语境中思考。石黑一雄的观点似乎是,人是社会属性的动物,并非孤身一人存在于这个世界。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特殊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身份,正是“社会身份”塑造了这个人。这不是说一个人为他人而活,而是说他人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而爱这种东西只会落在人类身上,不会被赋予一台机器。
这让我想起日本导演北野武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说过的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这句话的意思是,死亡不该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每个活着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死去并不是从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中抹去一个数字这么简单,死会让爱他的人身负伤痛,并留下久远的影响。
人的身体可以复制,但爱永远独一。爱绵延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络。这是只有人类世界才有的现象,基于一种文明的理念。爱成了人与机器人之间本质的差别,同时我们对某个个体的爱通常无法被轻易转移。克拉拉对乔西也有爱,但这种爱建立在乔西对克拉拉的选择之上。如果选择克拉拉的不是乔西,而是别人,那么克拉拉衷心侍奉的对象便会另有其人。

石黑一雄
对人类世界充满温情的观察
《克拉拉与太阳》借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视角展开了一趟对人类世界充满温情的观察之旅。克拉拉作为进入乔西家的外来者,一方面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以及人在社会网络和人际网络中流露出的脆弱和无奈;同时,在与人类的交往过程中,借助人类的言说和举动,克拉拉也看到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内在世界。
乔西和里克玩泡泡游戏的时候,克拉拉观察到两人之间暧昧的情愫,属于青春期男孩与女孩特有的性萌动。但孩子的世界并非如表面上看起来那般简单与美好。某次谈话过程中,克拉拉敏锐察觉到里克因为画家给乔西画像(其实是卡帕尔迪先生为乔西做人体模型)而吃醋。乔西则向克拉拉抱怨里克不想长大,想和妈妈永远生活在一起,这是乔西无法忍受的事情。乔西也透露,当她没有按里克的意愿表现出任何想要长大的迹象,里克就会生闷气。
成人世界则是另一幅情景,遍地是失败的婚姻和破碎的感情。乔西的母亲和父亲分隔两地,很久才能见上一面;里克的母亲与父亲早已离婚,不再往来。对于母亲,克拉拉是一台绝佳的情绪接收器。母亲会向克拉拉抱怨乔西的不懂事——“孩子们有时候挺伤人的。他们以为只要你恰好是个大人,你就刀枪不入,怎么也不会受伤。”这些话,母亲只会跟克拉拉讲,因为她知道克拉拉只是一台机器,而不是真实的人。不过这不意味着克拉拉没有情绪,相反,克拉拉不仅与人一样有着各种复杂情绪,甚至有着比人类更强的情绪捕捉能力,能细腻地分析出人内心隐含的心理。
当克拉拉想从母亲口中知道乔西的姐姐萨尔死亡的原因,母亲指责她“没有权力好奇”,并用直白而伤人的话回绝了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克拉拉从中感受到了母亲的脆弱:萨尔的离世给母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痛,同时也让母亲忧虑乔西会因为同样原因离世。对克拉拉来说,萨尔的去世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没有避讳的必要。但对母亲(人类)来说,丧亲之痛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创痛,再加上乔西患上和萨尔一样的病症,很可能也会像萨尔那样离去,克拉拉的询问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经过这件事情,克拉拉明白了人心深处的脆弱,也懂得了应该怎样继续和人类交往。
认识到“人心的变化”是克拉拉的又一功课。在乔西与朋友的聚会上,克拉拉一眼看出乔西嫌弃她的心理。当小伙伴问乔西为什么不要一个B3(一种比AF更高一级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时,乔西说“现在我开始觉得我确实应该要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觉得克拉拉还不够完美。比之AF,B3除了增加有限的嗅觉,可能还有其他更高级的功能,这一点小说里没有特别说明。克拉拉从这句话中理解到乔西的真实想法,为自己可能被抛弃的命运而忧虑、难过。这件事让克拉拉回想起经理跟她说过的话,“孩子在橱窗前许下的诺言,却一去不回;更糟的是,他们回来了,却转而选择了另一个AF。”“变”是人性的一部分,克拉拉要慢慢懂得并适应。同时她也要懂得,很多时候人会隐藏真实内心,仅展示出自己好的、希望展示给他人的一面。这并不能简单判定为虚伪,而是一种人类的自我保护机制。
人心的变化也体现在乔西和里克的爱情关系上。在克拉拉看来,乔西和里克应该一起上大学,携手走完人生。由此她才会问里克,他对克拉拉的爱情是否是真的。两人的关系没有像克拉拉企盼的那样发展,乔西和里克最终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克拉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出于逃避孤独的愿望会采取复杂和难以揣摩的策略”,这是基于一种感性思维的反应模式,而非克拉拉与生俱来的理性占主导地位、并且总能做出“最优选择”的思维模式。
人与人之间并不能完全相互理解,这是事实,也是克拉拉观察到的人类世界的真相。究其原因,在于人有时不愿意或不可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克拉拉具有极强的共情能力,这使她能站在对方角度为对方考虑。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克拉拉是没有“自我”的,因为正是人的“自我”阻碍了人相互理解。
拟人化的叙述者
昔有夏目漱石以猫的视角观察人世(《我是猫》),今有石黑一雄借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视角观察现代社会。夏目漱石的猫视角以拟人的方式呈现,《克拉拉与太阳》的叙述者克拉拉在叙述主体状态上看似与人类无异,却又明显不同。克拉拉兼具人与机器的双重属性,她既能够像人一样感受和思考,又不会像人那般感性。克拉拉做出的决定总是依内定的程序,最有利于她侍奉的主人。小说最终在克拉拉的第一人称视角下,展现出一个复杂而充满温情的人类世界。
这种拟人化的叙述手法,是小说写作中常见的“陌生化”手法。“陌生化”是俄国文艺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什克洛夫斯基拿托尔斯泰的《量布人》为例说明“陌生化”。在这篇小说中,托尔斯泰以马作为叙述者,用马的眼光来观察私有制和人类社会。类似的例子还有,卡夫卡在《一只狗的研究》中以狗的视角叙述故事,《变形计》以甲虫的视角观察人类世界……这些小说不约而同地将叙述者设定为动物,用拟人的方式将动物人格化,再以动物的视角观察人类世界,从而赋予了人类世界一种“陌生化”的审美距离,打破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惯常认知,得以洞见现实隐藏的面向。
与此同时,我在阅读过程中也感受到克拉拉的叙述中有类似于法国小说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他的“新小说”创造的“零度写作”的味道。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也被称为“物本小说”,是一种模拟物的视角观察现实世界的小说。小说文本呈现出的效果类似于电影摄影机拍摄的效果。罗伯-格里耶说,“世界没意义也不荒谬,只是存在着”(《为了一种新小说》)。因此他描写物理空间的时候会精准地表达出几何位置。无独有偶,石黑一雄给克拉拉的观察视角设定了一种特殊的分格模式,这应该来源于对机器人特有视网膜形态的想象,这使克拉拉的观察具有了一种精确的空间感和几何性。比如下面这段:
“当公路从一格穿越到另一格时,我尽力保留其线条的连续性,但面对眼前不断变化的景象,我只能认输,任由公路在每次跨过边框的时候都先中断,再重启……太阳时常躲在云朵后面,但我有时看到它投下的图案跨越了整道的山谷或是大片的原野。”除了“我”的在场,《克拉拉与太阳》的叙述模式与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叙述模式差别不大。这是一种未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作用下变形的原初世界。
除了观察能力,克拉拉还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和情绪捕捉能力。当她观察得越多,经历得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扮演乔西助手的角色。她说,“我观察得越多,我能够获得的感情也就越多。”在行车去摩根瀑布的路上,克拉拉与母亲之间发生了一段对话。母亲羡慕克拉拉没有感情,但克拉拉否认了她的这一看法。由于一直按照设定的程序运作,克拉拉在感受到复杂情绪后并不会像人那样转化为出格的举动。而母亲因为创痛,对克拉拉的态度有时显得喜怒无常。从两人坐在瀑布下的咖啡馆,母亲让克拉拉扮演乔西的一幕能看出这点。一方面,她对两个女儿身患不治之症感到无力,有发泄的欲望;同时作为人,她又清楚不该对一台机器动怒。正是在本性驱动与规训制约的拉扯之间,母亲做出了别扭的举动,说出了奇怪的话。
克拉拉与人类最大的区别之一是没有私心。是否可以说,克拉拉才是更高级别的智慧形态?石黑一雄似乎将克拉拉当作完美的造物来呈现,他一方面借克拉拉的视角极为温柔地批判人性深处的纠结、自私和软弱,另一方面,并没有像其他刻画人工智能的小说那样为读者呈现一幅可悲可怖的近未来社会。这使得整部小说更像一则带着小说家美好愿望的童话。克拉拉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帮助乔西活了下来。虽然最终难免被投弃在堆场的命运(消费社会 “用完即弃”的逻辑),但她看起来不仅没有丝毫怨言,反而感恩与乔西一家度过的时光。这段结尾读来不免让人心生悲凉,我们还是会感慨,即便像乔西父母那样的好人,仍然有自私自利的一面。
近未来世界的核心仍然是人
《克拉拉与太阳》呈现了一个近未来的世界,虽然并未特意涉及,仍有不少地方都写到未来的新技术。克拉拉是一台有着学习能力的AF(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点不用说。在未来世界,人类能够通过购买人工智能机器人为生活带来便利。生病的孩子在家通过矩形板学习课程,这类似于疫情期间学生用平板电脑在线学习。小说里也提到基因重组技术在未来将帮助人类生下更完美的后代。里克因为没有使用这种技术,失去了一些入学机会。他只能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考入母亲心仪的阿特拉斯•布鲁金斯。还有街上的“库廷斯”(一种不知道何种功能的机器)制造着可怕的污染,也是对当下社会环境污染的隐喻。克拉拉认为“库廷斯”带来的污染遮蔽了阳光,妨碍人类接受太阳的滋养,从而消灭了其中一台。
未来世界依然会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一点在小说中也得到了呈现。乔西和里克显然属于两个世界。乔西的个人聚会上,里克受到乔西朋友们的冷落,他们玩不到一起,显露了两人的阶级差异。同时,即便里克天资聪慧,里克的母亲也不得不求助多年前伤害过的男人“开后门”。导致隔阂的还有移民的因素。里克一家是英格兰人,虽然小说没有明确表达,可以推测应该是从英国移民到当地的,这从里克母亲看起来“有些神经质,并不太受当地人的欢迎”可见端倪。阶级问题也间接影响了乔西和里克最终分道扬镳。
石黑一雄写作《克拉拉与太阳》的目的,看来并非反思人工智能的发展将给人类带来的隐患——不然他不会把克拉拉塑造为几近完美的形象——而是阐述人工智能如何能够抚慰人心,帮助人类度过因为自身的缺憾陷入的困境。《克拉拉与太阳》更像是一部乌托邦小说,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克拉拉善良、真诚,全心全意服侍乔西。克拉拉说,“我只想做乔西的AF,这就是我唯一的心愿。”这种完全利他的心理很大程度上源自小说家本人的表达诉求,小说因此弥漫着一层美好的温情,这一点在克拉拉祈求太阳为乔西带来“特殊的恩赐”这一情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克拉拉两次进入谷仓,进行一种类似于神秘宗教的特殊仪式,来祈求她心中的“神祇”太阳为乔西降福神恩。
《克拉拉与太阳》虽说是科幻小说,但科幻显然并非它的核心。小说里没有一般人工智能科幻小说中常见的对于人工智能“奇点” (Singularity) 的探讨。与其说石黑一雄创作了一部科幻小说,不如说他借用了科幻小说的形态,探讨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的话题:关于人的情感与记忆。
- 糖匪:评《克拉拉与太阳》[2021-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