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诞辰150周年|记忆可能是现代人的最后一束稻草
1929年,瓦尔特·本雅明完成了长篇随笔《普鲁斯特的形象》,以向他心中的偶像致敬。在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章中,目光如炬的德国作家开宗明义地写道:“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十三卷《逝水华年》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综合,它把神秘主义者的凝精会神、散文大师的技艺、讽刺家的机敏、学者的博闻强记和偏执狂的自我意识在一部自传性作品中熔于一炉。”接着,他直陈这部巨著在文体、结构和句法上的卓绝之处,并关键性地指出:“这部作品的创作条件是极不健康的:非同一般的疾病,极度的富有,古怪的脾性。在任何一方面这都是不可效仿的生活,然而它却整个变成了典范。”是的,我们必须知道,患有哮喘症、花粉过敏症、失眠症(神经衰弱)的普鲁斯特只能长时间躺在床上,回忆成为了他的存在方式——观察和呈现世界的方式。

普鲁斯特
可以说,没有疾病,就没有《追忆逝水年华》。一个略带残酷的现实是,同样是躺平,普鲁斯特却完成了文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
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
如同20世纪多部革命性的现代主义经典的命运——以毕加索《亚威农少女》(1907)、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1913)、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等为代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问世过程也颇为曲折。1913年秋,普鲁斯特数次找到好友加斯东·伽利玛,希望把《追忆逝水年华》交由他出版,但审稿人纪德很快就被两叠五百五十页厚的稿子和公爵夫人家没完没了的饭局弄得不胜其烦,明确表示拒绝出版。接着,普鲁斯特辗转多家出版社,最后只能选择自费出版。同年11月14日,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问世,反响热烈。纪德重读之后追悔莫及,主动写信给普鲁斯特道歉:“拒绝这本书将是伽利玛出版社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我这一生做过最后悔、最内疚的事。”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也没有人质疑《追忆逝水年华》的巨大成就。本雅明将它称为“过去几十年里文学的最高成就”。1954年,法国作家莫洛亚在为该书巴黎版作序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对于1900年到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没有比《追忆逝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英国文学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的评价更高:“《追忆逝水年华》像《恶之花》或《战争与和平》,是一百年间只出现一次的作品”。显然,这不仅是因为《追忆逝水年华》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篇幅巨大、规模宏伟(法文本15卷,中译本7卷,200多万字,以至于法国作家法郎士发出了著名感慨: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更重要的是,普鲁斯特这部不世出的小说发现了新的“矿藏”。
回顾20世纪的小说世界,其中的大部头比比皆是,但很少有新的启示录,大部分作者只是开发已有的众所周知的“矿脉”,而普鲁斯特开辟的却是新的“矿藏”。作为普鲁斯特的杰出前辈,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旨在描绘一个社会的全方位图景,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与这一注重外部世界和个人行动的悠久传统相并立,小说家们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逐渐从看得见的外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18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森凭借《帕梅拉》和《克拉丽莎》开启了小说探究人的内心生活之路,这一传统演变的高峰正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前者探索的是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后者探索的是更难抓住的现在的瞬间。
因此,普鲁斯特的小说对外部世界的素材选择并不在意,他感兴趣的不是观察外部世界本身,而是观察、思考和呈现世界的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普鲁斯特完成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所谓“哥白尼式革命”,指的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打破了地心说的神话,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只不过像是大海上漂泊无依的一叶孤舟,从而人也就被放逐出宇宙中心的位置。普鲁斯特的小说通过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重新发掘,使人的精神、人的记忆、人的情感、人的意识重新置于天地的中心,这是与哥白尼革命相逆相悖的。更重要的是,普鲁斯特的个人回忆具有普遍的人类学意义(每个人都能从普鲁斯特身上读到自己),以至于科学界出现了“普鲁斯特效应”这样的专有名词。
毫无疑问,普鲁斯特这一“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关键性武器就是回忆。回忆构成了“追寻失去的时光”的真正题旨,是普鲁斯特为自己确立的恒常的生命形式。它也是人类把握已逝时光的方式,而从整个人类的“类”的意义上,回忆正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翻开《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第一页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Longtemps,je me suis couché,de bonne heure)作为一部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的第一句,它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其实却隐含了许多内容。从手稿中人们发现,普鲁斯特在前后五年的时间里,曾尝试了16种写法才确定了这第一句话。多种疾病缠身的普鲁斯特必须适应这种长期卧病在床的生活,而他最终赋予了这种“躺平”的生活一种最好的方式:即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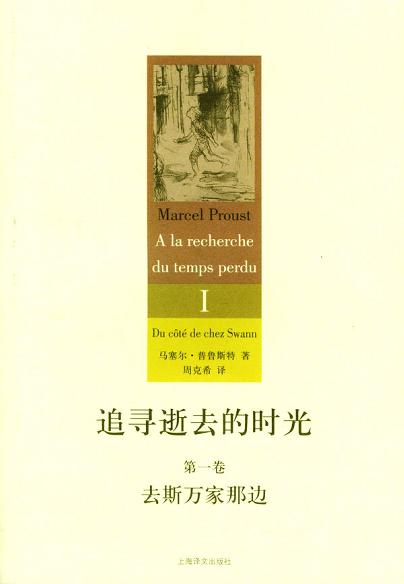
《在斯万家那边》
如同众多经典杰作的不同寻常的开头,普鲁斯特精心酝酿的首句同样意味深长,它一下子就奠定了“回忆”的主题,并向读者暗示,一方面是作为此在叙事者的“我”在回忆,另一方面,真正展开回忆的却是当初在失眠夜那段时间里的“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忆”既构成了生命的主题,也构成了艺术的主题。莫洛亚认为,《追忆逝水年华》的目标是呈现一个被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是的,不只是反映,更是歪曲,这与人的回忆的模糊性、多种疾病的作用、通感的影响等等因素密切相关,这就是其所隐含的人类学层面的空前丰饶的矿藏,它构成了普鲁斯特这部巨著最特殊的贡献。
往昔之井的召唤
法国评论家阿尔诺·当第幼写过一句非常精当的评论:“《追忆似水年华》是对往事的召唤,而不是对往事的描绘。”描绘更多是刻意的,单向度的;召唤则是非意愿的,双向的,是人与回忆在相互找寻对方。如果将整部《追忆逝水年华》看成一座巨型的华丽宫殿,那么它整个建筑在一个唯一的地基之上,那就是普鲁斯特本人所谓的“非意愿回忆”(mémoire involontaire)。当你无意中嗅到一缕芳香,听到从哪个角落飘来一串熟悉的音符,或是偶然翻到或触摸到一件旧物,便会突然唤醒沉埋在记忆深处的一段往事、一个场景或一种思绪。这些断片式的回忆纷乱芜杂,却又交织缠绕,如同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延绵不绝,好似一条语言的尼罗河,它泛滥着,灌溉着真理的国土。
这种“非意愿回忆”的偶尔开启乃是一个小小的奇迹,犹如那口“往昔之井”的光在某一刻突然直冲云霄,那种壮丽的内心景象让人久久无法平静。爱尔兰著名作家、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同样是普鲁斯特的超级粉丝,他于1930年完成了长达3万字的长篇评论《论普鲁斯特》,他将普鲁斯特通过“非意愿记忆”来揭示自身的存在视为一种笛卡尔式的“方法论”。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叔本华非理性哲学的影子,它体现出普鲁斯特一贯的反智性态度。对于“非意愿回忆”的诸多细节,贝克特专门排出了一张长长的列表,他将之命名为“有灵之物的列表”:
1.经茶水浸过的玛德莱特小甜品。(《去斯万家那边》第一部)
2.从贝斯比埃大夫的双轮轻便马车上看到的马丹维尔钟楼的尖顶。(同上)
3.弥漫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公共厕所的霉味。(《在少女花影下》第一部)
4.在巴尔贝壳附近,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上看见的三棵树。(同上,第二部)
5.巴尔贝克附近的山楂树。(同上,第三部)
6.他第二次在巴尔贝克的海滨大旅社弯腰解靴扣。(《所多玛和蛾摩拉》第二部)
7.在盖尔芒特府内庭院中凹凸不平的鹅卵石。(《重现的时光》第二部)
8.汤匙碰撞盘子的声音。(同上)
9.用餐巾擦嘴。(同上)
10.水管中刺耳的流水声。(同上)
11.乔治·桑的小说《弃儿富朗索瓦》。(同上)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无疑是人尽皆知的“小玛德莱特”点心的细节。当小说中的“我”喝了泡着“小玛德莱特”点心的茶,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也许,这感觉并非来自外界,它本来就是我自己。”小说中的“我”(背后无疑是普鲁斯特本人)认为,人们关于往事的记忆是理性和智力所无法企及的,只能在无意间被现实的感受和事物偶然唤醒。通过这块小小的玛德莱特甜点,普鲁斯特将创造出一座宏伟的“非意愿回忆”的纪念碑。
由于来自往昔之井的“非意愿回忆”的无序性和偶发性,普鲁斯特笔下的小说呈现给读者的不再是按照传统的故事时间的轴线,取而代之的是心理时间(受到亨利·柏格森的影响),这也带来了叙事形态上的革命:故事的时间顺序被打乱,构成小说细部的是无意识的联想,是沉思录,是议论,是解释,是说明,是一篇长长的散文,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张回忆之网,正如本雅明所言:“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特例。但在那些特例中,这一部作品属于最深不可测的一类。它的一切都超越了常规。从结构上看,它既是小说又是自传又是评论。”
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回忆方式,普鲁斯特完成了对“逝去的时光”这一最可宝贵的事物的追寻和求索。对于别的作家,时间也许只是一种意识,但对于普鲁斯特,时间乃是他生命的向度。熟悉普鲁斯特个人生活的读者都知道,他追求幸福的方式就是追寻逝去的时光。那由感觉、知觉向情感方向的衍变,那如潮水般在心中涌来、退去的纷纷往事,那由渴望、嫉妒和富有诗意的欣喜之情等的延绵起伏所构成的情感波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普鲁斯特一生的印记,也构成了这部超级宏伟又极为空灵、同时饱含深邃意蕴的巨著。“倘若假以天年,让我得以完成自己的作品,我一定会给它打上时间的印记。”他显然做到了。
记忆与遗忘的悖论
有心的读者可能会追问一个问题:靠着“非意愿回忆”就真能找回过去的时间吗?一个真实但令人沮丧的答案是:不能。博尔赫斯曾说:“时间问题就是连续不断地失去时间,从不停止。”事实上,任何人在回忆中(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回忆)捕捉到的过去都只是心理层面的幻象,小说家写进小说中,则成了文学的幻象。柏格森发明的心理时间的概念本质上与时间问题无关,而是心理和意识问题。令人困惑的是,每一个此刻似乎都无法抓住,就立即变成了过去,人能拥有的唯一切实的东西就是逝去的时间,而这又是最大的虚幻的根源。整部《追忆逝水年华》对自我追寻的悖论和困境正在于此。
受到叔本华哲学的深刻影响,身为悲观主义者的普鲁斯特显然深谙20世纪的现代主义精神。他很清楚自己所追寻的东西的幻象性以及记忆大厦的乌托邦属性。时间就像是一个古希腊的双面神,一面可以留下记忆,另一面也可以无情地剥蚀记忆,甚至摧毁记忆。因此,在普鲁斯特这部巨著显性的主题“记忆”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同样重要的隐性主题:遗忘。莫洛亚在序言中有如下一段精彩的文字:
人类毕生都在与时间抗争。他们本想执着地眷恋一个爱人,一位友人,某些信念;遗忘从冥冥之中慢慢升起,淹没他们最美丽、最宝贵的记忆。总有一天,那个原来爱过,痛苦过,参与过一场革命的人,什么也不会留下。
莫洛亚道出了普鲁斯特试图表达了更潜在的含义,即寻找逝去的时间其实是与时间本身以及与遗忘相抗衡的方式。颇有意思的是,这一隐性的“遗忘”主题在另一位小说大师米兰·昆德拉笔下成为了标志性的显性主题。他的《笑忘录》是探讨遗忘主题的经典之作,后来用法语写作的《慢》、《身份》和《无知》则被法国评论界称为“遗忘三部曲”。如果说普鲁斯特还只是把回忆看成是对遗忘的抗争,昆德拉的理解似乎更为深刻: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这是对普鲁斯特“遗忘”主题的发展和变奏。
或许,普鲁斯特一再反复修改的这部巨著想要最终暗示我们:记忆可能是现代人的最后一束稻草。人类尽管可能一无所有,但至少还拥有记忆,在记忆中尚能维持自身的自足性和统一性的幻觉。而这份宝贵的幻觉,在如今这个极度扁平化的世界里已经几乎不复存在。移动互联网的无处不在,让每一个人感受到人类空间的共时性对自身的压迫(你可以一边看欧洲杯,一边发弹幕,一边浏览新闻,一边微信聊天等等),时间的纵深感荡然无存。反过来说,普鲁斯特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降低了,而是进一步上升了。因为在小说的可能性的世界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种全人类所能共有的关于时间的幻觉。因此,当我们读到威廉·福克纳《野棕榈》的著名结尾时,我们依然能被深深感动(女人因流产失败而死去,男人仍在监狱,被判刑十年;有人给他的囚室里带来一片毒药;但他很快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唯一能延长他所爱女人的生命的方法便是把她保留在记忆中):
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已经不在;如果我也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在。是的,他想,在悲伤和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是的,普鲁斯特的价值是超越时代的,正如所有真正第一流的经典一样。只要有读者的地方,就有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就像一块巨大的有着无数切面的晶体,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普鲁斯特身上读到自己,正如米兰·昆德拉的洞见:“他(普鲁斯特)写这部小说并非为了讲他的生活,而是为了通过读者的眼睛照亮他们的生活:‘每一个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都是他自己的读者。作家的作品只不过是作家送给读者的某种视觉工具,以让他可以分辨出如果没有这本书他可能就在自己身上看不到的东西。读者如果在自己身上认出了书中所说的东西,那就证明这本书具有真理性。’普鲁斯特的这些话并非仅仅定义了普鲁斯特本人小说的意义;它们定义了整个小说艺术的意义。”
- 觅踪忆华年:再寻普鲁斯特的足迹[2022-02-15]
- 普鲁斯特早就预见了这部作品的命运[2021-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