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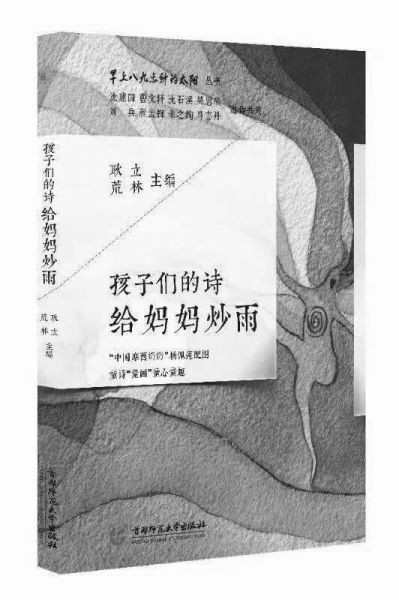
《孩子们的诗:给妈妈炒雨》,耿立、荒林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40.00元
“真”是诗歌的基本品格,在这本诗集中,基于生命本真、而又在虚幻的时空中展开的诗作比比皆是。
儿童诗就作者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给儿童写的诗,这些作者尽管是成年人,但葆有一颗童心,能以儿童的眼光观察世界,写出的诗受到孩子们欢迎,可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一些“大人腔”“说教气”;另一类是则是儿童自己写的诗,他们不是为别人而写,也不是为某种实用目的而写,他们只是有话要说,有感受要表达,写出的诗句,尽管稚拙简单,却自然天成,是真正的儿童诗。这本诗集《孩子们的诗:给妈妈炒雨》,便属于后者。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从五六岁到十三四岁不等的孩子。翻开诗集,读着那些稚气的、奇妙的诗句,仿佛面对着一个个充满好奇、纯洁善良的灵魂,小读者们会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成年读者也会从浮躁的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让灵魂得以净化,心绪得以安宁。
孩子们能在生活经验欠缺,知识结构不完善,语言储备不充足的情况下写出奇妙的儿童诗,靠的是一颗童心。童心的特点在于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童心说》)。“真”也是诗歌的基本品格,说到底,诗是掏自心窝子的一句真话。这个集子中孩子们的诗,所写内容不同,深浅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真,孩子们写诗不需要戴面具,完全出自内心,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童心的另一特点是超脱实用,这与儿童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按照皮亚杰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儿童的思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化的思维,是儿童与社会打交道时用,有明确的指向性;另一类是我向思维,是一种自我中心化的思维,是朝向自身的,儿童的自言自语便属于这一类。儿童在非自觉的状态下把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投射于客体,为自己创造一个想象的梦幻般的世界,它不是为了适应现实的某一目标,而是只求满足内心的欲望。我向思维由于排除了实用的功利俗念的干扰,因而有可能超越诗人所处的具体时空,建立一个瑰丽奇妙、闪耀着自己审美理想的艺术天地。在诗集《孩子们的诗:给妈妈炒雨》中,这种基于生命本真、而又在虚幻的时空中展开的诗作比比皆是。
殷明硕小朋友在吃掉渣饼时,突发奇想:“是谁把吃剩的/掉渣饼扔了/扔在/那漆黑的夜空/一半变成了月亮/掉下的/渣渣/化作星星”(《是谁把吃剩的掉渣饼扔了》)。这样的写法,让人想起诗人顾城12岁时写的《星月的由来》:“树枝想去刺破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从那里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叫它月亮和星星”。这两位小作者,均置星月由来的科学结论于不顾,或者是不懂,却从身边的生活展开联想,对星月的由来做出自己的解释,异曲同工,令人叫绝。
考察一下孩子们写诗的思路,会发现他们大多是从眼前的生活景象出发,但不是遵循寻常的思维路线,而是突然转换方向,迸发诗意。如徐圣乔的《海螺》:“我听到了海的声音”,循正常思路,下边应是对海的声音的具体描摹,小诗人却突然一转:“我想进到/海螺里面,/看看里面/有没有海”,这就把那种喜欢探险、好奇的孩子心境合盘托出了。再如卢君珂予小朋友的《西瓜藤》,也是从眼前见到的景物写起:“西瓜边上的藤是什么?”按正常思路,下边该是对瓜藤的介绍了,但作者却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是电线吗?/西瓜也要充电吧”,一个稚气、天真孩子的形象就浮现在你面前了。再如林蔚然的《晒被子》,也是从日常生活写起,但作者写的却不是常见的被子,而是把受潮的白云看成被子:“天空把受潮的/白云被子/挂在山头晾晒/没想到/山调皮地/伸了一个懒腰/被子一下子/滑了到了/半山腰”——山腰中的白云居然是这样来的,真是匪夷所思!这种随心所欲的想象,打破常规的写法,连成年诗人都不能不佩服。
当然,孩子也并非处在与人隔绝的世外桃源,当他走进成人社会的时候,他所持的观察世界的态度,会与成人的思维方式相碰撞,这在他们的诗作中也有反映。像刘存豫的这首《纸飞机》:“我有一个飞翔的梦/那天,我折了一个纸飞机/幻想它能飞上蓝天/替我向白云阿姨问个好/这时老师走过来了/纸飞机碎了/我的梦也碎了”。
至于成人社会中为追求工业化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在孩子的纯洁心灵中更是不能忍受,他们用稚嫩的声音发出了抗议。像穆薇的这首《天空哭了》:“天空哭了/它浑浊的泪水/惊醒了小草、小花//它们问天空/你为啥哭呢?//那黑黑的大烟囱/把我的眼睛/熏坏了”。像郑子都的《海的眼泪》:“谁来保护海/大海像委屈的孩子/那海岸像弯曲的眉毛/一片狼藉/垃圾、污水沾染了她的眼珠/使她睁不开眼/她揉揉刺痛的眼/几滴泪流出/可泪水融入海水/又有谁看得到她的痛苦呢?”
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在成长。成长的经历自然会成为孩子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孩子的生活不只是游戏与喧闹,孩子的心灵也不只是离奇的梦幻,他们也有对自己人生的思考。黄祥钰有首诗叫《我到底从哪里来》,追问自己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叫明年的小朋友写的《如果克隆一个我》,则展示了真实的我与克隆的我的对话,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真实解剖。
这种成长的历程,在典典的诗歌中有更明显的表现。典典七岁的时候,她把天上的云彩当成绵羊,写出了充满稚气的《绵羊,云彩》;当她14岁,成为少年的时候,她开始思索人生,在《童年》一诗中,她写道:
我背着一个大口袋,/出门去寻找童年。/找啊找啊,/童年终于被我找到了。/我把它装进袋子里,/背到家一看——/哎呀!/童年只剩下一点儿了。/原来,当我翻过高山时,/树枝勾破了袋子;/当我走过平原时,/荆棘刺破了袋子;/当我渡过小河时,/河水浸透了袋子;/于是,童年就从袋子里,/悄悄地溜走啦!/——这个袋子就是回忆。
这首诗的思维方式、所用的口气,都是孩子式的,她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回忆”赋予了一个“袋子”的外形:“我背着一个大口袋,出门去寻找童年”——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何等鲜明!“童年”是这首诗所要写的主题,“寻找”是这首诗的主旋律。这是一首成长之诗,意味着孩子由儿童向少年的转换。
为了保留与强化诗集中的童真童趣,编者还特别请中国摩西奶奶杨佩莲配了插画。杨佩莲奶奶80岁了,却葆有一颗童心,富于想象,她的画自然天成,趣味盎然。她用孩子的眼光观察世界,用稚拙、独特的画笔,给孩子们的诗还原出了一个童话世界。孩子们的天籁之音与老奶奶的画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为这部诗集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