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纳:“法国文坛上最孤独的作家”

路易-费尔迪南·塞利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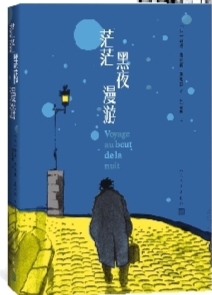
20世纪法国作家路易-费尔迪南·塞利纳,原名路易-费尔迪南·德图什(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其作品以其独特的口语风格和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揭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下层社会的真实状况,与描述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追忆似水年华》一起全面地呈现出了法国这一特殊时期的生活画卷,因此塞利纳被称为“平民普鲁斯特”。但是,长期以来文学界对于塞利纳的评价却总是褒贬不一,没有定论。塞利纳的政治立场似乎一直如阴影一般笼罩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上和他的生命旅途之中,正如法国评论家布吕奈尔所说,塞利纳是一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他的一生同时也是“被伤害的一生”。《法国小说论》一书中介绍塞利纳时甚至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塞利纳的形象:“塞利纳是法国小说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是法国文坛上最孤独的作家。他的一生颠沛流离。”
塞利纳出生于巴黎市郊的库尔布瓦。母亲是花边零售商,父亲是保险公司职员。“塞利纳”这一笔名来源于他外婆的名字,也是他母亲的中名。菲利普·阿尔梅拉在塞利纳的传记中写道:“塞利纳至少在外貌上酷似他的母亲,他是吉约家族的后代,具有鲜明的布列塔尼人特性。”外祖母逝世之后给他们留下了一笔较为可观的遗产,因此塞利纳得以赴英国和德国学习外语,掌握多种外语对塞利纳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回到法国后,他成为了商店学徒,依照母亲的意愿,为成为商人作准备。1912年9月28日,18岁的塞利纳应征入伍,逐渐卷入了改变他一生的战争之中。虽然他有幸从战火中活着出来,并且获得了银质军功章,但是这场战争仍然使他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失望和恐惧的情绪,塞利纳作品中体现出的悲观的和平主义正是在这场战争之中慢慢形成。因伤回到后方之后,塞利纳与一家贸易公司签约远赴非洲,亲眼目睹了殖民地生活的悲惨状况,更加加深了他的失望情绪。重回法国的塞利纳在雷恩安定下来,并且通过中学会考重拾学业,最终成为一名医生。从医期间,他曾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卫生方面的派遣人员,多次前往非洲和美国。跌宕起伏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为塞利纳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塞利纳独特的感受力和表达力更使其从事文学创作具有了可能性。
处女作《茫茫黑夜漫游》于1932年出版,此时他已经38岁,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小说出版后即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仅以2票之差错失龚古尔奖,获当年勒诺多奖。对于一个文坛新手来说,能够获得龚古尔奖的提名已经实属不易,随后折桂勒诺多奖,更使得塞利纳成为了当年名副其实的“文坛黑马”。《茫茫黑夜漫游》的颠覆性力量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浪潮,人们心中被战争压抑的文学激情仿佛一时间都被这本书释放出来,无论褒扬还是贬抑,似乎所有读者都难以控制自己发表意见的欲望。塞利纳的第二部小说《分期死亡》出版于1936年,和《茫茫黑夜漫游》一样,这部小说也同样是长篇巨著,其内容仿佛是《茫茫黑夜漫游》的姊妹篇,主要以自己幼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为基础,讲述主人公的境遇。从其写作风格来讲,塞利纳的口语特色与叙事张力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此时的塞利纳已经不再满足于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是应用更直接的论战手册的方式来直抒内心深处的呼喊。在随后出版的《草菅人命》(Bagatelles pour un masacre,1937)、《死尸学校》(L’école des cadavres,1939)、和《进退维谷》(Les beaux draps,1940)等小册子中,塞利纳发表了排犹主义言论。这些小册子成为了塞利纳作为“反犹主义作家”的罪证。在这些小册子中,他不但对犹太人进行攻击,而且埋怨西方世界在退化中的沉沦,并将此归罪于美国人的反法西斯宣传、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黄种人与黑种人的增多。塞利纳认为,是有钱人使人民生活困难,是有钱人剥削大众、统治社会,轻而易举地促使世人互相残杀。因此当他发现他的第二部小说不太受欢迎时,突然转向杂文,猛烈攻击种种社会不良现象,矛头直指犹太人。但是如果对其作品进行仔细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塞利纳所主张的“反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塞利纳的中文译者沈志明先生认为,塞利纳所反对的,是战争期间使人难以生存的社会状态和难以面对的社会现实,亦即塞利纳的“反犹主义”是作家期待变革、期待人类告别野蛮的战争、回归文明社会一种愿望。虽然很多人给塞利纳冠以“反犹主义”的帽子,但是塞利纳在德国依然拒绝了亲德主义宣传,并且因此遭到拘禁。沈志明在《塞利纳精选集》一书的译序中对塞利纳所受的各项指控进行了一一反驳,并且认为“塞利纳在大节上曾遭受的严重指控,是法国文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塞利纳在失宠于本国人民、不得不流亡国外的同时,也并没有得到德国人的青睐,他背负着反叛的罪名却从未与敌方合作,最终孤独地流亡,孤独地回归,孤独地逝去。
作为塞利纳小说风格集中体现的《茫茫黑夜漫游》,其内容涵括的时间范围是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直至小说出版之间。四年的战争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有140万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战后的法国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复苏时期,然而1931年的经济危机再次给法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政治方面,表面的平静之下隐藏着内忧外患,纷争不断,下层民众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引起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时殖民地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危机的加剧直接导致国际关系的恶化,加之战争遗留的多重矛盾依然存在,潜伏的危机逐渐明朗,新的战争一触即发,可以说1932年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和社会状况的风云突变都为《茫茫黑夜漫游》的创作提供了可能的素材和独特的背景。塞利纳本人的经验也成为《茫茫黑夜漫游》创作的必要的参考。首先,塞利纳本人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小说中战争的场面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作者对战争的感受和态度却并非虚构。其次,复员后的塞利纳重拾学业,通过医学博士答辩,并以医生的身份到美国、非洲、欧洲各地执行一系列医学任务,此间的经历在《茫茫黑夜漫游》的强烈空间性方面得以充分体现。再次,1927年开始,塞利纳在巴黎郊区行医,作为直接与郊区贫民接触的医生,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有着更深的体会与了解。最后,塞利纳自身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学生、学徒、战士、医生、职员等等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体会。《茫茫黑夜漫游》之所以能够在30年代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因为作者对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揭示,而且因为他把这些集中在一部小说之中,由一个人物来体验,而且这个人物总是社会的牺牲品,或者总是站在牺牲品一边。塞利纳把自己的经历经过艺术加工,移植到小说的人物身上,使读者产生真实的感觉。虽然从其极端悲观的基调角度和众多的虚构成分来看,《茫茫黑夜漫游》并不能够被视为作者的自传,但是这部小说的确是建立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基础之上,战争、法属非洲殖民地、纽约的噩梦、底特律地狱般的工业化操作等等,都是作者以个人经验为基础所构建出的无尽旅程。
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以医学专业大学生巴尔达缪的个人经历为线索,系统地揭示了20世纪初法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巴尔达缪与同学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时,受到军乐的鼓舞主动参军。战争开始后他才发现战争是一件“充满恐怖的蠢事”,于是产生了逃跑的念头。战争导致他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后方医院的生活中,他依然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竟曾为此发疯。可以说,战争的“后遗症”贯穿了巴尔达缪的整个人生。为了远离战争、到殖民地去寻找发财之路,巴尔达缪踏上了开往非洲的航船。这次航行本身就使他意识到,空间的转变并不能够改变他不断逃亡的命运。殖民地炎热的气候、难以忍受的食物和未开化的文明使巴尔达缪万念俱灰,因此他放火烧毁了自己公司的小茅屋,逃出原始丛林。几经周折之后,巴尔达缪被一位神甫转卖给一艘开往美国的商船。在经历过纽约街头的漂泊、底特律的机械化工作之后,巴尔达缪决定返回法国,重拾学业,由此结束了他环绕世界的漂泊生涯。回到巴黎的日子并不是风平浪静,成为郊区医生的巴尔达缪收入微薄却需每天面对着各种病态的人物。此时小说中的另一线索人物罗班松一直有如巴尔达缪的影子般追随着他,罗班松的再次出现把巴尔达缪的生活引向了另一种方向。罗班松受雇于昂鲁伊夫妇,设计杀害昂鲁伊老太太未遂,却伤到了自己的眼睛,巴尔达缪为他做了最初的医治,而后罗班松和昂鲁伊老太太一起被送往图卢兹,看管教堂地下室。巴尔达缪的生活并未因为罗班松的离开而好转,反而因为病人寥寥不得不另谋生路。在失去小丑演员这份工作后,巴尔达缪从“罗班松事件”中得到了一笔意外收入,前往图卢兹探访罗班松,并见到了罗班松的未婚妻玛德隆。从图卢兹回到巴黎,巴尔达缪进入了一家精神病院工作。罗班松的再次来访将小说引向最终的结局。巴尔达缪目睹了罗班松被玛德隆射杀之后,独自徘徊在塞纳河畔,流水有如无尽的黑夜,把这段旅程带向未知的远方。
《茫茫黑夜漫游》有如战争时代的诺亚方舟,几乎将各行各业以及社会各界的人物都网罗其中,每一位读者似乎都能够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因此小说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但是,《茫茫黑夜漫游》的接受过程充满了起伏和曲折。1932年作品出版之时获得了多方面的肯定。左派和右派都把塞利纳视为自己的盟友。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小说中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观点、“民众”语气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都极其符合他们的要求,苏联共产党也对这部小说分外青睐,斯大林甚至将此书作为“枕边书”,以致于小说俄文版很快面世,俄文版的序言称《茫茫黑夜漫游》为“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真正百科全书”。对于右派来说,塞利纳小说的“颠覆性”似乎表面看来有些令人吃惊,而莱昂·都德却认为这部小说所掀起的革命,是在“新基础上重建旧秩序”,因为塞利纳小说中充满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怀念。然而在塞利纳发表反犹主义小册子之后,这种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状况立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被视为通敌分子的塞利纳不得不流亡国外,并且忍受牢狱之苦,他的作品也随之遭受冷遇。在法国,从二战胜利到1957年,人们都不谈塞利纳,就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他,“塞利纳”这个名字几乎被人遗忘,成为了一个空白。1951年获赦回国后到1957年,他出版了两部小说,但无人问津,最多只卖掉了一两百本。对他的评价也经历了低潮,撇开他的反犹问题不谈,二战后,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认为他已经才尽。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况也影响到了塞利纳作品在外国的流传。在美国,派瑞克·麦克卡西(Patrick McCarthy)写道:“《茫茫黑夜漫游》于1932年在巴黎出版。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英文译本——由H.P.约翰所译的Journey to the End of Night于1966年在伦敦出版。我写了一篇褒扬的评论,斯诺女士在其书中无情地批判了我的评论,她认为塞利纳这样的作家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致命的衰退。对于很多人来说,塞利纳是一个危险的作家,他的作品极少有译本,已有译本又出现得非常晚,这一点也证实了人们对他的看法。甚至在法国,人们也依然是戴着手套、拿着火钳才去触碰他的作品,塞利纳与海明威在同一天去世,但是他在法国报纸上所占的篇幅却远远少于有关海明威的报道。”
1962年,即塞利纳逝世后的第二年,塞利纳作品被收入“七星文库”,他的文学地位逐渐得到肯定。法国《文学杂志》在《茫茫黑夜漫游》出版70周年之时推出了塞利纳专刊,该杂志此前出版的3本作家专刊分别为纪念弗洛伊德、尼采和普鲁斯特,塞利纳文学地位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1962年,塞利纳的“七星文库”版作品第一卷出版。这一版本的出版除了标志着塞利纳的文学地位得到肯定之外,还预示着塞利纳作品的研究将以更深入的形式展开。“七星文库”版塞利纳作品第二卷也于1974年问世,其中收入了塞利纳作品《从一座古堡到另一座古堡》《北方》《轻快舞》。直至1988年,《丑帮I、II》收入“七星文库”,“七星文库”版塞利纳小说三卷本才得以全部与读者见面。时间上的拖延,一方面表明了研究者和出版者准备工作的详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其中的周折。关于塞利纳的争议,似乎从未止息。2011年为塞利纳逝世5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在文学史上掀起伟大变革的作家,法国政府2011年初将其列入《2011年度国家庆典名录》中,但是由于犹太人状况研究者们的极力反对,法国政府不得不撤销这一纪念性行为。2017年法国仍有学者出版专著,洋洋千页篇幅指责塞利纳的反犹主义写作与充当“法奸”的行为。2018年新年伊始,围绕塞利纳3本小册子的再版问题,法国文坛再次引起了一场激辩,这一方面说明了塞利纳的政治观点确实给他的小说作品接受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学研究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塞利纳的关注依然热度不减,以致作家逝世五十年后仍然能够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如何在激烈的争议之中正确评价塞利纳小说作品的文学意义与历史价值,日益成为国内外法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塞利纳的研究者弗里德里克·维图将其称之为“非理性的作家”。这种“非理性”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即塞利纳的作品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反抗同时代的文学,力图回归拉伯雷的法语口语传统,但是他最终不仅打破了法语口语传统的语言规则,而且创立了自己的词法句法。塞利纳在法语语言与文体风格方面的这种创新,奠定了其在法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塞利纳作品的“七星文库”版负责人亨利·戈达尔正面地肯定了塞利纳的文学成就:“从蒙田到帕斯卡尔,从拉布吕耶尔到圣西门,从伏尔泰到夏多布里昂,从司汤达到普鲁斯特,他们都是能够且唯一有权力对于自己同时代的人或事表达些什么的作家,为了这种表达,他们创立了一种可以载入法国文学史册的文风。塞利纳也是这类作家之一。”戈达尔指出,“越来越多的读者感受到了塞利纳作品中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由此变得不可忽视。”
1999年由法国《世界报》组织的“20世纪100部最佳小说评选”中,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位居第六。塞利纳的作品不断重印和再版,也印证了这位作家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毋庸置疑,塞利纳政治上曾经的反犹思想是其人生中最大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给他带来了不可逃脱的诅咒与噩运。但是无论在何种噩运面前,塞利纳都不断地反抗与挣扎,他的作品有如从悲惨的世界中发出的呼喊,他不断地试图通过写作将历史的真相呈现在世人面前。塞利纳的译介先驱柳鸣九教授与沈志明先生都认为其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肯定了塞利纳作为经典作家在文学方面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因此,抛开围绕塞利纳的政治争议,从其小说创作角度探讨塞利纳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历史意义,是我们在文学层面给予塞利纳正确定位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