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分隔主义自画像
毛姆是个作家中的异数。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做到凭借写作技能立身,而他却凭之获取了不可思议的财富。《月亮与六便士》又是毛姆作品中的异数。在距离此书问世已有一百余年的今天,它的诸多译本仍然在异国书店的榜单上翻涌浮现。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初次听闻这个书名便留下深刻印象并被勾起了些许好奇心。多年以后,或许正是这被淡忘许久的好奇心促使我选择来做它,填补一段出版生涯迷惘期的空当。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作为书名并没有在这部小说的正文中出现,它的来源是一篇关于毛姆的上一部小说《人生的枷锁》的评论。在其中主人公菲利普·凯雷被如此描述:“他一心忙着渴慕月亮,从未看见过脚边的六便士。”六便士是英国当时最小的币制单位。在1956年毛姆的一封信里,同样的意思又被如此表述:“当你看向脚下,寻找六便士,你就错过了月亮。”
月亮在文学传统中历来是一个重要且多义的象征。在浪漫主义大诗人济慈那里,月亮这簇冰冷的火焰象征着智识之美(intellectual beauty)。人类灵魂和思想中的智识是对于宇宙秩序的感知,常以艺术之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是现代世界的滥觞期,而现代性在文艺领域的一个标志是,艺术作品的关注点从外部的物质世界朝向内在灵魂世界的转变。月亮在灵魂向度上的象征意义在浪漫主义之后的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文艺思潮中得到更多的演绎和阐发。毛姆的这部小说构思始于1904年,出版于1919年,正是这些思潮泛起的时期。毛姆显然把握并接受了这些思潮中的一些概念,运用到了小说中。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感受到物质世界纷繁表象下的大秩序,仿佛在内心深处被月亮投下的冰冷光镞射中,有了不凡的领悟,并被其掌控,便不顾一切地投身艺术生涯,像仰望月亮一般,开始了对于美的忘我追寻。这种精神力量的纯粹和强大,让六便士所象征着的一切物质的世俗的牵绊显得微琐而无足挂怀。
毛姆在后来的文章中言及塑造斯特里克兰德这个人物时部分地使用了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高更的生平。小说中关于斯特里克兰德及其画作的一些描述与高更本人及其画作多有吻合。很多版本的《月亮与六便士》也都选用了高更的画作为书中插图。

高更
高更专门从事艺术前也曾是巴黎的证券经纪人,收入丰厚、生活优渥,后来因股市低迷,收入锐减,几经波折便彻底转向了艺术事业。他曾随妻子搬去哥本哈根生活,两人却产生了隔阂,他又独自带着儿子返回巴黎。高更也曾几度陷于贫困,后来也奔赴南太平洋海岛,在远离尘嚣的原始环境中专注创作,产出了一大批令他身后声名鹊起的杰作。高更病逝于海岛后,他的经纪人为其举办了几次重要的画展,产生很大的影响,高更被推为后印象主义的代表人物。后印象主义又与象征主义有着深刻的关联。小说中,斯特里克兰德喜欢阅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诗作,而现实中的高更也是马拉美的推崇者。
然而除了这些背景生平上的大致吻合外,斯特里克兰德这一人物形象的很多方面也与高更相去甚远。高更的遗孀梅特曾评价这个人物跟高更没有什么关系。将真人实事编入故事,拼贴剪裁,虚实相掺,是毛姆小说写作的一大特色。毛姆晚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会为我想塑造的人物寻找一个现实中的人作为基座,真实与想象在我的作品中混合得如此充分,到后来我自己也忘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高更就是毛姆为塑造斯特里克兰德的形象寻找到的基座。仔细读过小说并对毛姆和高更两人的生平都有所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毛姆安排斯特里克兰德去做的正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摆脱婚姻和家庭的束缚。众所周知,用毛姆自己的话说,他是“四分之三不正常,四分之一正常”的双性恋,和男伴相处更为融洽。毛姆的婚姻发生在这部小说写作过程中,他是出于无奈才接纳了与他有婚外情并怀孕的医药大亨的妻子西丽。婚后两人的家庭生活颇为不谐。毛姆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男伴哈克斯顿在外旅行。性格开朗善于交际的哈克斯顿为毛姆收集小说素材,充当保镖。两人相伴三十年,毛姆作为“故事圣手”的声名里也有哈克斯顿的一种效力。西丽是著名的室内装饰设计师,开创了那种大面积采用纯白色的简约冷淡的装饰风格,当时在伦敦颇为流行。这也与小说中对妻子特长的描写相吻合。西丽应该是斯特里克兰德妻子这一人物形象的主要原型。
再看小说的另外两个男性角色,叙述者“我”的人物设定是年轻作家,在身份和旅居地点等多种细节上都与毛姆本人重合;如果说斯特里克兰德惊世骇俗地实践了毛姆被压抑的欲望冲动,是他人格中本我部分的投射的话,显然理性而平和的“我”便是毛姆人格中社会面具的承接者;至于那个对艺术之美怀有一腔赤诚,克己为人,极其善良,却总是被人嘲笑的平庸画家斯特洛夫显然也与毛姆的自我认知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是为毛姆理想化自我的投射。虽然毛姆当时已是作品大受欢迎的剧作家和小说家,却没有获得评论界足够的尊重和赞誉。那时文坛的风云人物是现代主义实验派大作家们,如乔伊斯、伍尔夫等,他们的独创性和勇敢被评论界大加褒扬。毛姆无法跻身其间。他谦虚地自称为“二流作家中的一流”,并归纳了几条自己不被评论界待见的原因:作品的抒情性不够,词汇量小,对隐喻的运用不够纯熟,等等;而幼年因为口吃问题屡遭嘲讽的经历也在毛姆心中留下了阴影。把一个高尚人格与滑稽形象的矛盾组合体设置成众人眼中的笑柄,一个曾经处于同样境地、满腹委屈的毛姆安放了自己,回应了他感受到的世情凉薄,想必也得到了心理补偿和纾解。
回顾毛姆的创作生涯,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初战告捷让他有了信心专事写作,但此后的几部小说都反响平平,收入甚至无法支持他的自立。毛姆便转而开始写剧本,并大获成功,有过伦敦四家剧院同时上演他一人的剧目的傲人记录。当时的英国媒体上甚至出现过这样一幅漫画:莎士比亚低头咬着手指用眼角的余光瞟着毛姆四部剧作同时上演的海报,似乎在因嫉妒而郁闷。但是风头正盛的剧作家却对他的经纪人弗洛曼说他要暂停剧本创作一整年去写小说,因为那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事。他有心头的负担要卸下。看到这里,你是否想到了小说里斯特里克兰德的那一句“我必须画画。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毛姆重拾小说创作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人生的枷锁》被普遍认为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他在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凯雷的成长叙事中代入了大量自己早年的经历和心理感受。但紧随这部作品之后的《月亮与六便士》由于采用了高更的生平作为故事外廓,历来被认为带有某种高更传记的属性。实际上,在这部小说里,毛姆审视和讲述自己的人生、在创作中达成宣泄和纾解的过程仍在继续。如果说第一部小说的关注投放在他过去的人生,那么第二部小说里,着眼点便在于他三十多岁时的现状和未来历程。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但凡作家在某部小说里使用第一人称来展开叙述,那么这部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深藏却又直白的自传性,有心且有洞察力的读者可以深入文本挖掘拼合出一个赤裸裸的作者本人。因此对于《月亮与六便士》,我们或许可以有两个层面上的解读:表面上,毛姆对艺术家高更的性格和经历进行了艺术处理,以提纯和夸张的手法赋予人物以一种纯粹到惊世骇俗的艺术家人格,使得人物形象异常鲜明,并且概念化,而作品也具备了一种神话或寓言性质,成为一则承载现代艺术理念的现代艺术生涯神话。而从深层看,这个故事是毛姆以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为原点为自己编织的一件隐身衣,是一部采用了“人格三分法”写就的隐性自传,一番真实深刻的自我讲述和自我剖析。
毛姆的叙事天赋令他将小说的这两个层面整合得几无缝隙,或者说他将自己的人生相当平顺地嫁接在了高更的生平之上。他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正适于神话寓言类故事的讲述,而生动讥诮的对白又为故事增添了肌理和趣味,承受着他的三分人格投射的三个主要男性角色及其互动提供了故事的深层心理构架,是情节张力和戏剧性的主要来源。最后,“月亮与六便士”这个象征主义的书名也起得非常妥帖。这一意象组合在文化传统里本来就有着广为接受的丰富意涵,易于深入人心。在我看来,艺术家神话中的传奇经历和鲜明形象,一个如毛姆般生活多姿多彩的人的内心戏剧外化而成的耸动故事,被毛姆的一支笔调和得如同行云流水,给读者以绝佳的阅读体验,再加上迎合了时代思潮的书名的点睛作用,使得这部小说成为畅销百年的经典,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在迈克尔·豪斯为毛姆拍摄的纪录片里,一位作家为毛姆辩护,说他其实和现代主义大作家们一样无畏,探索的是一样的主题,并且将之放置在了一个谁都能够读懂的框架内。
谈到毛姆的叙事天赋,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在结构布局上也令人联想到高更以粗线条分隔大色块的分隔主义画风。小说的故事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伦敦部分、巴黎部分和海岛部分。每个部分的叙述视角都不一样。在伦敦的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沉闷乏味的证券经纪人,从“我”和他妻子的视角看去,他的社交存在感为零(“他等于零”);在巴黎的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独自挣扎的艺术学徒,在绘画创作中陷于天人交战,穷愁潦倒,对朋友和情人冷酷无情,是个损友加渣男,得分为负;在塔希提岛,将岛民的视角汇集,他是比土著更土著的红毛画家,终于和环境水乳交融,全心创作,是一个无畏疾苦,在艺术之路上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勇士。毛姆数次在小说中提起关于叙述顺序和素材排列的考量,这让叙事本身及其意图的存在感变得很强,如同粗线条在分隔主义画风中一般清晰。毛姆似乎也有意提醒大家注意他在结构布局上的用心。
除去三个男性角色外,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也都塑造得个性鲜明。斯特里克兰德的妻子是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势利又清高,自诩爱好艺术,却颇为讽刺地没有眼力看出自己丈夫极高的艺术天分;她拥有才能可以自立,却固持着女性唯有依靠男人生活才有面子的陈腐观念。斯特洛夫的妻子布兰奇两度为爱情飞蛾扑火,却遭受抛弃最终悲惨离世,毛姆对此冷淡置词。他嘲笑女人对于爱情的执着,甚至通过斯特里克兰德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你像对待狗一样对她们,打她们打到手痛,她们却还是爱你。她们也有灵魂吗?这肯定基督教最荒谬的幻觉之一。”可以说,这两个女性角色的身上都有着毛姆妻子西丽的影子。毛姆虽然写出了一种社会和人性的现实,却也在此暴露出了他自己对两性隔阂的不解和观念上的局限性。
对于斯特里克兰德不管不顾伤及他人的行为,毛姆通过叙述者“我”之口先是表达了谴责,后来又以艺术之名做出了辩护,态度颇为纠结:“斯特里克兰德是个烂人,但我觉得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又比如,小说里斯特里克兰德遭抛弃的妻子这样诅咒他:“我希望他在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中痛苦地死去,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希望他染上恶疾,浑身烂掉。”虽然“我”认为这话很恶毒,但小说的最后,大家都看到了,毛姆对斯特里克兰德终局的安排正应了这句诅咒。可见毛姆虽然塑造了一个弃世绝俗的艺术家形象来替他冲破束缚,却在内心深处仍然受着社会禁忌和道德评判的禁锢。
同性恋在毛姆的时代尚属社会禁忌,王尔德就因为同性恋行为而被斥为伤风败俗,受到公开审判,毛姆的男伴哈克斯顿也由于同样的问题而无法踏足英国国土。因性向而形成的边缘人身份令毛姆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和观念对人性的种种束缚,因此在作品中也表现得颇为反叛。毛姆素以毒舌著称,唯独对作品中的一类女性笔下留情,只有赞美。那就是像《寻欢作乐》中的罗西和本书中的缇亚雷这一类热情慷慨、生性风流、敢于反抗世俗观念的女性。
文章的最后,我想有必要约略提及这个中译本的几位参与者。熊裕女士在翻译《雪落香杉树》一书后成为颇受欢迎的译者,豆瓣邮箱里收到过数十封来自各出版品牌的翻译约稿信。在她撰写的《雪落香杉树》译后记豆瓣页面下,近百位陌生读者留言感谢和赞美她的译笔,殊为罕见。收获普通读者的普遍赞誉,我以为是译者能获得的最好肯定。在《月亮与六便士》的翻译上她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多方查证反复校改。改错如扫落叶,一遍遍的打磨只求译本在通往信达雅的道路上有所推进。惟其如此,复译经典才显其意义。丁威静女士为本书选择的封面图案融合了月之形与银币之质,和书名一样,简洁而富于象征意涵;封面设计的整体风格冷峻纯粹,也与小说主人公的精神气质颇为契合。毕猊先生于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协助解决了部分技术性难点,在此一并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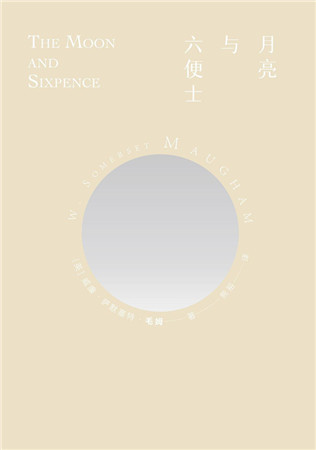
《月亮与六便士》,【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熊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全本书店,202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