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青哥》:在日朝鲜人的家与恨
这是一个关于家的故事,亦是一曲悲叹人间差别与冷漠的歌。
楔子: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初识“在日朝鲜人”(笔者按:“在日朝鲜人”是指在二战前移居日本的朝鲜半岛出身之人及其子孙,关于这一群体还存在“在日”“在日韩国人”“在日韩国·朝鲜人”“朝鲜半岛系居民”等多种称呼,本文以“在日朝鲜人”统称)这一群体,是在2013年赴韩读博之后。当时,我在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系师从郑泰宪教授学习日据时期的历史,课上时常会涉及近代朝鲜半岛海外移民的话题。郑先生不断用“자이니치(日语‘在日ざいにち’)”、“조센징(日语‘朝鮮人ちょうせんじん’)来指称这一在日朝鲜半岛移民群体。后来得知,郑先生赴日访学时,曾特意选择前往在日朝鲜人的高等教育机构——朝鲜大学。而当我又进一步从同门口中得知导师年轻时曾因参与民主化运动而一度入狱的经历后,我也便逐渐明白了这位左派进步导师缘何对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密切关联的日本朝鲜大学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2019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来到中山大学韩语系工作。巧的是,当时系里有一位特聘研究员竟然也是在日朝鲜人。有一次,我请他吃饭,他和我聊了不少家里的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在日朝鲜人身世的复杂性。这位在日朝鲜人第三代,先后在日本、韩国求学。在我眼里,他是一位优秀、刻苦、真诚的学者。但说实话,他的韩语并不好,且带有明显的日本口音。现在细细想来,或许比起韩语,日语才是他的母语,为何强求他要说一口流利标准的韩语呢?
我常认为,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是悲情与厚重的。苦难压弯了这片土地,却也将人间世相的风云变幻与善恶妍媸演绎到了极致。而在日朝鲜人的历史,无疑被迫地承载与延续了这片土地的眼泪与怨恨。
何以为家?
最近Apple TV+ 热映剧《柏青哥》(又名《弹子球游戏》)是一部基于美籍韩裔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说拍摄的电视剧,讲述了1910年至1989年一个在日朝鲜人家庭四代人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前行的故事。作家李敏金坦言,作品是一个关于“家”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于“失去了家的人们”的故事。作为一位7岁时移居美国的美籍韩裔移民,李敏金本人也是一个失去家的人。而在20多岁时,她听说了一位在日侨胞中学生因为是韩国人而饱受折磨,最后自杀的故事。这使李敏金大为震撼,并成为其创作小说《柏青哥》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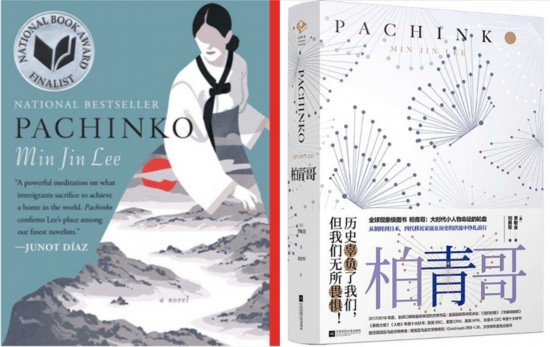
小说《柏青哥》
主人公顺子是殖民地朝鲜釜山影岛上一对经营民宿的夫妇的女儿。这对夫妇虽然并不富裕,却也能基本维持温饱。不幸的是,父亲在顺子13岁时因肺结核病逝,而对顺子的命运产生更直接影响的是16岁那年(1932年)与渔市掮客高汉秀的相遇。这个36岁的中年男人,在大阪娶有日本黑帮(やくざ)千金,并已育有三个女儿。他在隐瞒婚育事实的情况下,与顺子发生关系,并使其怀孕。顺子得知事实后,毅然与其断绝关系,并嫁给了怜悯自身处境的牧师白以撒,此后撇下母亲,随白以撒前往大阪,投奔兄嫂白约瑟和庆熙。在大阪,顺子生下高汉秀的儿子以诺,此后又和白以撒生下了摩西。

电视剧《柏青哥》海报
日本与中国的战争爆发后,1939年,白以撒因为卷入教会拒绝神社参拜的事件而被捕入狱,在两年后去世。顺子为了抚养两个儿子,毅然跳入了生活的洪流。而此时原本以为和顺子的人生早已绝缘的高汉秀又重新登场。原来高汉秀凭借自己黑社会头目的地位,一直在暗中帮助顺子一家,包括将顺子和庆熙安排在自己经营的餐厅腌制泡菜,以及在战争末期送顺子全家到后方的农场避难。
战争结束后,顺子一家在日本迎来了新的生活。诺亚在高汉秀的资助下进入早稻田大学英文系求学,而不爱读书的摩西则在15岁辍学后进入了柏青哥(“柏青哥パチンコ”,即弹珠机)行业。高汉秀的黑社会头目地位,再加上摩西日后大获成功的柏青哥行业具有的不雅标签,让这个家庭的后代愈发被“在日朝鲜人”这一身份性原罪压得无法喘气。事实上,顺子一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到了1970年代末,这个家庭在财力上已俨然跻身上流社会,而其生活的舞台也随着第三代——摩西儿子所罗门的赴美留学,拓宽至太平洋的彼岸。然而,物质的丰裕并不能完全消解精神的缺失,各代人对于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日益凸显,伴随着代际隔阂和家族成员价值观念的异质性,这个饱受风霜的家庭,又不幸地陷入了内部的撕裂与纠葛。
“历史辜负了我们,但没有关系”
在日朝鲜人的历史至今已有百余年。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殖民当局在朝鲜实行“土地调查事业”、“产米增殖计划”,导致大批朝鲜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被迫移居海外,以求生路。一战后,日本面临工业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这也为朝鲜人渡日提供了工作机遇。不过,日本政府并不欢迎朝鲜人无限制的入境。虽然朝鲜人名义上已是日本帝国的臣民,但是与日本人可以自由往返朝、日不同,朝鲜人渡航赴日时常受到旅行证明制度的限制。这一方面是忧虑朝鲜劳动力无节制的涌入会冲击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也是缘于对朝鲜人造成治安和社会问题的警惕。而其根源无疑是对朝鲜人的不信任与排斥,这在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爆发后的朝鲜人大屠杀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地震发生后,军方和官府故意散布朝鲜人纵火和井中投毒的谣言,据不完全统计,约有6500名在日朝鲜人被日本军警和维持治安的平民“自警团”屠杀,酿成了在日朝鲜人历史上的重大惨案。
然而,即便如此,朝鲜经济的疲敝和日本国内煤炭、土木、纺织等行业对于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驱使大批朝鲜人涌入日本。如下图所示,殖民地时期,在日朝鲜人的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并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因日本当局所实行的劳务动员政策而迅速增加。截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际,约有210万朝鲜人滞留日本,多达朝鲜半岛人口的十分之一。1945年8月,日本战败,大批在日朝鲜人踏上了归国的路程。然而,由于战争造成交通设施的破坏和朝鲜半岛解放初期局势的混乱,以及日本政府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对于回国携带财产的限制和再入境的禁止等原因,回国之路并不顺畅。到1946年3月,仍有60万人留在了日本。随着冷战的开始、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与对峙,在日朝鲜人再次被卷入了时代洪流的漩涡,他们的回家之路也变得愈发遥远。
GHQ最初将在日朝鲜人视为“解放民族”,支持送他们回国。然而,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其态度发生了转变。1946年10月10日,GHQ发布指示,要求在同年12月15日之前完成遣送朝鲜人回国。而对于拒绝回国的人员,则暂时保留其日本国籍,不再视为解放民族。同时,在GHQ的许可下,日本政府于同年12月中止了战前在日朝鲜人名义上所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其列入没有国民权利的“特殊范畴”。这是意识到在冷战形势日益严峻之际,当时在侨民社会颇有影响力的“在日朝鲜人联盟”偏向社会主义,为此在事前采取防止在日朝鲜人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举措。其后,1947年5月,GHQ又颁布“外国人登记令”,规定在朝鲜半岛成立正当政府之前,在日朝鲜人登记的国籍暂定为“朝鲜”。此处的“朝鲜”和其后1948年9月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关,并非实存的国家,而是单纯指称作为出生地的朝鲜半岛。因此,在日朝鲜人便从日本国籍转为了事实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国籍”民。这一“朝鲜籍”身份,一直保留到了今天。1952年4月,美日之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在日朝鲜人彻底失去日本国籍,成了日本境内的外国人。
1948年朝鲜半岛南北政权的分立和冷战局势,给在日朝鲜人的身份塑造带来了新的变数。大韩民国成立后,在日朝鲜人的外国人登陆证国籍一栏可以依照本人意愿由“朝鲜”变更为“韩国”。换言之,他们可以选择加入韩国籍,但不能同等地选择朝鲜国籍。这种偏颇性的国籍政策,在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后得到进一步强化。根据1965年6月日韩签订的《基本条约》及其附属的《关于在日侨胞法律定位和待遇的协定》,大韩民国被规定为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拥有“韩国”籍的在日朝鲜人视为大韩民国国民,日本政府针对此类申请者可以赋予永住权。而与此相对,“朝鲜籍”只是一个符号,选择继续维持“朝鲜籍”的人被视为无国籍者。这种区分“韩国籍”和“朝鲜籍”的做法,不仅促使大量原“朝鲜籍”的人选择加入韩国籍,也助长了在日朝鲜人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对立。
确切地说,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冲突并非是自然天成的。1945年9月,各地成立的侨民团体曾联合发起成立全国统一性组织——“在日朝鲜人联盟”(1949年被GHQ作为“暴力团体”强行解散,1955年改组为“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但是由于解放之初,更多人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在日朝鲜人联盟也选择支持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因此,倾向支持资本主义和反共的人士从中脱离,并于1946年11月,组建了在日朝鲜居留民团(1948年改称“在日大韩民国居留民团”,1994年更名为“在日大韩民国民团”,简称“民团”)。1948年南北独自建国以及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在日朝鲜人围绕政权的选择陷入了更为激烈的对立。民团和朝总联分别与韩国、朝鲜政府建立联系,两者逐渐成为南北政权在日本侨民社会进行角力的“代理人”。
朝鲜政府将争取在日朝鲜人视为显示体制优越性的重要手段,因此十分注重通过朝总联针对侨民开展民族教育和归国运动的宣传与动员。1954年8月,朝鲜外相南日发表声明,宣称“在日朝鲜人是共和国公民”,承诺负担他们回国所需的一切费用,并保证将为其提供稳定的生活条件。这一通过两国红十字会开展的在日朝鲜人的归国运动,从1959年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1984年,其间约有9万3千人从日本回到了北朝鲜。然而,由于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处理,该运动也遭到不少诟病。而因与朝鲜政府关系过于密切而失去自主性的朝总联,其社会形象也渐趋负面。不过,亲韩国政权的民团也并不单纯。尤其是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韩国当局为了牵制朝总联,积极扶植民团势力。不仅如此,民团和日本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其在日本社会的评价也偏于消极。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未将朝鲜视为正常国家,为了在日本能够更好地生活,战前移居日本的在日朝鲜人(Old Comer)不少选择加入了韩国籍。再加上通过朝鲜归国运动回国的人,以及1965年日韩关系正常化后从韩国前来的新移民(New Comer),在日朝鲜人的身份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据日本政府统计,截至2021年,在日朝鲜人中持韩国籍者为43万名(94.3%),而保留原“朝鲜籍”者仅为2万6千名(5.7%)。此外,从1952年到2021年,共有38万余人加入了日本国籍。随着朝韩国力对比的扭转、世代交替,以及身份构成的变化,在日朝鲜人社会最初偏向左翼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1990年,经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协议,“朝鲜籍”也被同样赋予了“特别永住权”,而冷战时期朝总联和民团之间的对立状态也有所缓和。然而,即便如此,历史本身带给他们的伤痕却久久难以愈合。
“做朝鲜人,就这么可怕吗?”
对于任何一个海外移民来说,身份认同永远都是一道难以绕过的坎,这也正是《柏青哥》要发出的另一个拷问。女主人公顺子曾问她的儿子诺亚说:“做朝鲜人,就这么可怕吗?”诺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对我来说很可怕。”这个从小就希望成为日本人而奋发向上的孩子,在得知自己的生父高汉秀竟然是一个黑帮头目时,整个人都崩溃了,最终选择和母亲及家人永远决裂。不仅是诺亚,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作品中的每个人,包括介入这一家人生活的日本人。
关于在日朝鲜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学界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者主张在日朝鲜人有着较强的作为朝鲜半岛族裔的民族认同,一者则认为随着世代交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其民族和自我认同已渐趋多元化。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均抓住了在日朝鲜人社会的某方面特征,但身份认同最终取决于个体的选择,恐怕难以轻易化约。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在日朝鲜人已经历了明显的代际交替。殖民地时期和解放初期渡日的第一代,即《柏青哥》中顺子那一代人(80岁以上),如今只占5%,而像以诺、以撒以及所罗门等在日本出生、成长的第二(50~79岁)、第三代(20~49岁),则分别占41%和45%,此外还有占9%的第四代——青少年群体(10~19岁)。几代人所经历的世事沉浮和人生体验显然是迥异不同的。
顺子那一代所经历的战前时期,日本政府的同化和差别政策是并存的,他们一方面希望朝鲜人成为日本帝国的顺民,乃至对天皇尽忠、献身,一方面却又惨无人道地进行差别和奴役,将朝鲜人视为二等公民。然而,对于被殖民统治这一时代性苦难压弯了腰的第一代来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生存和养家糊口。他们蜗居在人畜杂居、屎尿横流的朝鲜人聚居区,在矿山、工厂挥汗流血,在街头巷尾日晒雨淋,与其说是为了尊严,毋宁说是为了活路。在困苦难耐的岁月里,对解放和回家的憧憬无疑是支撑许多人活着的精神信念之一。
而到了以诺和以撒为代表的第二代,情况已经大相径庭。这一代人经历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虽然由于资本的局限以及进出公职的制度限制,他们的职业选择余地十分有限,但是凭借在柏青哥、烧肉屋、土木建筑、消费金融等行业的长期摸爬滚打,也有不少人实现了经济地位的上升。与此同时,196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增长,日本社会视在日朝鲜人为热衷于黑市交易、拉帮结派的扰乱治安者的认识逐渐退潮,与此相反,开始将在日朝鲜人等社会弱者、被歧视民众纳入社会福利政策的适用对象。从1970年代开始,伴随着在日朝鲜人废除歧视运动的开展,基于国籍的制度性歧视陆续废除,在日朝鲜人进入民间企业和考取公务员的门路不断扩大。自1980年代末以后,随着外国人的涌入和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普及,在构建“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导向下,日本社会对于在日朝鲜人的态度总体上渐趋温和。与此同时,入籍、通婚、取得日韩双重国籍的人数也日益增加。上述一系列变化使得很多在日朝鲜人第二、三代很难再将自己限定为朝鲜人或韩国人,毕竟日本才是他们出生、成长乃至成功的舞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日朝鲜人已经完全融入日本社会。即便他们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作为少数族裔,尤其是作为殖民地朝鲜人的后裔,依然会受日本人的歧视。“肮脏的朝鲜人”,这一殖民地时期延续下来的种族偏见式的暴力性言辞,仍不时无情地提醒在日朝鲜人,他们或许注定了是一群难以被完全接纳的“他者”。事实上,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低迷和日韩之间历史、领土问题的发酵,日本掀起了反韩热潮,而其中就包括了对在日朝鲜人的排斥。
面对这一现实,很多在日朝鲜人选择了隐瞒或者逃避,例如加入日本国籍,或使用“通名”(日本名)代替“本名”(韩文名)。不过,也有一些人顶着学费负担、升学压力和社会偏见,通过接受朝鲜学校的教育,学习朝鲜半岛的语言、历史、地理和文化,坚守朝鲜民族的认同。虽然这些朝鲜学校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资助,且被质疑在为领袖崇拜背书,但是朝鲜学校所提供的民族文化教育,在客观上无疑为这群异乡的他者寻找超越民族国家分野、构筑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种难得的路径。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不应该隐藏或否定自己的民族,也不应该被剥夺学习母语和本族文化的权利。这对少数民族来说也是一样重要的。”一位小学和初中就读于朝鲜学校,却对其间所受的教条式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感冒的在日朝鲜人如是说道。
一个没有差别、认可差异的社会,或许才是能够让他们真正释怀的家。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韩语系副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