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泽·克拉韦利那:回荡百年的“黑色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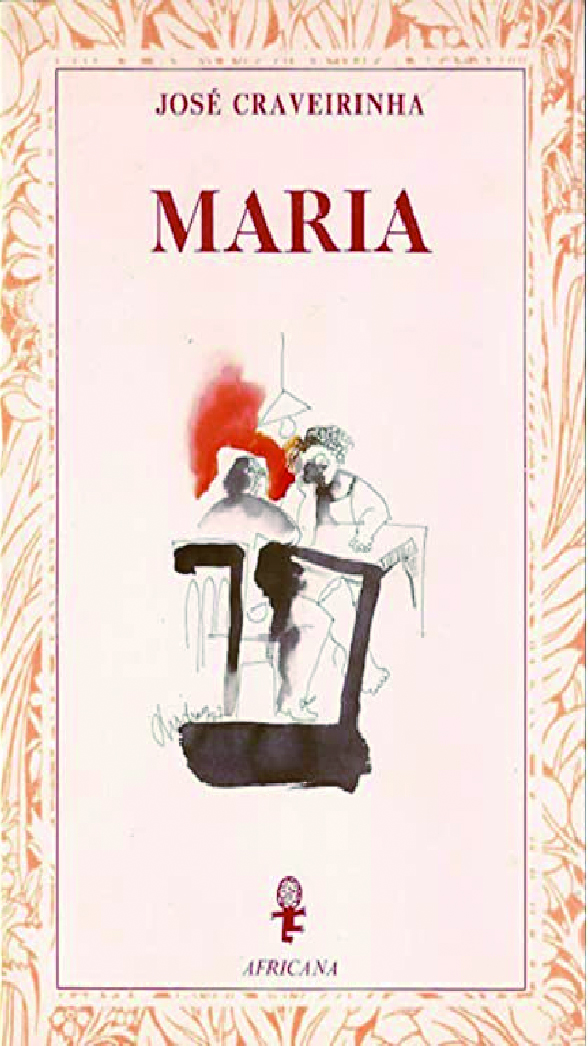
《玛利亚》
1568年至1570年,被誉为“葡萄牙最伟大诗人”的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在莫桑比克岛居住,据说正是在那儿,他对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葡国魂》)进行了最后的修订,这个沐浴在印度洋暖风中的东非岛屿与葡语文学就此产生了最初的联结。
莫桑比克是个盛产诗歌的国度。尽管如米亚·科托等一众为海外读者所熟知的莫国作家以撰写小说出名,他们在本土文坛崭露头角的最初身份却是诗人。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葡国殖民统治期间,相比于出版散文小说,诗歌以其低廉的发表成本、更容易逃脱审查的隐晦语言、篇幅短、易流传等优点成为了莫桑比克早期文学创作的不二选择。被誉为莫桑比克葡语诗歌先驱的鲁伊·德诺罗尼亚在20世纪初写到:“醒来吧,你的沉睡比大地要久……/聆听你进步的声音,这另一个拿撒勒人/向你伸出手并对你说:非洲,起来并前进!”莫桑比克醒来了。随之而来的是40年代涌现的大批诗人与一首首真正属于这片土地的诗歌。若泽·克拉韦利那(José Craveirinha,1922-2003),被称为莫桑比克“最伟大的诗人”,便是这一反殖民革命斗争浪潮中的先锋与灵魂人物。
1922年,若泽·克拉韦利那出生于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尔克斯市(现马普托),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来自于莫国南部的聪加族一脉。与众多同时代的非洲葡语作家相同,克拉韦利那的文学生涯与政治活动紧密相关。青少年时期,十几岁的他加入了当地由黑人与混血儿创立的“非洲协会”,并于1950年成为主席。自40年代末起,将近20年时间里,他以记者的身份为当地的许多知名报刊(如《非洲咆哮》《莫桑比克之声》等)撰稿。在1964年第一部诗集《希谷布》出版之前,他的诗歌大多发表于当地报刊以及诗选中。1965年至1969年间,作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第四军支部的成员,克拉韦利那遭受了葡萄牙国家安全警备总署长达4年的监禁。出狱后,《沥青神赞歌》《卡林噶那哇卡林噶那》《一号牢房》等诗集相继问世。1977年,妻子玛利亚去世,克拉韦利那创作了数百首悼念诗歌,这些作品被汇集成册,以《玛利亚》为题于1988年首次发行,并在1998年的第二版中以更加完整的形式出版。克拉韦利那2003年于南非逝世后,他那些海量未发表作品中的一部分被后人整理成册,以《狱中诗》《情色诗》《贝鲁特的酸椰枣》《柏格塞別墅和其它旅行诗》等名出版发行,并被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等多个版本在海外广为传播。
作为被多次提名诺贝尔奖、第一位获得葡语文学界最高荣誉“卡蒙斯文学奖”的非洲作家,若泽·克拉韦利那的作品范围几乎涵盖了莫桑比克葡占时期的最后30年与独立后的前20年。殖民剥削、民族认同、武装战争、非洲图景、爱与自由、孤独和死亡等成为了永恒的主题。克拉韦里亚将诗歌理解为艺术,他所描绘的现实,首先是艺术意义上的真实,其次才是确切的记录。在其民族主义诗歌中,他擅长以阶级观点展现社会矛盾、在语言上回溯本土语言以追求与大众共鸣,这种写作策略与他作为混血儿的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为非洲葡属殖民地的早期精英,大部分的本土作家都是“穆拉托人”,即黑白混血儿。这一混杂性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他们接受殖民者提供的学校教育,用殖民者的语言进行写作。随着文学书写,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具有批判性的身份,文学创作不仅意味着对个人身份的验证,对于整个国家文化身份的建立更是意义非凡。克拉韦利那很少谈论自己,却在一篇发表于1977年的简短自述中写道:“父亲去世后,我有了另一个父亲:他的兄弟……母亲去世后,另一位母亲出现了:莫桑比克。这一选择缘自我的白人父亲与黑人母亲。”对母族血缘的认同引导了克拉韦利那诗歌中对“非洲母亲”概念以及相关隐含符号的塑造。
这种血缘造就的不可避免的双重性、某些情况下甚至表现为一种剧烈的模糊性令非洲葡语作家带有极强的认同意识,投射在写作中,表现为用语言显化这一欧非文化叠加而产生的冲突。克拉韦利那用葡语写作,却坦言“卡蒙斯的语言/并未将我变成葡萄牙人。/而使我成为了葡萄牙人的兄弟”。他的作品将当地的土著语言“隆卡语”融入葡语叙事,例如,在诗集《卡林噶那哇卡林噶那》与同名诗歌中,诗人试图通过这一当地人在讲述故事时表示“很久很久以前”的土语来寻求与本土读者的共鸣,以期唤醒非洲本土文化中莫桑比克的根源,确立民族文化身份的自主性。
虽然克拉韦利那的每部作品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气息,他的民族主义诗歌按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种作品关于非洲文化与历史,专注于对非洲传统的审视与对非洲价值观的强调。诗人赞颂莫桑比克乃至非洲景观、语言、口头传统、无形遗产、古老神话与神明,试图激励同胞对历史文化的独有情怀,将在殖民统治中被征服方的明显文化劣势转化为创造力,以此救赎本土文化。这一题材从诗集《希谷布》的标题便可以感受一二,这种莫桑比克南部盛行的传统战歌与战舞作为抵抗殖民统治的象征,成为了一种被包裹在风雅艺术形式中的隐喻式反抗。在《我想成为一只乐鼓》一诗中,作者用急促连贯的韵律语言模拟出非洲鼓打击时的节奏:“年迈的乐鼓发出嘶吼/噢古老的万众之神啊/请让我成为一只乐鼓/只是那热带燥热夜晚中呐喊的乐鼓……只是故乡满月下怒吼的古老乐鼓。/只是故乡烈日中鞣制皮革打造的乐鼓。/只是故乡坚硬树干内打磨而成的乐鼓。”富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所传递出的高强度节奏与形象成为了一种群族主体性的建构,克拉韦利那在提醒同胞曾经拥有并亟待光复的美丽故土的同时,将莫桑比克的文化信息与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非洲国家形象传达给外部世界。
在第二类作品中,克拉韦利那对殖民时期黑人的遭遇进行了文学再现。他最广为流传的诗歌作品《黑色的呐喊》堪称这一主题下的巅峰之作。“我是煤炭!/我必须在抽剥中燃烧/直到燃烧成咒怨的灰烬/活活燃烧,像我的沥青兄弟一般/直到再也不是你的矿产/主人!……我是煤炭!/我必须燃烧/用我点燃的火焰将一切焚尽。/是的!/我将成为你的煤炭/主人!”诗人用重复的词汇、短句、韵尾与标点对剥削黑人劳动力的欧洲殖民主义进行了抗议与讽刺,展现了被强迫在矿区工作的莫桑比克人民的悲惨生活。自莫桑比克文学诞生初期,前述混血作家群体的写作诉求之一便是为了当地人——自己的“黑人兄弟”能够拥有与葡萄牙公民同样的社会权利。在他们的笔下,自小成长的世界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主题,非裔族群成为了文学真正的主角,获得了文字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与尊严。因此有论述认为,非洲文学的对立面并不是殖民国文学,而是以霸权视角再现非洲与非洲人的殖民文学。克拉韦利那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不觉得捍卫黑人性是种族主义的表现……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认可的方式。一个人强调自己的肤色是为了征得平等,而不是追求优越。”他对莫桑比克社会中黑人同胞所受不公待遇的担忧无处不在,从早期的民族主义诗歌延伸至带有强烈个人经历的监狱诗歌中。这种克诗美学的表现结果即为“莫桑比克性”——一种自我与集体认同的信仰体系的整体建构。
即便克拉韦利那的民族主义诗歌与政治宣传挂钩,这种政治性显然无法阻止另一类有关个人感情经历的诗句出现。如果说在反殖民主题的作品中,集体性的“我们”形象占主导地位,在为纪念亡妻玛利亚而写就的诗歌中,克拉韦利那的个人性则达到了顶峰——挽歌牢牢占据了诗集《玛利亚》的中心位置,不断的思念与回忆在几十首零碎的小诗中展开。
作者缩短了诗歌的篇幅与诗句的长度,许多诗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凸显了作者身为丈夫与故去爱人的生活日常。整部作品像电影的蒙太奇语言一般,所描绘的场景由葬礼上的哀悼转向生活空间与物品,拼接成一幅夫妻生活的长卷。“乌云沉沉的长日。/忧伤的鸟儿立在枝头/啾鸣哀转。一簇/缤纷的繁英/自花冠深处/氤氲出/香气。/痛苦如此/简洁如斯/我们如玫瑰般告别,玛利亚。”诗者所言之物无关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持续的当下。葬礼是玛利亚生命的终点,却是丈夫回忆以及整部作品的起点。重复出现的意象凸显出一个喋喋不休的“我”,忠实伴侣的故去是诗人心中无法释怀的执念。通过诗句,诗人内在情感得到了外溢与释放,这是一场内省与自述,是对个人最亲密生活的记录。由于克拉韦利那政治生涯的风波不断,玛利亚生前是“一位丈夫还活着的寡妇”,在《玛利亚》一书中,克拉韦利那已然成为了那个虽然妻子已故,却生活在“完美”爱情中的丈夫。如同诗人所言,二者在生命中的彼此缺席,是另一种爱情的开始。
诗人与诗互相赋予血肉与灵魂。透过复杂多面的诗歌作品,若泽·克拉韦利那试图表达与探索一种“自我-集体”、“小家-国家”的二元性。一手执剑,一手捧花,这是一个执笔为民族尊严和独立而战的斗士,也是一位用柔情与爱意追思逝去爱人的丈夫。1997年,由于为“人民解放、承认人权、尊重民主自由和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屈辱”做出了重大贡献,克拉韦利那被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授予“友谊与和平勋章”。他与众多殖民期间活跃的莫国葡语作家相同,通过文学传达了一种期待,准确地向人们表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总会到来,探索即将迎来曙光,苦难即将结束。这种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激烈情绪与英勇斗争通过诗歌能够与全世界有着相似革命经历的人民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
2022年恰是这位莫桑比克伟大诗人诞辰100周年。这100年间,我们看到了如路易斯·贝纳尔多·翁瓦那、翁古拉尼·巴卡·科萨、米亚·科托等众多杰出后继者们的出现,带领着莫桑比克文学走向独立和超越。愿这“黑色的呐喊”能够回荡更多个百年,有更多的莫桑比克文学作品为全世界所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