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菊的茶山》创作手记:杏花消息雨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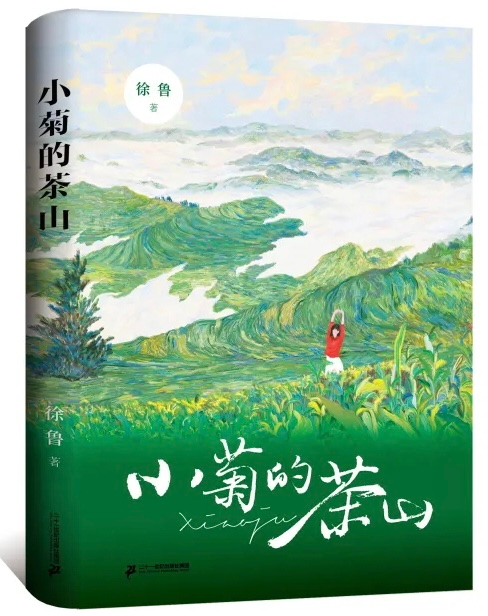
一、夙愿
2019年,一位素不相识的音乐学研究者、湖北科技学院音乐学院音乐系主任栗建伟博士写信给我,说他正在做一个鄂东南民间文化的研究课题,他把自己撰写的一篇长篇论文初稿发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论文题目是《阳新县文化馆鄂南民间音乐工作研究——以徐鲁的文学记载为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从没想过,早些年写下的一些幕阜山地域文化题材的文字(主要是散文),能成为民间音乐研究的素材。不过,栗老师的研究题目也透露出一点信息,就是我与幕阜山区、与鄂南阳新县民间文化的渊源,着实不浅。
三十多年前我在鄂南阳新县人民文化馆工作过多年,所从事的是一种“乌兰牧骑”的工作。我刚到文化馆第一天,一位老馆长、也是鄂东南民间文学专家梁万程就谆谆教导我说:“我们是人民文化馆,你来了,我们又多了一名乌兰牧骑队员!”他还给我解释说,“乌兰牧骑”的工作就是要深入到幕阜山区最偏远的农村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
幕阜山区横亘在赣、湘、鄂三省交界处。我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幕阜山中的穷乡僻壤,去搜集民间故事、歌谣和小戏唱本,就像当年的格林兄弟深入德国偏远的乡村,去收集民间童话故事一样,同时也给一些乡镇文化站和乡村小剧团修改戏本,做一些创作和演出的辅导工作。这种身份当时叫“文化辅导干部”。除了收集和整理民间文学,还要经常送文化下乡,要去辅导和组织乡镇和村里的业余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活动。比如,村里或者乡镇文化站要组织演采茶戏,如果正好我们这些人在场,还要临时帮演员改戏本、写幻灯字幕,帮着搭戏台、搬道具、甚至给演员化妆,等等。遇到“三夏”和“双枪”的农忙时节,就要挽起裤管,下田帮着割稻、栽红薯秧、运送秧苗,等等。这是真正的“深扎”,也是完全意义上的“三同”,比现在的作家浩浩荡荡组成团去“采风”,要艰苦得多,也深入和扎实得多。
那时候,幕阜山区一些偏远的小山塆还没有通上电,需要走夜路时,房东就会举着松明子或点上“罩子灯”,给我们引路和照明。在幕阜山区的崇山峻岭间走村串户、搜集民间故事和戏本的那些年,是我迄今为止最“接地气”的一段生活。饥了饿了,走进任何一户人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散发着柴禾气息的锅巴饭和老腊肉。渴了乏了,就猛喝一顿山泉水。翻山越岭走累了,呼啸的山风为我擦拭汗水。当年幕阜山区也还没有实行禁猎,我也曾被允许跟着老猎户去打过两次猎,猎枪就是长长的火铳。有一次老猎户打到了一只野物,他告诉我这叫“豹猫”,山里人又称“飞虎”。现在,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当然都是当地的保护对象了。
鄂南地处吴头楚尾,方言里犹带吴音,而且保存着许多古雅的字音,比如把耕田叫“劝春”,玩耍称为“戏”,穿衣称为“着衣”,给客人添加酒水,叫“酙酒”,称你为“乃”,称我为“阿”或“吾”,称他为“其”,把树叶叫“木叶”,洗脸叫“抹脸”,棉背心叫“棉褡魂”, 下小雨叫“落细雨” 太阳叫“日头”,白天称“日分”,夜晚称“夜分”,天亮叫“天光”,放牛叫“秧牛”,砍柴叫“斫柴”,选种叫“秧豆”。倘若遇到什么稀奇事或值得夸赞的场景,上了年纪的老人嘴里,瞬间就会蹦出了一两个现在已经不大使用了、但在幕阜山区依然保存至今的文言叹词:“噫,好矣哉,好矣哉!”
理解力栽培下的东西,季节会使它们成熟。虽然离开了云遮雾罩的幕阜山区已经多年,但那里的草木和牲畜,它一年四季的雨丝风片,也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还有我所熟稔的那些茶山、竹林、橘园、稻田、山坳、河流、渡口、井台、凉亭……也都在我的心底记忆和保留得清清楚楚,并且一直在温暖地爱着和回忆着。所以近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本类似沈从文的《边城》和孙犁的《山地回忆》式的小说。《小菊》的完成,也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夙愿。
二、文心
在创作之初,我这样设想着:要努力去写出一部带着四月茶山的清新与明丽的色调,既能展现幕阜山区的地域风情之美和人性之美,又能呈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时代气息的小说。
我很喜欢沈从文、孙犁两位老作家那种半纪实、半虚构的小说文体。沈从文的作品暂且不说,我读孙犁的《琴和箫》《荷花淀》《芦苇荡》《采蒲台》《山地回忆》《蒿儿梁》《纪念》这些短篇,甚至到他晚年创作的“芸斋小说”系列,其实很难分清,这是些虚构的小说,还是些真实的纪实故事。“我”(作者)自己的足迹、身影、声音、行止、所思所感,散落在每一篇短篇故事的字里行间。《山地回忆》写的是“我”在太行山区打游击的日子里,有一天来到一个熟悉的小村外的小河边,其中有一个细节:在河边洗菜的小女孩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这样的细节和感情,显然是来自作者真切的经历与体验。
我对于幕阜山的感情也是如此。当我在暌违多年之后,重新站在富水河畔,看着暮色里的枫林渡口、茶亭,还有远处的山岭、田畈和一座座灯火初上的小塆……那一时间,我的心里也涌上了与孙犁在《山地回忆》里同样的感受:这些都像是我的故园一样,分别得再久,也永远不会失却和淡去那份温暖、那份亲切的感觉。我甚至感到,我和这里也是永远不能分离了!
在这部小说里,我采用了孙犁小说的那种既是写实的、又带点抒情意味的散文般清新明丽的笔调,描绘了在全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赣湘鄂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区的奋斗故事与现实风情画卷。我试图用云雾缭绕的青翠茶园、风雨百年的义渡渡口、农家书屋的灯光、飘飞在青山绿水间的采茶戏和采茶山歌、白云深处的朗朗书声……构成了新时代山塆人家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图景。小说的故事以生活在富水河畔枫林渡的阿通伯和他的女儿阿香与阿秀、外孙女小菊三代人的生活日常为主线,着力刻画老一辈人对乡土的眷恋与守护,新一代幕阜山少年的觉醒、奋进与自强不息,以及风风雨雨中永难泯灭、在乡村振兴的劲风中更加焕发的人性之美和如细流汇聚般的时代力量。
这样的构想,这样的文心,当然是明亮和美好的。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热情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成什么风格的,就意味着肯定会写成、能写成什么风格的。其实未必如此。小说是否达到了我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是读者说了算的。
我很感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文学中心的谈炜萍、王雨婷两位年轻的编辑朋友,感谢她们耐心的等待和对我创作期间殷勤的照顾。好编辑总会把作者的作品视若己出。小说出版后,炜萍在《中华读书报》上刊发了一篇书评《山乡变革的故土恋歌》,其中有几句评价洵为公允和中肯,也正好道出了我的文心与追求:“小说采取半纪实的叙事方式,循着主人公即作者的足迹,在散发着泥土与春茶气息的旅程中,围绕富水河畔枫林渡的阿通伯一家三代的生活经历,全景展现了幕阜山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作者笔触极具江南风情与韵味,但在这乡土文化的探寻中,既充盈着作者浓烈的乡土眷恋情愫,也隐含着作者客观、冷静的反思。”这也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读者”。
三、人物
《小菊》出版后,我在微信圈里说道:“人间多奇葩,吾独爱小菊。”虽是戏言,却也道出了我对小菊这个人物的喜爱。作者写小说,对于故事里的某些人物,自然也是视若己出,不爱则已,爱之弥深的。
《小菊》是一部儿童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小菊、小芬、万新福、水芹等新时代山区的少年形象。他们是一群传承清新朴素的采茶戏的少年人,也是未来的幕阜山区新生活的主人。尤其是小菊,我想通过这个小姑娘的形象,让读者看到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志存高远、敢于担当的精神特征,以及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这一代少年对于家乡的山河、历史的认知与热爱。
小菊的性格跟她的妈妈阿香一样,有点“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她对自己的同学、从小患有肌无力疾病的小芬的帮助,视若己任,和同学一起组成了“爱的小船”行动小组,表现出一种坚毅的担当勇气。在小菊、韩叔叔等人的影响下,原本有着强烈的自卑心理的小芬,也像一棵获得阳光照耀、雨露滋润的小树,渐渐舒展开了自信的枝丫。我在小说里写到一个情节:坐在小船上,小菊和小芬这一对亲密无间的好伙伴,东一句、西一句的,又打开了说说笑笑的话匣子。“我”一边帮着阿香撑船,一边默默听着她们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接着就是两个小姑娘的长长的一大段对话。这时候,小船即将到达对岸,晨雾正在悄悄散开。我想,从两个小姑娘的这段对话里,不难感受到新时代少年的那种不从流俗、奋发向上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除了小菊、小芬、万新福、水芹等新时代山区的少年群像,我在小说里还塑造了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退伍老兵韩燕来,文化站长刘耀煌,枫林渡口两代撑渡人阿通伯和阿香,采茶戏传承人阿秀、肖冬云、小玉,大学生喜子,还有文娟、红菊、红菱等年轻一代的形象,展现了他们为守护美好的乡土文化、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付出牺牲和艰辛、自强不息的奋斗故事。
肖冬云、阿秀、文娟、红菊这一代年轻人,在艰辛的山区环境中长大,有的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忍受着委屈,离开山区去往远方,进入了灯光炫目的城市。虽然是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和角落里,但是只要不虚度自己的年华,只要脚步走得真实、踏实,他们就不仅分担了这个时代的风霜和艰辛,也分享了这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进步和收获。我在小说里书写了她们各自的故事,同时也透露出“我”的一种最深切、最质朴的感情:从心底里祝愿新一代幕阜山的孩子们,祝愿那些离开了家乡的小山塆,散落在他乡的角角落落的幕阜山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都能生活得快乐和幸福一些,并且都能平平安安的,莫要叫老家的阿爸阿妈、阿公阿婆们担惊受怕。
在驻村工作队队长和退伍老兵韩燕来、文化站的老站长刘耀煌、从摆渡人变身为农家书屋创办者的阿通伯这些人物身上,读者也可看到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为古老的山区带来的新观念、新变化和新气象,感受到一种春潮漫卷、山溪奔腾般的时代力量。在风风雨雨中永难泯灭的质朴的人性,又在乡村振兴的劲风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也希望能在缓缓展开的山乡风情画卷中,闪耀出一种永恒的人性之美,写出人性的光亮与温暖、质朴与坚韧。
四、风俗
因为曾在幕阜山区生活和工作多年,对幕阜山区的地域风习、文化风情和人情世故,有一些切身体验和积累,所以,我在小说里也写了不少属于地域文化和风情的内容与细节。例如阳新采茶戏的守护与传承,稻场上的采茶戏演唱,“鄂南落田响”等插田号子演唱,采春茶时飘飞在层层绿崖和茶梯之间的采茶歌,还有对哭嫁之夜等场景的描写,都属于这一类情节和细节。
我在小说里写到春工忙忙的早晨,伴着一阵阵朗朗笑语,韩燕来请来给阿通伯家帮忙开园采春茶的小嫂子们,像仙姑下凡一样,一个个驾着飘绕的晨雾,袅袅娜娜地络绎而来。这时,有的老爹看着街子上突然出现了这么多“仙姑”,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在这地处古代吴头楚尾的幕阜山区,依然保存至今的文言叹词:“噫!好矣!好矣哉!”阿通伯更是喜得合不拢嘴,笑着对骑着自行车赶过来的燕来说:“燕来哟,你请来的茶姑,个个赛过仙女,怕尽是挑长得好看的要,不好看的不要咯!”我在小说里,尝试适当采用一些鄂东南和赣北的民俗与风习,呈现幕阜山区的淳朴风情与美丽乡愁,也有意无意地添加了不少对山塆人家一些独特的方言遗存的重现。
也算是一种缘分,这部小说的编辑团队的炜萍、雨婷两位编辑老师,少女时代皆在幕阜山区度过,因此对小说里的方言、风习细节皆能莞尔会心。“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我想,这同样是我在创作时对读者们暗含的一种期待。
因为是有意追求一种散文或散文诗般的明丽与恬淡风格,所以,《小菊》这部小说与我前几年写的《罗布泊的孩子》《追寻》相比,并不以大开大合的故事见长,而是用一些鲜活的和散发着泥土与春茶气息的细节描写,撑起带有乡土韵味的叙事,从缓缓展开的风情画卷中,去写出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温暖与坚韧,去呈现出春溪奔腾、细流汇聚般的时代力量。
最后,再次感谢炜萍、雨婷这个文学团队的耐心等待和悉心照顾;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把这部作品列为2022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感谢著名小楷书法家唐传林先生(他也是《小菊》里的那位驻村第一书记、退伍老兵、先后担任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长的韩燕来的人物原型)为本书题写书名。
2021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爷爷的苹果园》,是以乌蒙山区的脱贫攻坚为背景的;2022年出版的《小菊的茶山》,以幕阜山区的乡村振兴为背景。《爷爷的苹果园》是我创作计划中的“美丽乡愁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菊的茶山》是第二部,2023年将会完成这个三部曲的第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