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个体与时代的“影像之书”
2022年10月6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凭借其“勇敢又确切地书写从个人记忆中挖掘出的根源,疏离以及集体约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其近50年的写作生涯中,安妮·埃尔诺共出版了20余部作品,其写作特色主要是从个体生活切入,关注社会问题,聚焦个人与时代的联结,并且创造了一种融合个人史和时代史的“无人称自传”。除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新头衔之外,今年安妮·埃尔诺还尝试了“第一次跨界”,她和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David Ernaux-Briot)共同导演的纪录片《超八岁月》(Les Années Super 8)于5月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上亮相,并计划于12月在法国院线上映。全片时长约一小时,原始素材来自于1972年至1981年间他们家用一部超8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后期经过剪辑,并配有安妮·埃尔诺本人亲自撰写和朗读的旁白。
安妮·埃尔诺生于1940年,在诺曼底的小镇伊沃托(Yvetot)长大,她的父母在当地以开杂货店为生。埃尔诺先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主攻文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法语教师。60年代前后,她嫁给了菲利普·埃尔诺(Philippe Ernaux),并生下两个儿子:哥哥埃里克和弟弟大卫,后者也就是本片的另一位导演。1974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空衣橱》(Les Armoires vides),1983年出版了《位置》(La Place)并于次年荣获勒诺多文学奖。在出版于2008年的作品《悠悠岁月》(Les Années)中,作家抛弃了第一人称“我”(je),而是采用无人称泛指代词“我们”(on)进行写作,通过一张张照片引出对过去的回忆,将个人的小事与时代的大事融合在一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法国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堕胎合法化、性解放、萨科齐当政等等,时间在她的笔下无情地流逝着。《悠悠岁月》一书出版后斩获多个法国文学奖项,并且成为一代法国人,特别是一代法国女性的集体记忆。安妮·埃尔诺的文学成就不一而足,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儿子大卫·埃尔诺-布里奥生于1968年,先后在安纳西和塞尔吉-蓬图瓦兹长大(正如纪录片中所呈现的那样),在大学期间他主攻科学方向,毕业后从事相关新闻节目工作,他参与了电视节目《E=M6》和《原来如此》,还为一些数字教育平台编导了《机器剧场》《语料库》《艺术与运动》等迷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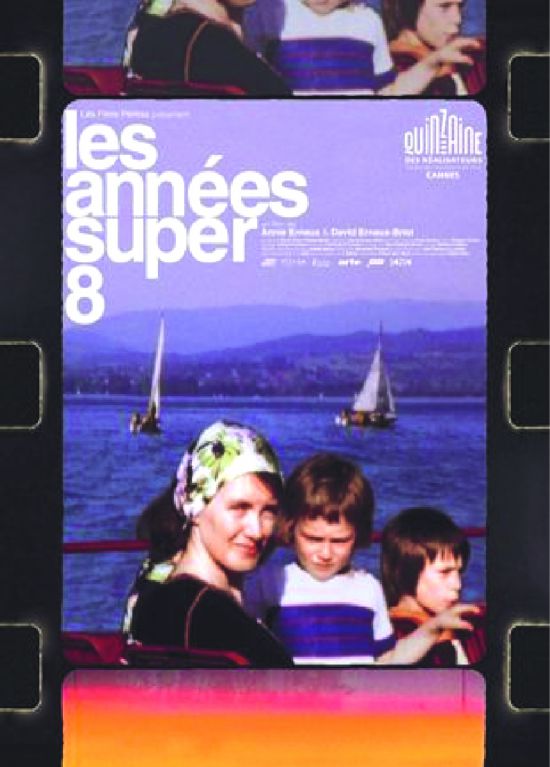
《超八岁月》纪录片海报
事实上,纪录片《超八岁月》也可以看作一曲“六手联弹”,因为其素材几乎都是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菲利普·埃尔诺拍摄的。表面上看,它是埃尔诺家的影像档案,记录了一家人在生日、圣诞、假期的日常图景,但同时,它犹如一扇窗户,呈现出当时法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特征。正如导演安妮·埃尔诺所言:“当我回看我们在1972年至1981年期间拍摄的超八胶片时,我意识到它们不仅是一份家庭档案,也见证了1968年后的十年间一个社会阶层的品位、休闲、生活方式、热爱与期待。我想通过引用我在那些年写的日记,把这些无声的影像融入到个人、历史与社会的交汇叙述中。”超8摄影机拍摄的画面均没有声音,安妮·埃尔诺为它们撰写了文本,可以说,纪录片《超八岁月》和作家的其他作品一脉相承,并且因影像的介入弥补了文字的短板,进一步拓展了其文本维度与丰富内涵。
作家笔下的几个典型元素在纪录片中清晰可辨。首先是社会阶层。彼时安妮·埃尔诺的丈夫担任安纳西市副秘书长,一家人住在市政府分配的房子里。她在纪录片中介绍,在当时,超8摄影机是一件比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更令人心动的东西。菲利普·埃尔诺拿到相机后热衷于拍摄住所的装饰,包括精美的墙纸、从古董店淘来的小玩意儿等等,它们和超8摄影机一样,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中产阶级的象征标志。不仅如此,在上世纪70年代,拥有“闲钱”的中产阶级还热衷于去远方旅行。超8摄影机也记录下了他们一家前往智利、摩洛哥、阿尔巴尼亚、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国家的画面。1972年,在《新观察报》的邀请下,埃尔诺夫妇二人来到智利,彼时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推行了一系列“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包括进行大型工业国有化,给儿童提供免费牛奶,深化土地改革等等。在智利的所见所闻触动了安妮·埃尔诺,她想起了自己在20岁立下的誓言:我要写作,为我的阶层复仇。镜头之下,个人的游历与时代的变迁合二为一,安妮·埃尔诺以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视角窥探着法国乃至世界的变化。
在纪录片中还可以看到安妮·埃尔诺母亲的身影,这一人物形象曾出现在《位置》《一个女人》等其他作品中,而母亲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正是作家拼命想要叛逃的阶层。安妮·埃尔诺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便离开伊沃托来到安纳西和他们一起生活。然而镜头下母亲的形象略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对家中墙上的装饰有不同的见解,常常身穿一件带口袋的花罩衫,或许是受到贫穷出身以及战争期间饱受饥荒之苦的影响,她总要在口袋里放一条手帕和几块方糖。安妮·埃尔诺说,母亲和丈夫代表了其社会旅程的两个端点:起点和终点。安妮·埃尔诺无疑实现了她的“阶级叛逃”,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她想要说的话还很多,甚至可以认为,她的文学之路恰恰开始于她有意识地对“阶级叛逃者”这个社会学概念的探讨与回应。
在《超八岁月》的独白里,安妮·埃尔诺称,她常常在没有课的下午进行写作,写那些教育和文化如何让她叛逃自己所出生的社会阶级的故事。用她的话来说,在一个温柔的年轻母亲形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迷恋写作的女人,这个女人想要把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全部写进一本让人感到震撼的小说之中。只不过,她的写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她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丈夫也好,母亲也罢。当她陪同丈夫出席活动时,她心里想的都是家中藏在抽屉里的创作手稿,它宛若一颗定时炸弹,悄悄埋在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内部。夫妻二人的情感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超8摄影机拍摄的家庭画面越来越少,亲密时光似乎不复存在。安妮所接受的理念是自由和男女平等,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奶妈”,是“沉默的后勤管家”,甚至在纪录片开头,当她提到超8摄影机多是丈夫在使用拍摄,一部分原因也是根据夫妻共同生活里的性别分工而定。1980年夏天的西班牙之旅,安妮清醒又痛苦地意识到:“我在他的生活中已然是多余”。念完这句话,独白便戛然而止,镜头转向一场斗牛表演,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只逐渐筋疲力尽的公牛,最终躺倒在地,被拖出斗牛场。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整个国家处处洋溢着充满希望的喜悦气息,然而,随着《被冻结的女人》(La Femme gelée)的出版,家庭关系愈发紧张。次年,二人分开,丈夫带走了超8摄影机,把之前拍摄的全部胶片和投影设备,还有两个儿子,留给了安妮·埃尔诺。
时间流逝,胶片在角落里静静地沉睡着,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安妮·埃尔诺和儿子再次观看这些影像。尘封已久的回忆再度开启,镜头里的很多人却早已不在,包括安妮·埃尔诺的母亲和前夫。在安妮·埃尔诺眼中,这些在时代大背景之下于不经意间拍摄的家庭生活碎片构成了一段无声的时光,而这段无声的时光需要用词语赋予以意义。于是有了这部《超八岁月》。在纪录片的最后,安妮·埃尔诺用温柔却充满力量的声音动情地说道:“这是一个家庭自传的片段。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能让我回望人生至关重要的那几年的契机,重新找寻一点点洒在过去之上的光芒,一束金色耀眼的光芒,就像那些年乔·达辛在歌曲《秋老虎》中唱的那样。”
《悠悠岁月》中译本出版后,安妮·埃尔诺特别撰写了一篇“致中国读者”,她在文章中提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无独有偶。在作品合集《书写生活》(Écrire la vie,2011)的前言中,安妮·埃尔诺写道:“既不是我的生活,也不是他人的生活,甚至不是某一种生活。生活的内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人们以各自的方式经历着:身体、教育、对他人的归属、疾病、哀悼。”纪录片《超八岁月》远非简单的怀旧,它见证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一个阶级和一个时代。个体的光芒照亮幽暗的历史,集体记忆构建于个体记忆之上,今日的《超八岁月》与彼时的《悠悠岁月》遥相呼应,成为一本个体与时代的“影像之书”。
- 冷知识:《悠悠岁月》暗含法国知识女性阅读史[2022-10-09]
- 获奖之后,安妮·埃尔诺会成为图书市场下一个爆款吗[2022-10-09]
- 安妮·埃尔诺:勇敢且慷慨的女性写作者[2022-10-09]
- 安妮·埃尔诺:创造“无人称自传”[2022-10-08]
- 安妮·埃尔诺:我们的语言、历史不一样,但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2022-10-07]
-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2022-1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