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云雀自西至东:雪莱在中国
今年是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逝世200周年。自1905年这位伟大诗人的画像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开始,100多年来,中国文学界对他的译介、接受与学习几乎是全方位的,其广度和深度非同寻常。雪莱经常被称为“希望的诗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西风颂》中的诗句不断被世人传唱,曾激励无数人坦然面对困难,满怀信心迎接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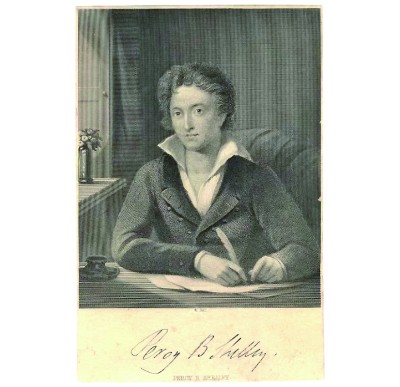
雪莱像,威廉姆绘
一代青年人的偶像
1822年7月,雪莱意外葬身大海,还不满30岁。1922年至1924年间,他的画像和纪念文章出现在包括《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国学丛刊》《学衡》《学灯》《创造》季刊在内的中文报刊中。事实上,当时掀起了一场较大规模的雪莱百年纪念活动,以至于在鲁迅创作于1925年的爱情小说《伤逝》中,诗人雪莱已经成了一位被年轻人挂在墙上的浪漫偶像: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涓生从杂志上裁下来的雪莱“最美的一张”半身像,其实并非鲁迅的拟浪漫想象,而是可验证的写实。从小说中貌似不经意的细节可以推断出的是,雪莱在当时年轻男女的心中,已经是某种形象的代表,以至于追求自由爱情的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而涓生则在子君低下头便断言她“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
这幅画像还出现在胡也频发表于1928年的小说《北风里》中。穷困潦倒的年轻作家珍藏了一幅雪莱画像。为了救穷,他终于不得不将其卖出,却遭到了当铺老板的奚落。雪莱之于这位年轻人,是偶像般的存在。而画像在当铺老板眼中的一文不值,则暗示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位青年幻想的破灭。
而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人视雪莱为偶像。比如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曾经评价当年的胡也频说:“由于崭新的生活使两人感情皆在眩目光景里游泳,海军学生(即胡也频——引者注)当时只打量作英国的雪莱。写诗赞美他的同伴,似乎是他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沈从文说的是和丁玲恋爱时的胡也频。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曾被视为雪莱似的人物。处于蜜月中的他在完成《边城》之后,曾向林徽因倾诉自己的感情困扰。林徽因仿佛发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现代人”:“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感情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于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自己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到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林徽因由雪莱想到了徐志摩。徐志摩曾被世人誉为“中国的雪莱”。但钱钟书说:“徐志摩先生既死,没有常识的人捧他是雪莱,引起没有幽默的人骂他不是歌德”,而事实上,“志摩先生的恋爱极像雪莱”。
徐志摩本人对雪莱也极为钟爱。他在发表于1923年的文章中这样评价雪莱:
他是爱自由的,他是不愿意受束缚的。他是“不愿意过平凡的生活的”……但是仅仅爱自由的精神,热烈的利他情绪并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诗人。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对于理想的美有极纯挚的爱,不但是爱,更是以美为一种宗教的信仰……他又说,诗人以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的精神来测度人情的深浅人类的境遇。诗人是接受灵感的祭司,是世界的立法者。
徐志摩似乎对雪莱的一切有着深深的认同。他说自己“最爱中国的李太白,外国的Shelley。他们生平的历史就是一首极好的长诗”。对雪莱作出如此深刻的体认和评价,恰恰成了他自己传奇一生的注脚。梁实秋认为徐志摩这种单纯的追求和信仰,换个说法,其实就是“浪漫的爱”:“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陆小曼在回忆徐志摩时提及:“他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他覆舟的死况。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世人谈起就寄与无限的同情与悲悯!’”
不仅仅是林徽因、陆小曼,吴宓也认为“以志摩比拟雪莱,最为确当”。事实上,他坦陈自己也是雪莱的崇拜者。吴宓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大师白璧德,弘扬传统道德,这与实际生活中压抑不住的浪漫激情产生剧烈的冲突,因此一生殉道殉情,缠绵郁苦。他把自己周遭的女性与雪莱感情生活中的一一作比:“我的Harriet幸未投河自尽;我所追求眷恋的Mary,却未成为Mrs.Shelley;是的,种种都合适,只是我的Mary未免使我失望。我的痛苦,自然是我所自造,应当自己负责,不错。但是,我何能比志摩,遑论雪莱。”

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方然译),桂林雅典书屋1944年版
浪漫的启蒙者
虽然仅仅活了不到30岁,但是雪莱是一个有着复杂情爱经历的诗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情感经验,都具传奇性。上面引文中,吴宓提到的Mary,是雪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雪莱。她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作者。这部作品的另一个名字叫作《现代的普罗密修斯》,是她在20岁完成的。而雪莱在几年之后写出的代表作,则名为《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两部作品都与“普罗密修斯”(今译“普罗米修斯”)相关,不难看出两人在创作中的紧密联系。
已婚的雪莱爱上了17岁的玛丽并与之私奔。玛丽有着不凡的出身,与雪莱对“智性美”的期待相契合。她的母亲玛丽·伍尔斯顿克拉夫特,是女权主义先驱。父亲是重要的思想家威廉·葛德文。玛丽父母倡导的女性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都对雪莱产生了深刻影响。
也不能忘记雪莱当时的妻子,吴宓提到的Harriet(哈丽雅特)。她比玛丽大一岁,同样是在17岁爱上雪莱,两人已育有一个女儿。在丈夫和玛丽私奔后的1816年,被抛弃的哈丽雅特自杀了。之后玛丽和雪莱二人结婚。他们住在泰晤士河畔,分别创作了自己重要的作品:玛丽基于他们在日内瓦和拜伦等人一起讲的鬼故事,创作出了《弗兰肯斯坦》,雪莱则写出了《伊斯兰的起义》。要特别提到的是,在哈丽雅特死后,她的家人对雪莱提起法律诉讼。大法官认定雪莱所持有的无神论是邪恶的思想,于是剥夺了他对与哈丽雅特所生两个子女的抚养权。1818年,失望并身患肺病的雪莱和玛丽再次前往意大利。这一次离开之后,雪莱至死都未回过英国。
雪莱在1821年的长诗《心之灵》中写下了自己的爱情观:
我从来没持有
一般人所抱的信条:我不认为
每人只该从人世中找出一位
情人或友伴,而其余的尽管美丽
和智慧,也该被冷落和忘记——
这就是今日的道德规范,它成了
许多可怜的奴隶所走的轨道:
他们在世俗的通衙,以疲倦的脚步
直走向死人堆中的家——坟墓,
总曳着一个友伴,甚至是一个仇人,
看呵,这旅途多漫长,又多么阴沉!
真正的爱情不同于黄金和泥土,
它不怕分给别人,越给越丰富。(查良铮译)
他说:“人总是有所爱的,爱这或爱那,本是人之常情。但我得承认,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说,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而我的过错就在于,欲在一堆尘俗的行尸走肉里寻求一个也许会永存不朽的形象。”
应该说,雪莱的爱情观给了中国当时的新文人多样的启发。一方面,这契合了他们当时希望摆脱旧传统婚姻制度的束缚,进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另一方面,雪莱的爱情观代表着一种普遍存在于浪漫主义者身上的特质。可以说,在当时,雪莱身上代表着自由、浪漫、革命,意味着打破一切道德束缚,追求爱情,追求自我真实的部分得到了放大,因此他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偶像。然而,鲁迅笔下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在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雪莱与哈丽雅特的感情跟涓生与子君的何其相似!也许这是将近中年的鲁迅前瞻性地看到了青年人对爱情盲目的追求可能带来的悲剧。
多年后,张爱玲也反思过这场追求爱情的革命。小说《五四遗事》中,1924年的一个夜晚,两位男青年和两位女学生在湖上泛舟约会,月夜下男青年朗诵着雪莱的诗,打动了两位女孩的心。在小说结尾,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的范小姐最终嫁给了曾经一起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章先生,然而“这已经是1936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章先生’拥着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那位被五四倡导的自由恋爱观念启蒙了的新女性就这样又回到了旧的轨道中。张爱玲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对迷恋浪漫主义的男女主人公的讽刺,契合了世界文学中新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对雪莱和浪漫主义的嘲讽。
反抗的革命诗人
当然,作为1905年和拜伦、雨果、歌德、席勒一起被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介绍进中国的世界文学中的经典诗人,雪莱在中国,绝不只是被当作一个浪漫偶像所接受。他的诗论作品《为诗辩护》曾被叶芝称为“英语中对诗歌的最深刻的论述”,其中“诗人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等文学启蒙和救亡的思想,与20世纪初苦苦求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相契合。而他作为诗人所具有的多样性,被译介者们在中国不同时期进行着各有不同的选择、理解和接受。
雪莱曾创作出用英语写就的最伟大的政治抗议诗歌。1819年,远在意大利,他听到了“曼彻斯特大屠杀”的消息。这激起了他难以压抑的义愤和强烈无比的同情。“只要协力同心坚定不移,多数就能控制少数,就像一些年以后被历史进程所标明的那样,这伟大的真理使他渴望着教会他的同胞如何反抗。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的支配和鼓舞下,他写出了《暴政的假面游行》。”玛丽这样写道。雪莱写出了《给英国人民的歌》《1819年的英国》和《暴政的假面游行》等反映英国现实、号召人民起来反抗的作品。
虽然雪莱的很多诗歌被视为一种政治预言,但是在他看来,诗歌的本质是想象。如果诗歌必须具有真与美,最终达到善,那么必须通过扩大想象来取得。他认为一切诗歌都具有独白的性质,“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唱歌来慰藉自己的寂寞;诗人的听众好像为了一个听得见却看不见的音乐家的绝妙声音而颠倒的人……”听众和诗人之间的“看不见”的关系,才是创作者最富想象力的阶段。
对未来美好生活和人类春天的憧憬,对“黄金时代”的预言歌颂,这些构成了雪莱后期诗剧的主题。他宣扬宽恕、善良、仁爱等道德品质,特别强调人类爱的力量。但需要注意到的是,雪莱的“爱”,并非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他将“爱”置于宇宙万物之间,成为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通感,是一种精神的共振、情感的共鸣,是人间的共同感受和共同体验。
雪莱经常被称为“希望的诗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西风颂》中的诗句不断被世人传唱。但必须看到的是,恰恰是这首诗表现出雪莱心中,“希望”与“绝望”如影随形。如果雪莱对人类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希望一定与季节周期相一致,毫无疑问,如果春天紧随着冬天,那么冬天也同样尾随着春天。诗人内心对这令人悲哀的规律的清醒意识,使他对绝望有着更切痛的认识。而雪莱的伟大在于,他并不屈服于绝望,他依然相信。
在《生命的凯旋》这部并未完成的诗作中,诗人描写了地狱的景象。人们在狂奔,“生命战车”开过来,身后都是被生活征服的囚徒。他写道:
我已爱过恨过怕过痛苦过,
作过而且活过。
…………
征服我的
只是我的心,无论是年岁、嘲弄,
眼泪,或是现在的坟墓,都难以
使它屈服。(江枫译)
“生命战车”没有放过他,最后他问:“那么,生命是什么?我高声质疑。”诗在这里中断了。雪莱以他定格的年轻生命,为人生画上了一个戏剧化的“休止符”。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又是另一个“开始”。他在遥远的东方具有了新的鲜活生命。
雪莱是中国文学家们初识浪漫时接触到的西方诗人,他诗歌中蕴藏的丰富和复杂性,见证了他在中国被阐释的多义性。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雪莱是“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的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反抗诗人。而苏曼殊则被雪莱“为恋爱而恋爱”的“哲学家的恋爱者”的抒情诗人形象所吸引。这两种看起来矛盾的特质,最初便被两位中国文人牢牢地赋予在雪莱身上。
与鲁迅强调反抗的破坏性不同,周作人看重的是雪莱的建设性和“理性的力”,认为雪莱哲学中最重要的是“无抵抗的抵抗主义”。当时的创造社文人同样看重革命的雪莱所具有的反抗性,但与鲁迅不同的是,他们具有“艺术家意识”,认为雪莱身上体现的“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化”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他们对雪莱的理解呈现出一种将美学形式注入现实生活中的新形态。
天才的预言家
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的序言中指出:“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最最卓越的人物也无法逃避这种支配。”(邵洵美译)他不仅向我们指明了理解作品的路径,也指明了理解他在中国被接受的路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战火纷飞中的国人必须面对充满苦难的社会现实,袁可嘉回忆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时写道:
那时抗日烽火正烧向西南边远地区,民族生存已到最危急的关头,我们这些流亡异乡的青年学子读到雪莱的《西风颂》那样壮怀激烈的革命诗篇,直觉得自己被一把熊熊烈火烧着了,浑身就要爆炸似的。还有一层,20岁的年青人,对人生、爱情、创作,事业有着许多美不可言的幻想和追求,是天生的浪漫派,雪莱、拜伦等诗人的作品在这些方面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雪莱的人品和作品曾经使我着迷,暗暗拜他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朱光潜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也向同学们深情讲述着雪莱:他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这些都是专业读者感受到的雪莱诗歌中恒常的诗意和美。
而从此时新诗创作上来看,学院派新诗人们摆脱了郭沫若早年直接取自雪莱的“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诗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新诗理论建构中诗人们逐渐抛弃了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但在各自诗学发展的追求中却呈现出丰富的复杂性。
吴兴华、宋淇、徐迟、袁水拍和方然等身份不同、诗学观点各异的诗人都曾在这一时期集中译介过雪莱作品。他们在各自的诗学发展中,或者隐微的不忘浪漫主义中恒常的诗意美学,或者在现代主义的探索中不经意的折返至浪漫主义寻找资源,又或者以新的革命的视角对浪漫主义曾经的伟大事业进行全新的阐释。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充溢着民族复兴、人民革命和个性解放热情的大时代,在这样一个急需抒情的时代,雪莱浪漫诗歌中充溢的对疗救自身的不懈追求、对智性之美的无尽探索和对希望的永恒崇拜,为中国新诗人寻找“新的抒情”提供了资源并埋下了种子。
从20世纪40年代之后,雪莱诗歌具有的功利性和革命性在中国开始具有了压倒性优势。随着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文艺创作方法的倡导,随着马克思所说“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以及恩格斯将雪莱称为“天才的预言家”说法的广泛流传,雪莱逐渐成为革命浪漫主义诗人重要的代表之一。
邵洵美1956年翻译完成了《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他认为“诗人所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是一个故事的曲折的情节,而是一个故事的深刻的意义”。这部作品中涌动了一种生命力量,一股不断向前、向上的无穷力量。正是这种来自人类内在的无可名状的力量使人类挣脱旧的束缚,不断向上攀升。
事实上,普罗密修斯是被自己而非其他人所解放的。他放弃了仇恨,于是他所仇恨的对象也便不复存在,他也不会再被此束缚。当压迫和反抗共同得以毁灭,则是循环论的终结。最终,普罗密修斯的解放带来了整个人类的解放:
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
没有阶级、氏族和国家的区别,
也不再需要畏怕、崇拜、分别高低;
每个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
每个人都是公平、温柔和聪明。(邵洵美译)
进入到新时期,雪莱依然是被广泛译介的诗人代表。1992年是雪莱200周年诞辰,学术界举行了重要的纪念活动。郑敏认为《为诗辩护》是工业革命之后面临物质与精神对立的困境,传统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次挣扎。事实上,当时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印证了雪莱的预言:科学发展强调大脑的分析和认知功能,却忽视了想象和领悟力。雪莱开出的药方是爱和想象力。而陆建德则重新确认了雪莱柏拉图主义的一面,他将雪莱的爱称为“大空之爱”,认为他不爱具体的人,他“爱上了爱”,爱上的是“凌虚蹈空的纯粹理念”。
2000年,《雪莱全集》出版。主编江枫邀请王佐良翻译了其中的《朱利安与马达罗》。这是这首长诗第一次被译为中文,也是王佐良英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的最后成果。这首诗是根据拜伦和雪莱的对话写成的。雪莱借着朱利安的口说道:
束缚我们的原是我们自己的意志。
如不自找心病,我们早已实现了全部的梦,
变得快乐,崇高,恢宏!
何处去寻求爱、美和真理,
如不在我们自己心里?(王佐良译)
雪莱的诗歌总是将人生的苦难和对美好的追求结合起来,正如王佐良所言,“使读者能够在忧郁或沉痛的深渊里,抬起头看见星月”。是的,仅仅宣泄苦难感,不论怎样打动人的灵魂,也许都不能算是诗的最高境界。而雪莱总是能登上一个峰顶,那里永远有希望和理想的光闪烁。就像《致云雀》中写下的那样:
向上,再向高处飞翔,
从地面你一跃而上,
像一片烈火的轻云,
掠过蔚蓝的天心,
永远是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江枫译)
200年后,这只自西至东的云雀,依然在我们心中歌唱,以美妙的音色。
(作者:张静,系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