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耳《鹊桥仙》:能不忆江南

有书友自“云”中来,不亦乐乎?云友读书会成立于2020年5月,是中国作家网在疫情中联络策划的线上跨校青年交流组织。此读书会面向热爱文学的青年,通过线上学术沙龙、读书分享、主题演讲等活动,推动青年学人的文化与学术交流,力求以文会友,激荡思想。云上时光,吾谁与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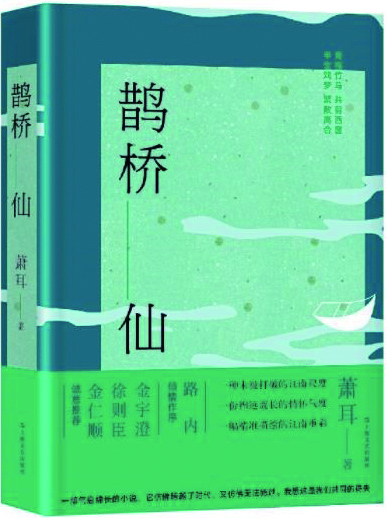
从古至今,江南都是文人墨客笔下魂牵梦萦的描摹对象,从“春风又绿江南岸”到“能不忆江南”,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到王旭峰的《望江南》……江南独有的吴侬软语和氤氲水汽仿佛也给变幻无穷的人、事、景镀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与灵气。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萧耳作“河边书”,“来记录独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属于那个水乡古镇的青春故事”,便是如今的这本《鹊桥仙》。本期云友读书会的四位读者,分别从人物形象、语言特点、时空变迁等角度来阐述自己心中的《鹊桥仙》。
——本期主持:刘雅
@李一默:忽而少年,忽而迟暮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与其说小说家萧耳赋予了《鹊桥仙》异常明显的时间观念,不如说“江南人”萧耳有一颗纯粹的少年心,《鹊桥仙》的底色是怀旧的,充满了忧郁而落寞的气质,更像是一场与时光对抗的旧梦。那些少男少女在一个叫江南“栖镇”的地方生活着、恋爱着、梦想着、希望着,同时一次又一次失去;出走归来,聚散离合,故土远方,忽而少年,忽而迟暮,真的是各自前程各自奔;桨声灯影,断桥残烟,霞蒸云蔚,烟雨迷蒙,流水落花,早已分不清哪里是真实哪里是虚幻。
靳天阳光,戴正憨笑,何易从略显严肃,陈易知有点骄矜。四个如此性格的少年在小说开头被定格在一张照片中,似乎也是萧耳有意为之。可是,少年们意气风发,才不会拘囿于照片,自然也不会服从所谓命运的安排。他们注定要踏上各自的征程,收获星辰和大海。然后,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身后不仅有造物主萧耳,更有真实庸常的日常生活和不可阻挡的残酷时光,即使作家在暗中为其标明万千号码,但生活终究会教给他们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靳天再见易知,他一边唱歌,一边含情脉脉注视她,两个人沉浸于陈慧娴的《飘雪》中,飞扬的青春早已不再,他们只能躲在回忆的世界中找寻一点安慰。当何易从故国一别千万里七载再归来,走上有点年久但依然可以使用的老木楼梯,看着日光倾斜,从木头楼板的几处裂缝里透进空荡荡的屋子,那时那刻,在异国他乡前程似锦的他仍免不了孤寂和落寞。憨厚正直的戴正一直是单身汉,独自前往五台山散心,面对同样出来游玩比他还小一轮的杜慧,他倒也潇洒,自嘲道:人生半途,无问西东,出来荡荡。
《鹊桥仙》塑造出的最重要的四男五女都是江南人物,寄托了作者对江南人物的理想。《鹊桥仙》初名《河边书》,这个名字与萧耳自身的生命体验高度契合,萧耳出生在京杭大运河边的塘栖古镇,运河是她青春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运河也见证了这些江南古镇几百年的繁荣。由此,萧耳想写一本书,来记录独属于她们这一代人的、属于那个水乡古镇的青春故事。《鹊桥仙》自然是一部描写江南风物人情的长篇小说,以细腻繁密的江南意象和绵长深厚的江南气息再现了一代人的青春往事。正如萧耳在后记中所说,“我希望有江南情结的人,能在此中依稀寻梦。”
@陈铭:长长斯远 粼粼水光——语言之于“文气”
河畔点点灯影闪烁在微微荡漾的水面上,栖镇一条普普通通的河因为一双眼睛的注视忽而浮光跃金起来,于是,滴滴涓流便在一位地道南方姑娘的笔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绵延流淌到新世纪。漫长的时间施予小镇变化,也施予小镇里青梅竹马小儿女们变化,然而纷纭世事流转到这里,仿佛被这里的温山软水汰洗,俗世的斑驳和沧桑倏尔不见,翻山越岭,远涉重洋,兜兜转转,生生死死,清灵秀丽还在,潋滟水波还在。
清灵秀丽是小说故事的调性,潋滟水波是小说故事的背景。作者萧耳从遥远的关关雎鸠与白露为霜中采撷到某种优美的诗性气质,满怀感情地注入到对这个江南小镇故事的讲述中,翻开书页,字里行间弥散出氤氲水汽与纤纤风致,这是这部小说的“文气”,也是最让我留恋徘徊,咀嚼不已的地方。
“少女思春,河边一梦。雨滴敲窗,敲瓦,密密匝匝,桨声灯影,旁逸斜出。水蒸云梦,恣肆漫漶,舟楫棹歌,渔栅幢幢”。开篇首段,高密度的四字句为小说打出一个极其精雅的亮相,也就此铺下整篇语言运用的基调。
小说语言极少出现长句,即便陈述事件,语言仍旧轻简。尤其在少年部分,人物对话在轻简之余,更添意气率直。“湘湘抬头看靳天,说,叫我一声姐姐。靳天不好意思,脸有点红了。湘湘说,是不是想我了?靳天脸涨得更红了,轻微地点点头。”颇有汪曾祺《受戒》掠影。同时,南方方言不时夹杂其中,如“小辰光”“小人”“荡发荡发”“天墨墨黑”“纤丝扳藤”,更直接有效地增添了江南气韵。
语言运用中不断间插诗文,或曰诗歌或曰戏文,文辞精美,被包含在作者所要书写的“江南底蕴”之中,平添斯文书香气。如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易从去省城上大学前,在收音机里听到昆曲唱腔“春深离故家,叹衰年倦休,奔走天涯”。“离家”搭建起小说人物与戏曲人物之间某种隐微的联系。同时,这“斯文”语言之中亦有对古代经典文学的回望与呼应,如易从撞到现实中的男女之事时,想到“司棋与潘又安也做了这样的事”;靳天与心爱的湘湘见面后,“眼前则是湘湘连衣裙外露着的一截白嫩的胳膊”;以及借女主人公易知之口直接点出:“说得轻一点,你(何易从)就是何宝玉。”皆在文中将作者对《红楼梦》的理解与致意点染进去。而诗的气韵、青春的少男少女,又在《鹊桥仙》与《红楼梦》之间搭建起某种隐微的联系。
借刘勰之语:体植必两,辞动有配。作者对语言的使用和经营对于讲述江南地域中的江南故事,对于描写江南儿女间的绰约情态,是相配且流丽的。而这“相配”与“流丽”无疑是小说“文气”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让这个从长长斯远讲起的故事一脉流下,没有漫长时间跨度带来的仆仆风尘,而呈现出江南语境中的粼粼水光。
@程远图:“江南性”与怀旧的诗学
《鹊桥仙》中“江南性”的生成,既与作家笔下的人物有关,也与对江南小镇栖镇的怀旧书写有关。
《鹊桥仙》围绕着在栖镇成长起来的易知、易从、靳天、戴正等人的少年和中年经历展开,讲述一代人的人生轨迹与对过去岁月的回望;与此同时,作为一部空间属性很强的小说,两个时代的栖镇本身也成为作者着力书写的对象。虽说小说中空间的诗性意蕴不能截然独立于人与故事之外,栖镇作为一个具有江南意蕴、承载着作家情感和记忆的所在,其本身也有了诗性的品质,成为了生成怀旧意味的载体。
作家对旧日栖镇的书写蕴含浓郁的怀旧气息。小说中少年时代的故事,读起来犹如沉入一场关于江南的旧梦中,作家赋予了栖镇一层怀旧的滤镜。而书写的时代越接近当下,灵韵渐渐变淡,少年已成中年,怀旧的风格逐渐被现世的中年生活所冲淡。伴随着时代变迁,栖镇也不复当年,过去的时光已然消失,不可重现。在某种意义上,这反向印证的记忆往往会被构造为神话。小说将两个时代的栖镇空间交叠并置,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时间感,也凸显了时代的变迁给小镇带来的变化。
对小镇空间的追忆成为怀旧的一种方式,也成为回溯旧时光的线索。这片江南的古镇空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在时代洪流与岁月流逝之中的人们,对于这种无能挽留只能以记忆作为纪念。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其实为作家提供了怀旧的前提:在曾经追求着到世界去的那些少年们历经半生的奔忙生活和聚散离合后,栖镇给了他们一个回望的方向。小说中的人们在历经社会与人生进程的变迁后,对过去的不断回溯,意味着在精神层面上对这些变化的某种隐性抵抗。易知、易从,那些少年的朋友们,那些从栖镇走向世界,从世界归来栖镇的人们,始终还在追忆着旧事,即便有的归来只是短暂的停留。这种融合着个人的记忆和时代印痕的回溯,也成为了一曲对旧日江南的低吟挽歌。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和空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作家萧耳在小说中构造了一种人和空间的关系,在她的写作中,栖镇空间不再简单是人物和故事的背景和舞台,其本身成为一种富有灵性的前景。那些小镇里的寻常生活,那些吴侬软语的声音,那些极具地域特色的风俗,都成为了怀旧的要素。与其说作家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是在编织着关于人、空间和时间的共同体,故事性、戏剧性在其间被稀释淡化。作家立足于当下的书写,使得对过往的回望具有了诗性的意味。用写作把过去小镇里的辰光凝固下来,少年们已然逝去的“荡发荡发”的时光,那些枕河而眠的时光便足以使人长久回味了。
@陈梦霏:荡发荡发,应是绿肥红瘦
栖镇、运河、码头、行船、小桥流水、地道两三代的江南女子、青梅竹马的流年、嗲嗲糯糯的声音伴随着吴越腔调,徐徐拉开江南重彩卷轴的一隅,诗意水乡的唯美意境为栖镇儿女们灿烂忧伤的故事提供了舞台。
故事发轫于栖镇,一切都要从一张老照片讲起。十二岁那年,四个“小人”陈易知、何易从、靳天、戴正定格在同一张合影上,由此展开了这群发小少年至中年的人生故事。他们的“小辰光”总是与欢愉搭边,小打小闹也都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是明亮。青春年少的少年们永远在“荡发荡发”,会在夜晚数着过往的船只,卧听轮船发出的鸣笛;会骑着自行车飞驰谈天说地,心中留痕或雁去无声;更多的是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里互生情愫、各怀心事。易知纯粹不谙世事,心心念念隔壁少年郎,却心口不一,在她的“小辰光”里始终贯穿着一场少女的小心思。易从这个少年郎可谓倾注了作者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说他羸弱又不合群,说他博学又多才,说他太像贾宝玉,怨他不曾坚定地选择自己,在摇摆中迷茫。而同为好友的靳天倒是与易从有着不一样的气质,他是书中最有江南公子哥儿风范的少年,清新俊逸、器宇不凡,尤其是其骨子里透露出的敢爱敢恨的性情,真是赚足了眼光。
“荡发荡发”,高考后大家各奔东西,转眼半生已过,在沈美枝的婚礼、靳天的婚礼、家乡亲戚的婚礼、钟晓伟的婚礼、刘晓光的葬礼以及春节等节日下,这群人也由青年过渡到中年。在中年时光中,沈美枝情场失足,孤寡一人;靳天爱而不得后,四处留情;刘晓光负债累累,一命呜呼;杜秋依妻凭夫贵,扶摇直上;陆韶走入仕途,锒铛入狱;易从走出国门,顾影自怜;易知心向远方,却被亲情羁绊……纵观人各不同的人生道路,不难发现他们都一样根系故乡,难逃情爱的枷锁。唯独最“闲适”的戴正,成为了自己最喜欢的“柳敬亭”,一把惊堂木,讲述人间百态。三个男主人公中,靳天率性洒脱,戴正悠然自乐,而被称为“贾宝玉”的何易从身上始终笼罩着江南烟雨的水雾气,不免心性黏腻,性格上又不够爽利。性格中的“优柔寡断”,让何易从一生郁结于心、困顿于情,周旋于多位女性之间,又因这份“柔情”不经意间让他身边的四个女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读罢《鹊桥仙》,仿佛是乘坐了一次时光机,在体味他人人生的同时,也禁不住反刍自己的人生经历,正如路内所说:“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得失。每个中年人都能标榜过往年代的好,却往往无力诉说曾经的自己。”通过这本书唤起些许怀旧之心,也是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