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不妨先“阅读”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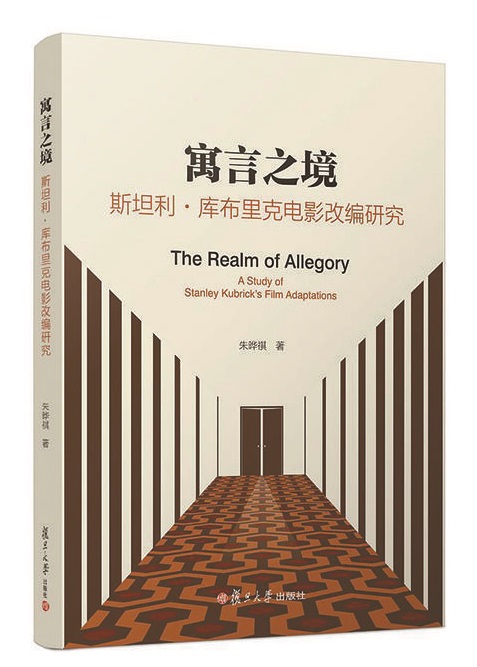
《寓言之境: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改编研究》 朱晔祺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影从未像今天这样焦虑于自身的原创性。从端庄素净的文字到闪烁流盼的影像,这中间不仅是导演媒介转译手法的魔幻再现,也是导演竭尽全力捍卫电影作者身份的一种博弈。最近看到的这三本著作,《寓言之境: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改编研究》《经典之后的银幕奇景:好莱坞中生代导演研究》以及《法国“作家电影”流派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导演研究的一些新方法和新动态,为读者汇聚起了一种多元共生的电影阅读经验。
库布里克:一个寓言型读者
作为“导演中的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一直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他的成就不仅引来詹姆斯·卡梅隆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交口称誉,甚至连伍迪·艾伦这样的导演也不得不坦陈自己对他的敬意。确实,库布里克作品题材各异,形态迥然,议题深邃。可以说,他的作品兼具怪诞的娱乐性与迷宫般的思辨渴求,并因此成就了一种晦涩迷人的整体风格。遗憾的是,现阶段关于他的研究大多止步于传统的导演传记层面,甚而是以讹传讹的八卦趣味,而未能精准回答这种风格背后的精神成因和作者技巧。这正是《寓言之境: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改编研究》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区别于以往导演研究的普遍思路和范式,作者朱晔祺别出机杼,选择了从库布里克作为文学-电影改编者的角色介入,跳出了“作者电影”的习惯性窠臼,转而从文学文本追踪溯源,试图重新探讨有关库布里克创造性的深层秘密。
在我看来,本书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首先,它重新定义了“作者电影”的范畴。众所周知,自弗朗索瓦·特吕福1954年在《电影手册》上公布自己有关作者策略的思考之后,“作者电影”常常被用来强调电影导演在创作上的独立性以及作品的独属气质。那么当面对库布里克这样一位视文学改编为创作重要契机的导演时,作者理论该如何生效?我想,这正是朱晔祺决意从文学改编这个“非原创性”的源头尝试探讨库布里克作品创造性的出发点。那就是,将库布里克视为一个寓言型读者,并以此建构他的作者身份。这就过渡到了文学-改编电影的标准判断问题,也即这本著作的第二个亮点。一直以来,“忠诚观”都支配着文学-改编电影的创作标准。罗伯特·斯塔姆甚至认为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的话,“电影改编就是俄狄浦斯,象征性地杀死了作为‘父亲’的源文本”。而朱晔祺巧妙避开了这一陷阱,将目光转移到作为创作策略的改编行为本身,专注于探讨导演在转换“非语言体验”过程中如何激发电影的媒介优势,自然而然地将媒介转译问题引入了导演研究,从一个更大的媒介场域中印证了库布里克获得“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这一过程。
《寓言之境》的第三个亮点,或许也是最具抱负的一点就是,作者试图通过将库布里克定义为一个寓言型读者,继而在德勒兹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的哲学理路中为导演建构起一种寓言-影像,即“肯定影像自身的矛盾性和差异性,让原作、陈套、刻板印象和舆论常识都再次回到零度”。当然,“回到零度不是为了摧毁和消解,而是为了在非零和的互动中实现一种朝向未来、充满活力的创造”。必须坦承,就库布里克晦涩迷人的整体风格和原著文本之间的“断裂”而言,我确实感知到了朱晔祺所说的寓言-影像,那是导演对原作文本和影像不确定性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库布里克改编作品总是持有一种混沌激撞的视觉印象,但对故事的感知却总是恍如梦游一般绵软无力的原因。不过,就书中寓言-影像的逻辑推演而言,我以为所涉理论之间仍有很多缝隙尚待填充。这是一本能够对阅读发起挑战的著作,当然会伴随着不断解惑的快感。也可以说,就它的研究对象而言,这本书的行文风格与库布里克作品的整体风格颇为般配:晦涩迷人,欲罢不能。
诺兰:好莱坞最后的电影作者
《经典之后的银幕奇景:好莱坞中生代导演研究》选择了克里斯托弗·诺兰、戈尔·维宾斯基以及达伦·阿罗诺夫斯基三位导演作为管窥好莱坞中生代导演群体创作现状的一个切口。正如书名暗示的那样,三位导演的创作实践构成了相对保守的好莱坞主流叙事之外的一道银幕奇景,令读者从不同题材、风格和价值取向中领略到了电影创作的多元形态和创作潜能。确实,通过作者对几位导演创作路径的详尽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欧美电影文化之间的传承与互动。诺兰作品中困顿纠结的个人英雄主题、维宾斯基反英雄的角色塑造,以及阿罗诺夫斯基对灰色人性的反复摹写,都能在库布里克的作品中找到回声。最重要的是,沿着书中提供的线索,好莱坞中生代导演与昔日“新好莱坞”导演作品的精神地图逐渐显影。那种由“消费社会所孕育,并从消费社会提倡和反对的价值中诞生的现代性”,通过不同的角色发出了各自的呼声。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持续不断地发酵着“作者电影”的独特魅力,并力图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为“作者电影”赋予新的意蕴,那就是“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自觉趋同”。
正如罗伯特·考克尔所言:“电影不仅是娱乐物,而且是工业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三位中生代导演来说,如何将严肃的社会议题和人类深邃神秘的精神世界镶嵌进基于类型的好莱坞主流盈利框架,同时还要在形式风格上做到清晰可辨,首先就是要尊重和恪守被验证过无数次的好莱坞电影工业经验,然后才可以触及风格化的“作者”符号。以诺兰来看,围绕着造梦(《蝙蝠侠》系列)、寻梦(《记忆碎片》)与盗梦(《盗梦空间》)这一不断重复的抽象主题,使得他在技巧上形成了以碎片化剪辑、非线性叙事以及低密度暗黑冷峻的影像(对梦境的营造)为特征的整体风格。而他一直坚持实景拍摄,坚持使用传统胶片,拒绝使用数字中间片来调色的“固执”习惯,也为作品整体上赋予了一种“不妥协”的作者气质。但它经由碎片化剪辑和高度视觉化的梦境再现所形成的那种大开大合的节奏,又极其精准地击中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里浸淫已久的观众口味,使得“作者电影”这个概念从法国新浪潮时期那种对形式技巧的僭越冲动,演变为一种融合了几许“作家电影”气质的混合物(诺兰承认《盗梦空间》里有好几处情节“碰巧”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相似)。无怪乎斯皮尔伯格直言诺兰“是好莱坞最后的电影作者”。我想,通过这几位中生代导演的实践,好莱坞主流电影已经确认了它的自我更新意识和推陈出新的能力。
“作家电影”:将文学表达不了的用影像再现
盛柏则在《法国“作家电影”流派研究》中仔细辨析了“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的区别。对于一个深受20世纪中叶“存在主义”和柏格森“直觉主义”影响而导致的富于心理意识特征的电影流派来说,“作家电影”独有的哲思意蕴与内敛气质和新浪潮时期“作者电影”在形式上的激扬狂放大相径庭。它对戏剧化叙事模式的摒弃、对情节套路的淡化、对角色线索的交错处理、对旁白的偏爱、对时空场景的跳跃式剪切等处理,使得观影过程犹如在一个私密的内心世界里梦游,成功地在电影世界里复制了类似文学阅读的沉浸经验,一度为“作家电影”赢得了声誉,也将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推到了话题中心,历史上第一次为电影媒介赋予了文化深度——电影从此不再是一个肤浅的娱乐产品。譬如在面对《广岛之恋》这样的作品时,观众即便全神贯注参与进去也仍然不得要领。在那一刻,电影仿佛由热媒介又变身为冷媒介了。看起来,“新小说”派的作家们虽然拿的是导筒,却仍然是按照文字去思维。不知道曾经提倡将摄影机视为一支自来水笔的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对此会作何想。
事实上,无论是“作家电影”还是“作者电影”,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强调电影作品的原创性,表面的差异背后或许是对媒介表达可能性的某种焦虑。正如盛柏观察到的那样:“‘作家电影’流派的导演们并不是为了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将文学表达不了的东西用影像再现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个判断放在上世纪中期视觉文化开始呈井喷之势的语境中(正好是“作家电影”群体的创作高峰),或许更容易理解“作家电影”隐含在意识流影像中的不安与纠结。正像他们对旁白的过分倚重所导致的“影像与声音的堆砌”最终对电影本体美学的伤害那样,“作家电影”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可能就是重新思考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倘若阿兰·罗伯-格里耶所言属实,即小说和电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形态”,因而需要为他们的电影创作出专属的剧本的话,那么当我们回望库布里克寓言式的改编策略,或许就更容易理解他作品中的“作者”属性:创造性的媒介转译与激进形式的完美结合。
概括而言,以比较阅读的经验来看,这三本著作围绕电影的作者属性和电影与文字的媒介属性,角度各异,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了一种多元共生的电影经验,大致勾勒出了当下导演研究的一种新视界。期待中国导演研究也能涌现更多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上独具一格的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