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4年第3期|娜仁高娃:裙子
冰凉、清爽、干硬、洁净的空气,嗬——北方初冬霜降后的空气,来自雪山之巅的寒冷的、彻骨的、令人浑身战栗的空气,让裹挟着“生命激流”的空气滑过肿胀发麻的舌头,使舌头瞬间苏醒过来,使酸疼的喉咙打个激灵,使疲倦的胃恢复体力,猛烈蠕动,在胸腔里掀起一股空前的震荡,驱逐占领她整夜的恶心、晕眩、憋闷。然而,无论她如何张大嘴,倾尽所有力量,贪婪地,吞云吐雾似的大口大口地吸气,胸腔里依旧是油腻腻的,脑壳里隐隐发痛。她所渴求的“来自雪山之巅”的空气只不过是她那毫无行动能力的遐想。空气早已变质,变得油腻且浑浊,甚至有了重量,化作一层保鲜膜似的东西,紧紧地裹着她,堵塞了每一个毛孔,血液正慢慢地凝固,骨头也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五脏六腑变成暗紫色,近乎糜烂,一股污浊的液体从她口腔里溢出。
噢——她干呕着睁开眼。她不确定刚才的一切是一场梦,还是她醒来的瞬间所感觉到的。她仰躺着,虚弱地睁开眼,瞟一眼青灰色的吊灯,又匆匆闭上眼。可怕的眩晕使她感觉吊灯会突然摇晃着坠落下来,重重地砸在她脸上。然而,极度的口渴又催促她立刻用一杯冰凉的水,嗬,不,最好是冰块,驱逐她胸腔里的焦灼感。她揉了揉额头,小心翼翼地睁眼,向床头柜看了看,可那里没有水杯。口腔里涩涩的,唾液黏稠而辛辣,嗬!她猛地坐起,蹙眉,低头,胡乱地抓头皮。
再也不了,一滴都不沾,我发誓,该死的酒,就算天王老子盛邀,都不行!
她愤愤地发牢骚,吐热气,可难忍的眩晕感一阵赛一阵。她只好再次躺下,恼怒地蹬腿踢去棉毯。而就在那瞬间,一股陌生的丝滑感传遍她整个躯体。她立刻觉察出自己赤身裸体。
呃!她不由得猛地坐起,向周边看去。内衣内裤都在,被她揉成一团放在床头柜上, V 领淡粉色贴身毛衣扔在地板上,连体长筒袜被丢在床正对面的衣橱下,黑黑的、长长的袜身像是褪掉的蛇皮。黑色超短裙呢?掀去床被、枕头枕巾,没有啊。伸胳膊,拉出床头柜抽屉,也没有。探过半截身子,面颊几乎贴着地板看向衣橱一侧的椅子下,那里空空的。拽过窗帘,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又惹来一阵眩晕,可窗台上啥也没有。最后,她还掀去床脚的地毯。
“你醒了啊,头很痛吧?来,喝杯蜂蜜水吧。”
丈夫进来,端着水杯,一步一步地蹭过来,然后将满满的一杯水举到她胸前。蜂蜜还没有完全融化掉,像团鼻涕似的漂浮在水里。呃,油腻的烤串,丈夫因抽烟熏黄的指关节,还有某种野兽般苍老而呆痴的眼珠——她痛恨这种突然占满脑子的联想,她捂住嘴,强忍着呕吐。
“来,喝一口,喝下去就会好一点儿。”她吃力地摇摇头,闭起眼,拽过棉毯遮在身上。
“看你,眼睛都肿了。” “开开窗户吧。” “咦,好烫啊,不会是发烧了吧。” 黏糊糊的,也不知为何,她感觉丈夫的掌心像只野蛤蟆用无比肥胖的腹部贴着她的额头。
“快啊,让风吹进来。”
她说着,一手抓紧被褥,一手推开丈夫的手。她的语调低沉,但丝毫没有因为身体极度不舒服而导致的虚弱,反而是夹杂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命令味道。她用力揉胸脯,像支船桨用力搅动着水好让船离岸。
“哎,看把你难受的,再躺一会儿吧。”现在,她仰面躺着。窗帘缓缓地随风摇摆,然而,她所期望的凉爽的风却迟迟没能洪水般扑进来。它们只是慵懒地,迟缓地,甚至有些暧昧地掀开窗帘。它们还带来嘈杂的车流声,而这嘈杂声又与厨房那边传来的豆浆机近乎疲倦的旋转声,冰箱冷藏低沉的轰鸣,防盗门钥匙孔传来冗长的呜咽,以及马桶冲水时类似某种巨兽吞咽猎物时的声响,相互交融,浑然一体,造出天然的、粗陋的“交响曲”,这使她脑壳里的嗡嗡响越发清晰。她痛苦地用棉毯蒙住头,却又烦躁地掀去。
哦,裙子!
直到午后,她已经把屋内能翻腾的角落都翻了个遍。她披散着头发,穿着一身夏天才会穿的裙式睡衣,一言不发、执着而带着一种令人诧异的憎恨寻找那条裙子。是的,她带着一种憎恨的情绪,把衣柜里的衣服全部丢到地板上。不过这一切都是她丈夫出门后发生的事。后来,她疲倦地斜躺在沙发上,一遍遍地回想前一夜的事。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怎么按捺着焦躁的心绪,平静地勾勒前一夜,可脑子里始终空空荡荡的,不但想不起整个过程,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想不起,仿佛仅仅过去十多个小时,前一夜的一切变得无比遥远,像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模糊记忆。
翻开手机看,通话记录里显示晚上九点半,她给丈夫打过电话,通话时间是五十六秒。她想,她大概是跟丈夫说她们要去唱歌了。而且打电话时她一定非常激动,冲着电话喊:就我们四个,米子、曲子和曲子的男朋友,我们要去唱歌了。她确定,当时的她特别兴奋,因为已有一年多没和闺蜜们聚了。十一点一刻,一个未接电话,是丈夫打来的。她没有任何印象。十一点半,也是丈夫的未接电话。凌晨一刻,三个未接电话,都是米子的。猜出是问她有没有到家,很显然,这时候她是一个人。她舒口气,丢开手机,慵懒地半躺在沙发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吊顶。相比早晨,浑身虽然不舒服,但呕吐感和折磨人的眩晕感消失了。
谢天谢地,她喃喃自语——她真的没有给那个远在千里之外、与她青梅竹马的男人打电话。谢天谢地,在她丧失所有理智后,竟然没有被潜意识中的欲念——是的,这是一种可怕的、无法磨灭的、无法抗拒与逃避的、在她心灵深处扎根多年的欲念——所挟持着,她没有向欲念投降,去寻找欲念本身呼应的对象。
她打败了它,终于打败了它,让它变成一座死火山。她坐在那里,凄然一笑,仿佛是一个刚参加完亲人葬礼躲在某个角落黯然伤神的人。
二十五年前,她十九岁,在小镇中学读高中。一个周末的黄昏,两人在湖边隐蔽的角落接了吻。那是他们的初吻,也是她至今最短暂的一次接吻,感觉嘴唇刚刚触到什么,类似一股滚烫的气流后便结束了。然而,就在那奇妙的“滚烫”过去后,她感觉整个人在那幽暗的角落里变成一轮透明的、圆鼓鼓的月亮,轻轻戳一下,便会溢出浓稠的液体。高中毕业后,他去了省城的大学,她则在距家乡不远的小城读专科。临走他送她一条花色围巾。那次他们也相拥亲吻了。专科毕业后,她在小镇当了一名邮递员。起初,她以为他大学毕业后会回到小镇,可他却选择了到成都去,他考上了那里的一个用他的话来讲“富有大好前景的”企业。他要她跟他走,但她没有。等到春节他回来看她,她却躲着没见。她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一个大风天寄过去的。信中她说,她得留下来照顾母亲和弟弟,她弟弟是个患有麻痹症的少年。那次她躲在被窝里号啕痛哭。而那天的风却在窗外吼,很是狂欢的样子。哭累了,她走到外面,看见一大群乌鸦铺天盖地,像个巨型逗号似的飞过屋顶,一会儿又像是被磁铁吸着似的向着同一个方向飞去。再后来,也就是十年前,她和他在小镇某个宾馆过了一夜。那时她的女儿已经七岁了。自那之后,她拉黑了他的电话号码。可是,在一次元旦联欢晚宴上她喝了几杯酒后,竟然拨出了他的电话。而在拨通的瞬间,她又挂掉了。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还清楚地记着他的电话号码。也是那次之后,她不敢再喝酒。
酒液是来自地狱的使者,用它无影的手攥着她的魂灵,露出驯服者的得意面孔。那么,她的反击呢,那便是以一种无比虔诚的信念来克制自己。归根结底,她不喜欢背叛,或者说她不忍心背叛她那无论任何时候都不会冲她发脾气、露出阴沉神色的丈夫。
他好像在遇到她之前已经发完了他今生所有的坏脾气,或者说,他在遇到她之前已经是一个深谙“夫妻相处之道”的人。他总是说:哦,没什么大不了的,都会过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的确是,只不过是丢了一条裙子,一条价格中等、款式也普通的裙子。就算丢到大街上,也没有人会当个稀罕物捡起来,反而会任由风卷飞,随意地吹进某条窄长的、很少见到阳光的胡同内。可是,哪有风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然而,最最关键的是,此时此刻裙子到底在哪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她步出家门,走到楼道,从五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慢慢走下去,翻看了邻居家的鞋柜、水暖管道箱、一楼过道口的垃圾桶。她脚步放轻,没有任何响动,简直是化作了一个幽灵。她还到小区小花园走了一圈,仔细地查看了花园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她不敢去门房查看监控,那得多难为情。门房的那个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人,可不是好惹的家伙,他有双光芒四射的“精准的捕捉器”般的眼睛,每次见有人进出,他都会站在门房玻璃窗后,向对方投去警惕而胸有成竹的眼神。
临近傍晚,她来到街上。她决定沿街找一遍。她用口罩、围巾、手套以及墨镜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那样子看上去像是一个坐月子的产妇因某种刺激而变得神经质。她含胸弓背,步履匆匆,时不时还会半蹲着,扒开路旁修剪过的绿化带,仔细查看。那些造型笨拙散发着臭味的垃圾桶她也一个也没有漏掉。有几次,她站在路旁的树下,仰起下巴,歪着脑袋望向树冠。树上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尽,稀稀疏疏的树叶,不像夏季那样近乎雍容地叶尖向下,而是怪异地抽缩身子,干瘪地横于半空。有一回,她从花池低矮的铁栅栏旁用食指勾起一块黑色的布片,然后便近乎呆痴地兀立在那里,好一会儿都没动弹一下。
等到路灯都亮了,她才回了家。 “好点儿了吗?”
“嗯。”
“风里走走就是挺好,来,把这碗菜汤喝了,出出汗。”
“嗯。”
“要不我给你拔拔罐吧。”她丈夫说。
“不用,我好多了。”
临睡前,她给米子和曲子发语音问自己前一夜怎么回来的,两人都说是她非要自己一个人打车走,她俩也没办法,只好恳求出租车司机一定要安全送到小区,还拍了出租车的车牌。她没问裙子的事,也没让她俩给她发照片。听口气,她俩好像根本没觉察出她这边有什么不对劲。这么一推测,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便是在出租车上什么都没发生,上出租车的时候她一定穿着裙子。
然后呢?
然后啊,米色长款风衣衣摆上布着好多块污渍,那是她的呕吐物,好恶心,呃,不管它了,它已经被她清洗挂在阳台上,松松垮垮的,像个无首怪物。高跟鞋也在,小挎包也在,包里的钥匙、口红、纸巾、购物卡、口香糖、卡包、揪眉镊子,都在。除了裙子,什么都在。她舒口气,翻转着身子,侧躺,眼巴巴地盯着窗户。没有开灯,也没有拉帘。客厅那边传来隐约的嘈杂声,那是丈夫在看篮球比赛。一切都很正常,不是吗?什么都没发生。
一切完好如初,风平浪也静。
大约过了三个礼拜,天气越来越像冬季,街上行人中看不见穿半袖的小伙子,看不见裸着踝骨的女孩子,小孩子脸上出现了受冻后的红润。她已放弃了寻找裙子的念头。虽然每次下班回家途中,条件反射似的带着期待的眼神瞥一眼小区某个角落,或者一个人在家时翻一翻沙发垫什么的,但是渐渐地还是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偶尔还觉得自己过于神经质。又过了几日,有天早晨,她走到外面,发现小镇被白茫茫的雪和雾笼罩着,新鲜而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激得她不由轻叹一声:唷,下雪了。她决定徒步去单位。过了两个十字路口,在经过那家酒吧时,她抬头看了看酒吧。起初她只是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继续走,突然,她猛地驻足,像是听到某种奇怪的声音从酒吧那边传入她耳朵似的立在那里。
一个圆圆的、黑黑的、吊在半空中的“眼珠”,一个安在酒吧牌子一侧的、无死角的探头——她直直地盯着它,它也直直地、冷冷地盯着她。它这纯属毫无掩饰的对峙,就连密集的雪花都没能遮覆它。
一张干瘪的嘴,嘴角抽动着,露出无声的笑。一张叼着烟的嘴,轻松地撇了撇,露出熏黑的牙齿,笑得很诡异。一张涂了口红的嘴,翕然一开,发出咯咯的笑。一张嚼着泡泡糖的嘴,陡地停住嚼动,倏尔扑哧一笑——他们躲在屏幕后面,看着屏幕上的黑裙子,不,是她,看着她,发出他们各自的笑声。
她疾步走着,双臂紧紧搂着前胸,脑子里乱乱的,她不知道那些“笑着的嘴”怎么突然涌进她的脑子里。一切都横空插进她的脑子里。在那些重叠而转瞬即逝的画面中看到她还看到粉色花裙——那是一年前在网络里闹得沸沸扬扬的“步行街粉色花裙”事件。
一切又回来了,一定有人看见她究竟在哪里脱去了黑裙。
是的,一个知晓她所有秘密的人一定存在。而且,在不久后的某一天,这个人会把图片或者视频发到网络上,或者给她寄过来一个装着她所有秘密的包裹。甚至,某一天,这个人突然从街角,或者超市门口,用一根指头勾着她的裙子,说:“喂,这是你的吧。”
这种联想使她感到窒息,心怦怦跳个不停。雪丝落在她脸上,发出轻微的“刺刺”声,仿佛是因撞击而导致的骨骼断裂。等到下班,她没有立刻离开单位,而是磨蹭到天黑,然后换了路线往回走。天气不是特别糟糕,也没有风,但雪还没有完全融化,马路上尽是斑驳的足印。有井盖的地方呈黑黑的、湿漉漉的一个圆圈。她不看路旁的商店、宾馆或者饭店,她知道每一扇门门首都吊着一个“黑眼珠”。她一路低头,跨过一个又一个井盖,她惊奇地发现路旁的井盖原来如此多。有的井盖上小小的眼里还冒着热气。污浊的热气,令人眩晕的、肮脏的气浪,她感觉身上油腻腻的,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醉酒的早晨。
接下来的几天,她深居简出,除了单位哪儿都不去,等到周末,她丈夫要她一起去参加亲戚的婚礼,她硬是找了借口没有去。她变得神色郁悒,面色苍白,食欲大减,一有空便躺在床上,并一根一根地拔去种植的假睫毛。
“最近怎么了,身体是不是出了啥毛病,要不咱去医院查一查?”
“不,我没事。”
“ 是不是想闺女了, 要不咱去看看闺女?”
“不,我只是有点儿累。”
“萨玛干(蒙古语,指老伴儿),我把摩托车卖掉了,明年我想买辆动力大的越野车,你知道的,人们越来越喜欢刺激的玩法。”
丈夫滔滔不绝地说着,仿佛两人因分开好长一段时间而积攒了太多想要说的话。她安静地听着,头枕在沙发垫上,一只手放在丈夫的腿上。她的双目盯着丈夫长年被沙漠风吹得干燥而呈茶色的面颊,以及些许下垂的腮帮。她没见过他青少年时期的样子,他们相遇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但他有一对肌肉发达的手臂,浓黑的眉毛,还有一双深邃且透露着无比坚强光芒的眼睛。不过,起初这些都没怎么吸引她,如果他没有一个好脾气,脸上总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温和的笑,给人一种青春永葆的感觉,她是不会嫁给他的。一个能时刻主宰自己情绪的人,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在她眼里,丈夫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虽然他只是个在沙漠腹地景区给人当向导的驼夫。
元旦前几日,她大病了一场,白天昏睡,夜里出虚汗,需要有人不断在身边陪护着。等到腊月中旬,她才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屋里走动。
“不会的,儿子,我可是它的主人,如果它敢挑衅,它知道我的鞭子会狠狠地击在它额头上的。”
“可我还是不敢靠近驼王,即便您在跟前,我还是很怕,它把牙咬得嘎嘎响,怪瘆人的。”
她站在窗前, 望着小镇南郊很远的位置,那里好几根细长的烟囱正吐着喇叭状的白烟。更远便是铅色的天空,以及冬季裸露的野地。在她身后,靠近客厅拐角处的家庭式酒柜前,她丈夫和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面对面坐着,正在谈论着如何调教驼王,也就是发情后变得“醉醺醺”的公驼。小伙子是他与前妻所生的,这几日从省城回来,准备待到春节结束。他正在准备考取土木工程师。相比父亲,小伙子有张女孩儿似的漂亮脸蛋,说话声音也是柔和而缓慢的。
“你可不能让驼王发现你很怕它,驼王很聪明的,它能听到你的心跳声,也能从你的眼神里看到胆怯。”
“爸,真的会那么神奇吗?”
“当然,那可是我一辈子的经验。” 她回过头,看向丈夫。他坐在高脚木凳上,双腿却像是坐在炕沿上似的耷拉着,左手胳膊肘抵住吧台,嘴里嚼着什么,正在听儿子的话。他的背有点儿驼了,眼角的皱纹也依稀可见,不过鼻梁还是山峰一样凸出。她觉得肖像摄影师会特别喜欢如此饱经风霜而又散发着某种原始美的侧脸。
“来,儿子,干杯。”
听他这么讲,小伙子举起杯,抿嘴一笑,同时扭头看着她,说:“妈,要不您也来一杯吧。”
“来嘛,度数很低的。”她摇摇头。
“妈,我从视频里看到少喝点儿红酒对人体是有益的。”
“呃,什么视频?”
“就是网络视频啊,说的是红酒能软化血管。”
“好喝,不过太甜了,我是喝不惯,这种甜酒就是给女人准备的。来吧,你也来一杯吧。”
“不,我说过,我讨厌喝酒。”
小伙子举着酒杯有些惊讶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父亲,当父亲的也是满目疑惑地看着妻子。显然二人都听出她嗓音里的颤抖,以及极力掩藏的哭腔。
“妈,您生气了?”
“哦,你妈还是不要喝了,她身体还没完全好起来呢。”
“我很好,我只是讨厌闻到酒味。” 说完,她双手拢着肩膀,低着头,近乎逃也似的进了卧室。
腊月二十一,她起了个大早。先是打开窗户看了看天际,判断出将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于是用床单兜着被褥下楼到小区栅栏上晾晒被褥。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在她年少时她的母亲便是如此做的。当时他们一家还在人烟稀少的沙窝地。每到腊月二十一这天,她母亲把家里的毛毡、炕毯、被褥,以及所有人的冬服拿到外面晾晒。那是何等的情景啊,墙头、柴垛、牛车、晾衣绳,就连牛圈栅栏上都披上五颜六色的衣物。她母亲还会带着一种欣慰的口吻说:扫尘,扫尘,扫去旧尘。等到晚上,她父亲开始拆旧灯,那是用四块玻璃和红色纸包边的煤油灯,每年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初七,这盏灯都会被吊在檐下。她母亲坐在炉前,用一截短棍搅拌铝盆里的面糊糊,那是用来粘灯的。没人说话,面糊糊“吱吱”地冒泡,母亲打个呵欠,父亲向妻子瞥一眼,又继续低头捯饬手中的活儿。她和弟弟躺在炕上,炕毯散发出淡淡的太阳的味道。
浓烈的太阳的味道,火热生活的味道。这句话从她心底涌出,像只从旋涡中扑腾飞跃着的鱼儿,从她四十年的生活中腾空一跃——多么完美的一跃,简直就是熬过北方干燥、清冷的夜晚后绽开的马兰,看啊,一簇簇紫色火焰,在春末寥落的大地上恣意地燃烧。美丽的季节依然,不是吗?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些令她惶恐、窒息、心悸、束手无策的日子结束了,那无数个沉重、凝滞、阒寂的失眠之夜,只不过是一场折磨人的梦。
她双膝跪地,用一条粉色毛巾擦拭着地板。她的丈夫则用改锥在拧酒柜脱落的螺丝。多么熟悉的景象,她俨然是当年那个在炉火边打呵欠的女人,他则是小心翼翼拆开油灯灯罩的男人。世世代代,生活并没有改头换面。什么午夜的狂欢,酒液的辛辣,恼人的眩晕,什么“黑眼珠”,统统都见鬼去吧。
她撩起汗津津的发梢,开始擦拭卧室的窗户。一会儿,她走到酒柜前搬高脚凳,她丈夫说,我来吧,她说,不用,我抱得动。她把高脚凳放在衣柜前,一手拿着湿毛巾,一手扶住衣柜。她知道衣柜上布着一层灰尘,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会认真地擦拭那个家里除了她别人永远都不会留意的死角。
呃,一团黑乎乎的什么,像只死去多日的黑猫蜷缩在那里。她用手指头轻轻地捏起,举高,仰起脸看着——尘粒雾气似的浮荡。
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喜极而泣,而是静静地看着。
“什么呀?”
“我的裙子。”
丈夫突然扑哧笑起来。 “你知道?”
他还在笑。她回头,俯视着丈夫。 “你不会是刚刚才发现吧?”
她点点头。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你早就知道裙子在这上面?”
“是啊。”
“为什么不跟我讲?”
“什么?”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的裙子在这上面?”
除了扭头看丈夫,她没有做别的动作,一条胳膊依旧停在半空里。
“我以为你知道呢,是你自己一脚踢上去的啊,你醉酒回来后一句话不说,进了卧室,坐在这里(他指了指床沿),褪下裙子,勾在脚尖上,然后就踢上去了。”
她放下胳膊,慢慢地蹲身,准备下来,可身子变得僵硬而迟钝,她不得不倚着衣柜站稳。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她不说话。
“来,把手给我,是不是头晕?”
“对不起!”她的泪下来了。
她丈夫愣了片刻,往前一步,手扶着她的腿,说:“来,萨玛干,把手给我。”
她抬起双臂,满眼泪地看着丈夫。 “嗨,你听说过吧,在沙漠腹地,外出的男人们回到家时会唱歌,会从十里地之外开始把歌声传给家人。他们绝不会趁夜偷偷摸摸地回来,蹲在窗下听。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是不是?你知道的。”
她摇头。 “我的意思是,生活没那么糟糕,我们
活一回,就得把好多温暖的、纯洁的瞬间记住,忘掉其他的。我们活着,就像现在,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她听了,可仍旧固执地摇头。
他看着她笑一笑,举高一只手,示意她把裙子丢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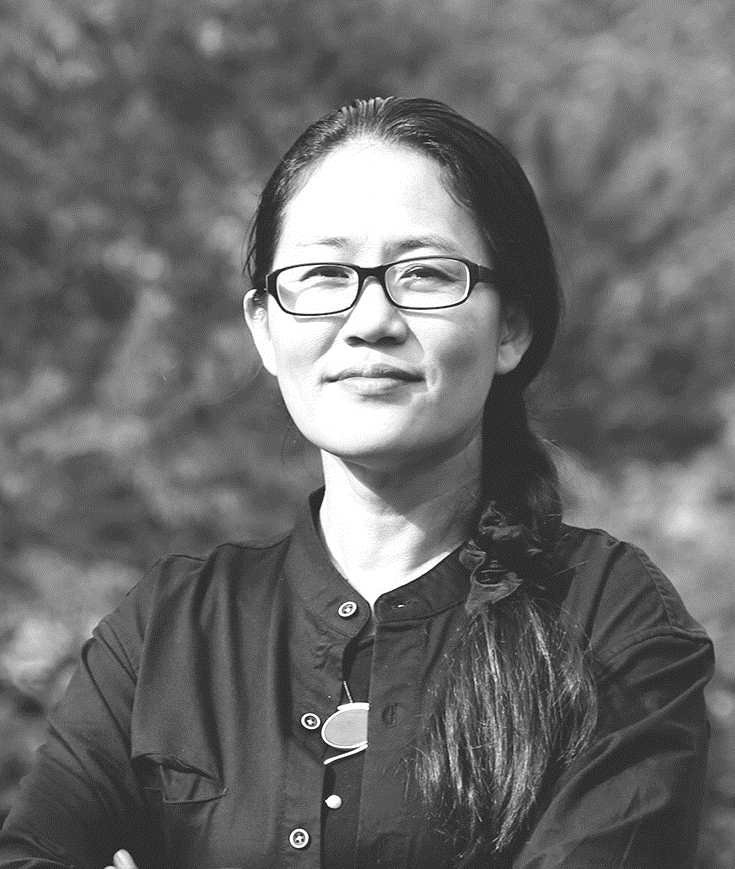
娜仁高娃,鄂尔多斯杭锦旗人,蒙古族。著有短篇小说《醉阳》《热恋中的巴岱》,长篇小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