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逝世八周年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出版,拾遗亲友往还
1998年12月19日,一代鸿儒钱锺书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2016年5月25日,钱锺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撒手人寰,享寿105岁。为向这对20世纪中国文坛最耀眼的学者伉俪致意,亦是纪念杨绛先生逝世八周年,今年五月,《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问世。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书封(本文配图 三联书店提供)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由杨绛的遗嘱执行人吴学昭整理。今年已经95岁的吴学昭是著名教育家吴宓之女,而吴宓又是钱锺书、杨绛两人在清华大学就读时的老师,两家素有往来。据介绍,吴学昭在退休后,常帮杨绛打理事务,两人可谓是“闺中密友”。接触交流中,她们也时常谈论往事,闲话家常。正是有着这么一层亲近信赖的关系,2008年,吴学昭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是唯一一部征得杨绛首肯后传世的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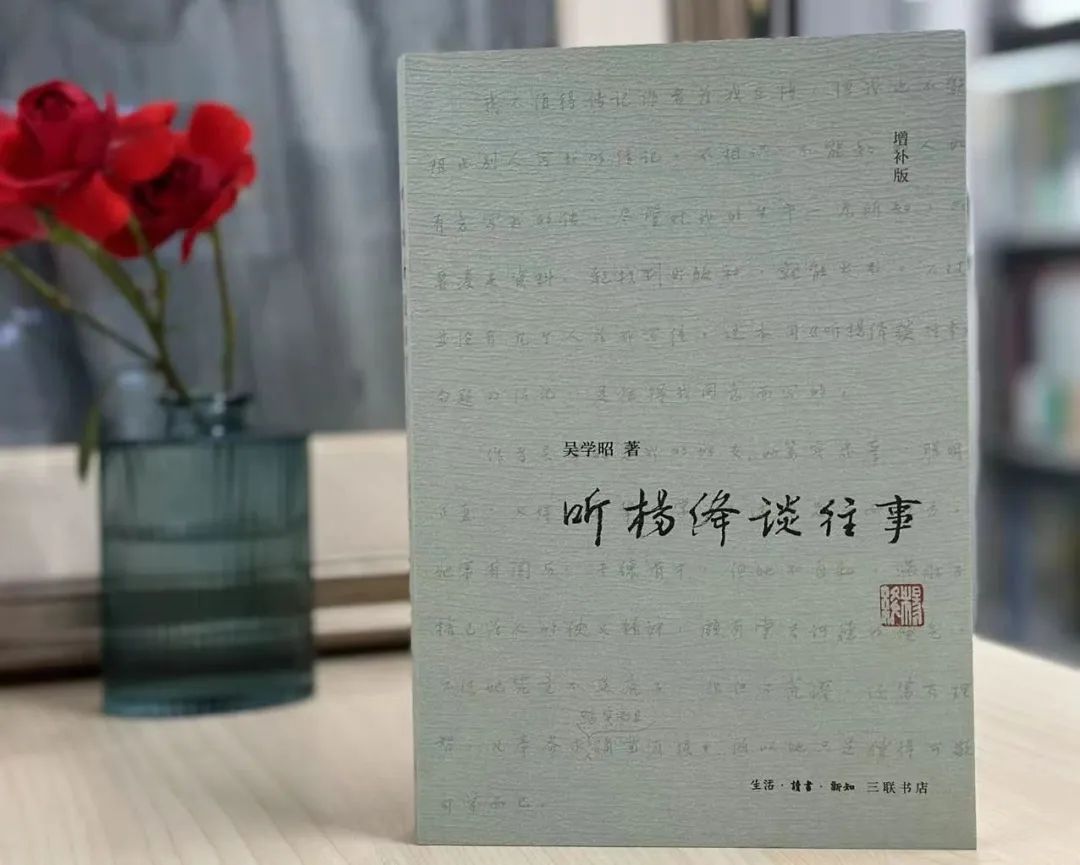
《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吴学昭 著
杨绛逝世后,遵照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堪为逝者一生高洁,“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终极写照。在逝者生前亲自审定的讣告中还特别写明,“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开篇“整理者言”中,吴学昭写道:“杨绛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认为很必要的事,是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先生和她本人的日记,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虽然我觉得很可惜,曾多次劝阻,但未能让她回心转意。”
“那天在她的卧室聊天谈心,杨先生想解释一下她日前销毁日记和友人书信的缘由,我没让她往下说。2013年那场关于拍卖钱杨书信的维权诉讼,经过与法学家们一年多的并肩抗争以及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虽然最终得到了圆满结局,但私人书信竟被当作商品用来交易,毕竟伤透了杨先生的心,我能理解她这样做的无奈及隐衷。”
吴学昭表示,“我相信杨先生自毁的日记和书信,数量也不会多。实际上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后来的社会动乱,一般人很少能完整地保存自家文稿、日记和书信。”那天见面话别之际,杨绛从橱柜里捧出一个大布袋,幽幽地对她说:“这都是我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我近来愈感衰弱,自知来日无多,已没有心力处理这些信件,现在把它们全部赠送给你,由你全权处理,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写信人中,不少你都熟识,哪怕留个纪念也好!……”
读毕杨绛相托的书信,吴学昭联系此前所知的一些片段,对许多事顿有豁然贯通之感。“我越读越投入,越读越感动,也更理解了杨绛先生何以不忍心销毁它们。这哪是些普通信件?它们荷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是极为珍贵的文史资料!如何处理这些书信,成了我面临的一道难题,也成了我一块心病,我只有找杨先生商量。”
其时,杨绛的健康已每况愈下。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前,吴学昭向杨绛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您留赠我的书信十分珍贵,您都下不了手撕掉,我更不敢也不舍毁弃。这些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宝贝,不宜由我个人私藏。我的想法是:争取在我有生之年得空时亲自将它们整理翻译出版,留给社会,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然后将原件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收藏。”杨绛听罢笑着肯定,“所见相同!可谓灵犀相通。”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吴学昭在“整理者言”的最后写道:“我因有约在先,直到整理、翻译、注释完《吴宓师友书札》,编著好《吴宓年谱》后,方着手整理、翻译、编辑和注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并与诸多写信人(包括已逝作者的家人)联系,获得授权同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总算不负杨先生所托,完成了这项工作。”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全书收入致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信函277封,以及钱、杨二位的若干复函。这些信函始自1946年,至2014年止,多集中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信函作者包括二位先生的至亲好友、学者同人,乃至译者、读者逾90人。所收信函呈现了钱锺书和杨绛的部分工作、生活、心境、交往、论学状况,既是时代的记录,也见证了学人之间的友情和思想共鸣,于学术史当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信中的一些内容不仅可补罅年谱、别传的失载,也为读者认识钱、杨二位先生的多种人生向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为胡乔木“改诗”,“愿这友谊永存”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胡乔木(1912—1992)堪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30年代,胡乔木和钱锺书同在清华大学读书,情谊甚笃。之于两家的过从交往,杨绛曾在《我们仨》中这样写道:
“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锺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
钱锺书、杨绛夫妇和胡乔木、谷羽夫妇(胡木英摄)
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同钱锺书间的交往,有一段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轶事便是“改诗”。《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胡乔木(十七通)”章节还原了这段往事的全貌。1982年,胡乔木七十感怀,写诗四首七律《有所思》,并寄给钱锺书指正,不想后者涂改批注很多。这让胡乔木一下子有些为难,他告诉李慎之,“我做旧诗总是没把握,因此,请锺书给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
作为胡、钱两人共同的朋友,李慎之心知“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他向钱锺书直陈自己的理解,“乔木是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像‘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句子,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你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
钱锺书听罢立刻会意,说“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在给胡乔木的复信中,他明确表示“僭改的好多不合适”。“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Pope, an Essay on Criticism(英国作家亚历山大·波普,著有《批评随笔》)的箴言:‘A perfect judge will read each work of wit, with the same spirit that its author writ.’(秉持作者书写的精神,是一个完美的评判家在阅读每一部作品时应有的智慧。) ”
虽然表示“新改本都满意”,耿介的钱锺书还是在信末提出,只有“风波莫问愚公老”一句,“觉得‘愚公’和‘风波’之间需要搭个桥梁,建议‘移山志在堪浮海’,包含“愚公”而使“山”与“海”呼应,比物比志,请卓裁。”就此,胡乔木在回信中称,“拙作承多次指正,又承奖誉过当,甚感甚愧。”并表示,“承您三次来信,这几首小诗确已成为我们友谊的纪念了。愿这友谊永存!”
最终,七律最后一首诗作定为:“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两位老同学间的书信往来虽字斟句酌,却一派率真磊落,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吴学昭在“整理者言”中介绍说,从时间上看,(杨绛最后托付的)绝大多数的信,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时间,一向低调沉默的钱杨夫妇好像忽从多年噩梦中苏醒,迸发出了巨大的创作力。杨绛的《干校六记》写成后,起初怕触犯时忌,不敢在内地出版,拿去了香港。胡乔木同志读后立即带话给文学研究所说:这本书内地也该出!在1983年欢迎赵元任的宴会上,又对钱锺书讲了他对该书的十六字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不讲、不提《围城》,此人便算不得‘in’person”
1978年9月,意大利北部山城奥蒂赛伊(Ortisei)召开的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期间,钱锺书走出关闭了十年的国门,这也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国访学。他在会上生动回顾了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并介绍了我国文学的概况,最后高呼:“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全场掌声雷动。自此开始,充满好奇心的外国作家、学者频繁访华,交流互动,钱、杨亦成为接待这类外宾的忙人。
在吴学昭看来,“钱先生出访顺利,对陌生的海外学术界能应对裕如,钱、杨作品能成功推向世界,被钱锺书称为‘文字骨肉’的知己好友宋淇(悌芬)先生功不可没。”宋淇(1919年-1996年)为我国著名藏书大家宋春舫先生哲嗣,出身燕京、光华,上海沦陷时期与钱先生相交甚密,每周前往钱府问学,评书论文,无所不谈。据宋淇回忆:“那些年,深觉受益于正规教育者少,而受益于钱锺书的熏陶最多,做学问、写文章都时时不敢忘却钱先生的训诲。”
作为在1949年后移居香港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宋淇也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人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影业出品的多部影片,如《空中小姐》(1959)、《花好月圆》(1962)等的制片人,都是邵逸夫所深为倚重的宋淇。小说《围城》1947年初版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在内地再次重印,旋即也推出港版。
1981年年初,宋淇向钱锺书去信提到,“《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恐不如内地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然而,这一次宋淇显然低估了香港读者对《围城》的热情。前封去信一个月后,他再度给钱锺书写信汇报。“大作《围城》新版运到后,大受读书界注意,报章上评介几无日无之,当择其无碍语者影印寄上。而且此书越传越广,连家庭主妇都以一读为荣,几如当时竹枝词:‘闲谈不说红楼梦,谈尽诗书亦枉然。’任何人在香港口中不讲《围城》,专栏中不提《围城》,此人便算不得‘in’person。晚前估计大作在港销路恐有问题,此回要‘跌眼镜’矣。”
据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回忆,父亲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八封。“我爸爸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但钱锺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
早年投身电影业,人到中年之后,宋淇则斩断“银”丝,甚至戒掉了看电影的习惯,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他在主持翻译研究中心期间创办了《译丛》(Renditions)期刊与丛书,专事英译中国诗学、词学、史学及现代文学作品,宣扬汉声,不遗余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便已开始筹划推动《围城》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并亲为校阅修改译稿。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收录宋淇信笺二十八通,首封来信写于1980年年初。此前一年,69岁的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术交流的讲坛上登台亮相,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妙语连珠的外语对话令众人折服。宋淇在这封信的开篇便提到,“忽闻大驾出国‘表演’,心中高兴不言可知。”
信中,宋淇还力邀钱锺书“有无可能来此讲学一月,作公开演讲三至七次。”“新亚学院(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正式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有‘钱穆讲座’之设,对象是国际间有极高声望的学者,第一届为钱穆本人,第二届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第三届拟请锺书先生。如能前来,未始不是一次大突破,一露身手,必可有空前绝后之盛况,impact之大无可比拟。”考虑到钱锺书有哮喘痼疾,信中还特为说明香港天气温暖,“很少冷达摄氏十度以下,尤其今年冬行春令,舒适异常,不会引发哮喘病(校中还有一位全港内科的第一把手)。春天(四至五月)和秋天(十至十二月)尤其宜人,绝对不用担心。”
不想,钱锺书在回信中婉言谢绝。“承兄邀请,真正‘受宠若惊’!我若来港,主要是为见兄夫妇一面……至于讲学,已无兴致,亦无能力……七十老翁,不宜走江湖卖膏药了!另请高贤,盛情只有感激而已。”再次复函中,宋淇就此表示了理解。“事实上,这生意经也是友人所主动,如果不试一次,他们一定认为我不愿尽力,现在也好让他们死了心。钱穆讲座不来也罢,大家尊他为史学大师,前二十年他为文云莎士比亚远比不上杜甫,给少壮派学者写了一文:‘为五四下半旗’!其实先生这位同乡应有自知之明,你就谈谈国史好了,兰姆的莎氏乐府都不知道看了没有,真是何苦来?”
守望相助,“我们有他,是我们的幸运,这时代有他,是这时代的运气”
1998年,钱锺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实非常人所能体味。在回忆录《我们仨》中,她曾感叹:“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中收录了众多友好对杨绛痛失爱女和丈夫的慰问信,读来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及现代汉语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亦是德语版《围城》《我们仨》的译者,被钱锺书视为“文学女儿”。听闻钱先生过世后,莫芝宜佳在给杨绛的信中写道:“我不知能对你说什么,不知怎样能给你些安慰,只愿我一直是你心头的一团温暖,你什么时候都有我,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个人。钱先生走了,可他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永远有他,中国永远有他,世界永远有他。报上登了中国领导人、法国总统等都表示极沉痛的哀悼,中国和世界都是该感谢钱先生的。我们有他,是我们的幸运,这时代有他,是这时代的运气。”
莫芝宜佳回忆说,“最初,我读中文,是读‘孔孟之道’或是‘革命文学’,是1978年在意大利听了钱先生的报告后,中国文学才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后来通过翻译《围城》,读《管锥编》,可谓茅塞顿开,开了窍,发现了博大精深又充满智慧的中国文学的无穷魅力,去掉了许多狭隘偏见,读文学也变得满是乐趣。”
法国汉学家、翻译家郁白(Nicolas Chapuis),曾独自翻译出版了杨绛的小说《洗澡》,与钱、杨夫妇有较深的友情。时任法国驻沪总领事的他在同杨绛致信时写道:“我将终生铭记他于心:虽然我们相遇次数很少,但我们的谈话却如此富有启发性、富有成效;他如同我的灵魂之父,我为他的离去而哭。我将努力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他总是怀有最高期待却不提要求。请放心,我的思想和内心都支持您。”
时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唁函中写道,“钱锺书先生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智慧、优雅、善良、开放和谦逊……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为文化历史所铭记,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漫画家华君武与钱、杨夫妇同住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多年,相互关心,时有往还。上世纪90年代初,钱先生以《围城》电视剧上映而引发所谓的“钱锺书热”炒作不休不堪困扰;华君武立即发表一幅题为《先生耐寒不耐热》的漫画,为老友解围,画中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坐在浴缸中作痛苦状,四周蒸汽氤氲,头上四把分别标注“钱”“锺”“书”“热”的烫水壶仍不断往里加热水。杨先生称华君武先生为难得的“好邻居、好朋友”。华君武迁居后,还时来电话问候。
1996年,钱锺书和杨绛的爱女因罹患脊椎癌入院,华君武在给杨绛的信中写道,“我听到钱瑗住院。我不敢来看你,因为你的精神负担太重了。我无法帮助你,也无法安慰你。我的画册出来了,我用第一本来送给你,一是祝锺书同志能好起来,二是祝钱瑗早日康复,三是请你保重。”
至亲情深,“劳可节则节,心得放且放”
除了同友人间的鱼雁往还,《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中还收录了钱、杨二人至亲戚属的来信若干。在教育家钱基博(1887-1957年)去世前一年给“先儿”(钱锺书小名“仰先”)的手谕中,落笔就显现出一片舐犊情深。“昨日见汝致声淮(石声淮,钱锺书的妹夫,常年与钱老先生生活在一起)书,悉检查血管是否硬化,结果如何?极念。老人病是当然。汝夫妇正在中年,未来许多担荷压在肩上。我不以老病为忧,而愁汝辈之衰早。劳可节则节,心得放且放,不必以老人为念也。”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1878年—1945年)是近代革命党人、法学家。杨家姊妹兄弟一共八人,杨绛原名杨季康,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孩,家里人称她“阿季”。阿季上面是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下面两弟两妹——大弟、小弟、阿七和阿必。阿季姐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高,其次是三姐和七妹,阿季居中最矮。爸爸曾为阿季辩护,笑说:“猫以矮脚者为良。”
说起“杨绛”一名的由来,也要拜家中姊妹所赐。抗战时期,阿季写了一部剧本《称心如意》,被导演看中,要排演。可是阿季怕出丑,不敢用真名,想起平时姐妹们嘴懒,总把“季康”二字说成“绛”,就叫“杨绛”吧。于是,“杨绛”这个名字才用到了今天。
长姐如母。1920年春季,已留校任教的大姐杨寿康带着三姐和阿季去上海启明女中上学。这是阿季第一次离开父母,好在有大姐和三姐朝夕相伴。大姐大阿季十二岁,管着阿季的衣食住行。是以阿季有心事都会说给大姐听。日后在清华借读时,阿季与钱锺书恋爱,也是先把这段感情告诉了大姐,再由她转告给父母。
杨寿康在启明女中毕业时,中文和法文均是第一名。由于法语娴熟,曾翻译法国小说家波尔才(Paul Bourget)的著述《死亡的意义》( Le Sens De La Mort),1940 年商务印书馆于作为世界文学名著出版。明代天文家徐光启的后裔,天主教神父徐宗泽为该书做序时称,“这书现在由杨寿康女士介绍到中国,译笔流利,忠实,美丽,合乎‘信达雅’的条件,足以传达著者底高尚思想,给予醉生梦死者以绝好的教训。”
杨寿康信奉天主教,终身未嫁。解放后在上海与三妹闰康一同居住,生活上由杨绛供养。在一封给杨绛的家信中,大姐先就写道,“来信汇款都已收到,谢谢你。”接着便关心起四妹的身体,“你拔牙伤元气,我很觉不安。牙齿作怪这一阶段我有经验。等全部拔光,全口装上才能相安无事。牙床上生骨刺,又是一件麻烦事,看来只能忍痛切开牙肉铲去骨刺。一个人老了,身体上的麻烦事真多。”
在舅舅的女儿唐瑞琳上世纪80年代给杨绛的一封家书中,则可以窥见杨家的庭训家风。“二姑父、二姑母(指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荌)在我心目中一向是使人十分敬仰的人物。记得大姊告诫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时,总是说二姑父怎么怎么讲的。我记得很清楚,二姑父讲的两件事。一是二姑父说:‘穷的时候,不要勉强与有钱人应酬来往。’二是二姑父说:‘挣了钱,要有计划积蓄,要不怎好开口向人借贷。’这两句话对我们家当时的境况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也一直记着未忘,并常以此自戒。”
小说《围城》在1980年再版重印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从唐瑞琳的书信中,也可见得家人之中也讨论得兴味盎然。“我看《围城》,也很喜欢‘对号入座’,志在亲戚中找模特儿。这次看了你的《记钱锺书与〈围城〉》,都明白了。书中的方鸿渐写得很可爱的,我最佩服他的敢于回绝苏文纨的婚事。我对唐晓芙有个模式。我祖父逝世后,三朝成服,你与二姑母一起来的。我记得你穿了件粉红色的宽袖衣,外罩淡湖色的旗袍背心,面色又白又嫩,好像水蜜桃一样。《围城》中的唐晓芙就是这个样子,她也是律师的女儿。我这想象对不对?望批评指出。”
对也不对呢?请见这一页下角的“整理者按”:杨绛在这封信的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表妹唐瑞琳认识唐晓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