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尔迦:一个“戏剧的狂热爱好者”
1936年6月炎热的一天,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在马德里一位友人家中,为朋友们朗读自己刚刚完成的剧作《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La casa de Bernarda Alba)。在这个以“二七年一代”诗人群体为活动核心的文人圈子里,聆听洛尔迦朗读作品一直是大家公认的乐事。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聆听诗人亲自朗读他的《古怪的鞋匠老婆》(La zapatera prodigiosa)、《血的婚礼》(Bodas de sangre)、《叶尔玛》(Yerma)、《老处女罗西塔或花的语言》(Doña Rosita la soltera o el lenguaje de las flores),享受那富有韵律的词句,被强烈的戏剧冲突所震撼,为悲剧性的结局慨叹,进而热烈期盼作家以他充沛的活力和无尽的想象力尽快投入到下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去。只是这一次的结局有所不同。就在朗诵会后的第二天,忧心忡忡的洛尔迦深感日益紧张的时局所带来的压力,没有听从友人劝告离开危局中的西班牙,而是乘火车回到格拉纳达。但本想在家乡寻求庇护,在与家人的团聚中需求安宁的洛尔迦,却就此走向自己的人生终点。不久后,内战于7月17日爆发,格拉纳达很快便落入叛军之手。8月18日,洛尔迦被长枪党武装分子枪杀于比斯纳尔的荒野之中。

出生于1898年6月5日的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以诗成名,早期的《歌集》(Canciones)、《深歌集》(Poema del cante jondo)在洛尔迦二十多岁时就已广为传诵,后来的《吉卜赛谣曲》(Romancero gitano)更是让他享誉诗坛,而当他开始戏剧创作后,其独特的创作角度和戏剧语言又让他成为西班牙剧坛的杰出代表。在洛尔迦的戏剧作品中,《血的婚礼》《叶尔玛》和《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习惯上被称为“乡村三部曲”,是他最有影响力的戏剧作品,直到今天还常常被搬上舞台,具有穿越时空的舞台感召力,成为西班牙戏剧的经典之作。
纵观洛尔迦的整个戏剧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完成“乡村三部曲”之前,洛尔迦曾走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探索之路。首部公演的戏剧作品《蝴蝶的妖术》(El maleficio de la mariposa)一俟上演便遭恶评,让初试戏剧创作的洛尔迦备受打击,沉淀七年后才又写出以西班牙19世纪自由派女英雄为主角的《玛丽亚娜·皮内达》(Mariana Pineda),并开始在剧坛崭露头角。从20世纪30年代起,受当时欧洲文艺领域先锋主义
盛行的大环境影响,洛尔迦在诗歌和戏剧领域都开始尝试先锋派创作风格,在1930年至1933年间,创作了《诗人在纽约》(Poeta en Nueva York)、《观众》(El público)、《就这样过五年》(Así que pasen cinco años)和《堂佩尔林普林与贝丽莎在花园中的爱情》(Amor de don Perlimplín con Belisa en su jardín)等有着显著先锋特点的诗歌和戏剧作品。在那几部剧作中,洛尔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引入了很多在其他作品中出现过的因素:人类的情感、戏剧的理论认识、对社会的观察、文字游戏等等,使作品具备了深刻的戏剧性和丰富的表现层次,但同时他也宣称,这些作品是无法表演的“不可能的戏剧”,因为当时的西班牙观众并不具备能够理解作品所传达信息的基本能力。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完成了先锋戏剧创作的探索阶段后,洛尔迦就试图通过另一条途径来实现与观众或读者的交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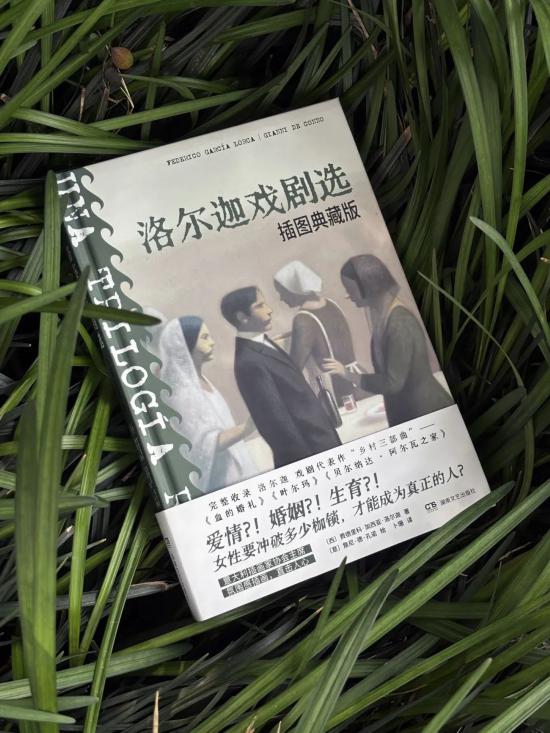
从1933年起,洛尔迦又回归了他创作《玛丽亚娜·皮内达》和《古怪的鞋匠老婆》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重新开始创作那些既能取悦于观众又能取悦于投资者的戏剧作品,同他先锋时期的作品相比,他成熟时期的作品多半取得了经济意义上的成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洛尔迦的这种对“现实主义”风格的重新启用并不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回归,而是在长时间实践的磨砺后向更高层次的进发。对于戏剧对观众的教化作用,洛尔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30年代的戏剧创作中,他一直将这一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宗旨之中,注意为自己的戏剧作品选取适合他所属时代观众的题材和场景,这是他在经历了无数实验后日趋成熟的标志,也成为日后他的作品广受欢迎的基础。
《血的婚礼》《叶尔玛》和《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便是洛尔迦戏剧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其共同之处便在于它们都表现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乡村生活中的真实场景。洛尔迦曾在格拉纳达附近的富恩特巴克罗斯和阿斯克罗萨乡间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对于这一地区乡间生活的熟稔使得他在三部曲的题材选择、场景设计和人物塑造方面都自然而然地凸显了安达卢西亚的地方特色,以呈现他在现实生活中早已熟悉的故事、场景和人物。
1928年7月25日,彼时已在马德里“大学生公寓”居住学习的洛尔迦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涉及发生在阿尔梅里亚尼哈尔村的一桩罪案。一位新娘为与旧情人私奔,从自己的婚礼上逃走,愤怒的新郎率众追捕,进而引发流血冲突。这桩血案的发生和结局给洛尔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以此事件为素材进行构思,并在1932年完成了《血的婚礼》。剧中的新娘与莱昂纳多本有情意,但因后者家境贫寒而无法终成眷属。莱昂纳多另娶门户相当的女子成家生子,而新娘则不得不顺从父亲的意愿与田产丰厚的新郎相亲,并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成亲。可就在婚礼当天,新娘与前来观礼的莱昂纳多旧情复燃,决定逃婚私奔,与莱昂纳多家族本就有世仇的新郎在母亲的催促下愤而追赶。在化身为月亮的死神的注视下,逃亡的情侣和追击者们终于相遇,莱昂纳多与新郎拔刀相向,最终用生命祭奠了一场血的婚礼。
《叶尔玛》的主人公是一个婚后多年饱受不孕折磨的女人。她嫁给丈夫胡安只是为了做一个母亲,如果无法达成所愿,她就无法理解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婚后多年不育的结果,让叶尔玛觉得自己的命运就像一条通向干涸池塘的水流,即使到达终点也终将不会有生命诞生。她曾期盼能通过祈祷得到神的祝福,甚至不惜冒险去参加带有巫术色彩的朝圣集会,以求实现受孕神迹,但在认清朝圣集会背后那有违社会道德准则的真相后,她又决然放弃。就这样,在经历了从最初的希望到失望再到最终的绝望的过程后,叶尔玛杀死了丈夫胡安,也亲手扼杀了自己实现人生意义的唯一希望。
叶尔玛的悲剧命运在洛尔迦的现实生活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洛尔迦的父亲堂费德里科的前妻玛蒂尔德·帕拉西奥在和他共同生活了十四年后因病去世,身后未留子嗣。几年之后,堂费德里科与维森达结婚,并在婚后诞下二子二女,长子便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幼时随家人居住在阿斯克罗萨时,洛尔迦的卧室床头上方曾挂着一幅莫克林的布衣耶稣的石版圣像画,据说就是父亲早亡的前妻玛蒂尔德所遗。在安达卢西亚乡间,莫克林的布衣耶稣被认为具备可令不孕不育之人受孕生子的神力,并因此而广受崇拜,围绕着这一形象进行的求子朝圣集会在乡间也频频可见,这些无疑都对洛尔迦构思《叶尔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当看到那幅圣像,一个未曾生育便已离世的女性形象便会出现在他脑海中,让他将不孕不育与悲剧命运联系起来,并在多年后经这种关联呈现在《叶尔玛》的舞台上。
洛尔迦幼时非常喜欢去拜访他的姑妈,在姑妈家那所典型的安达卢西亚村居院落里有一口深井,而与姑妈家共用这口井的是女邻居弗拉斯基塔·阿尔瓦,姑妈和堂姐妹们关于这位女邻居一家生活情形的描述和评论,让洛尔迦对未来的《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有了最初的构画,而另一位亲戚帕卡·马苏埃科斯在女儿离世后便长年穿戴丧服一事也成为洛尔迦的素材,被用于《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的人物塑造,成为包括贝尔纳达和她几个女儿在内的女性群像身份的标志性元素。
与先锋时期的作品相比,“乡村三部曲”中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退居到相对次要的层面。艰深、晦涩的主题和语言消失了,人物也显得更接近现实生活,情节的设置和发展也在竭力顾及观众的理解力。三部曲中的人物——新娘、叶尔玛和贝尔纳达——身上所集中的特点强调了她们作为“目标虚构”人物的性质,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使她们各自的生活都带上了强烈的戏剧性。
《血的婚礼》中,内心真实的情感要将新娘推向莱昂纳多,但世俗的规范又让她承担未婚妻的职责。如果这是一个完全来自现实的人物,新娘会试图克服情感的煎熬,与看起来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男人成婚,同时注意不去违背社会对其行为的期待,也就是说,她会牺牲一定的自我,避免让它推动自己去犯下有违社会规范的错误,同时也避免去破坏被社会所认同的传统婚姻。但新娘是一个“目标虚构”人物,她的身上同时具有“堕落女人”和“贞洁少女”的双重身份。新娘与莱昂纳多一起逃跑是《血的婚礼》的戏剧高潮,此时,主导新娘性格的是“堕落女人”的身份,很明显,新娘已经摧毁了环境施加在她身上的一切控制力,在那一刻,她掌控着自己命运的缰绳,而其他人,在使他们变得格外软弱的环境的压力下,听凭自己的生活被任意摆布。
叶尔玛算是洛尔迦所创造的最成功的“目标虚构”人物之一,即使她独自出现在舞台上,其戏剧表现力也不会有丝毫减弱。叶尔玛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内心独白,她身上反映出一些洛尔迦先锋时期作品中人物的特点,因此也就集中了不少相互对立的特质。表面上的现实显示出叶尔玛是一个因为无法生育而痛苦的女人,命运已经判定她无法完成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女人应完成的职责。观众们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处于这种境地中的女人应该表现出的行为,她的言谈举止中的激烈表现都缘于她做母亲的企图的落空。但如果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通过主人公的话语,洛尔迦在向观众暗示一个隐藏得更深的事实,一个真正的事实。当叶尔玛说道:“就在那些墙壁后面封闭着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因为那些事儿根本没人听见。”她的话直接指向了造成她痛苦的真正根源。叶尔玛不能生育的事实只不过是她失败的表面原因,从这里产生了人物的二重性
。观众们能够认同和理解的是叶尔玛作为不孕女人的可悲命运,但是这部作品的真正悲剧性却来自叶尔玛的孤独,是她作为农村女性而注定承受的孤独。剧中有许多意象都在表明叶尔玛在孤独中的感受,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动物和花朵时刻向她展示着生命的繁衍和延续,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一个无法生育的女人倍感痛苦和孤独。就在与丈夫的相处中,叶尔玛体会到了这种将她同自然的和谐分离开来的障碍,以及在这种障碍面前产生的挫败感,她言谈举止中的歇斯底里都缘于她想在自己身上找到“有活力”“自然”这些因素的愿望的落空。在全剧的终场,观众可以通过舞台上的表演得知叶尔玛愿望的落空实际上缘自胡安的不育,但在全剧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叶尔玛戴着不孕的面具来维护着丈夫的名誉,而她的不孕也是观众们在观看这部作品的第一时间里形成的概念。叶尔玛的悲剧在一层掩饰的幕布后面发展着,洛尔迦让自己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双重性,观众们在舞台上既可以找到符合传统家庭概念中女性形象的叶尔玛,也可以找到为了找到自我而在事物的另一个层面上不断寻求的叶尔玛。在观众们对这种对立的双重性格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作品便可以更容易地走近他们,为他们所接受。
在《贝尔纳达·阿尔瓦之家》中生活着梦想自由和爱情的女性,但这两个梦想也正是贝尔纳达用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来压制、消灭的对象。富有的贝尔纳达·阿尔瓦刚刚办完丈夫的丧事,一回到家中便对五个女儿宣布,家中一切事务均须唯其令是从,其中当然也包括她们各自的婚事。五个女儿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不满,但真正将不满付诸行动的,只有最小的女儿阿黛拉,但她对自由和爱情的勇敢追求最终被母亲贝尔纳达镇压,而阿黛拉只能用死亡做出最后的抗争。从剧情设置中可以看出,贝尔纳达的性格在她女儿们的身上得到了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女儿们表现了她的不断变化的自我。女儿们出于惧怕而服从母亲,因为她们有着相同的本质。除了阿黛拉之外,其他的女儿都是潜在的贝尔纳达。贝尔纳达强加在女儿们身上的束缚在阿黛拉那里遭到了激烈的反抗。贝尔纳达和阿黛拉代表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力量,而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我们在新娘和叶尔玛身上都能找到踪迹。贝尔纳达所代表的力量在叶尔玛身上是她因自己的不孕而产生的对丈夫的仇恨,而表现在新娘的身上,则是在她内心纠缠不去的对“美德”的倾慕。阿黛拉的形象则会让我们想到试图摆脱早已注定的命运却不得不陷入绝境的叶尔玛,而阿黛拉与新娘之间的相似之处则更为明显,两个女人都在用自己的存在去冒险,以获取真正的爱情。新娘和叶尔玛都可以作为完全独立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而贝尔纳达和阿黛拉作为舞台上的两个重要形象却彼此需要,缺一不可。在她们身上集中了戏剧的冲突:如果没有贝尔纳达,阿黛拉的抗争将失去动力;同样,阿黛拉的抗争也会使贝尔纳达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与三部曲的戏剧情节设置相比,这些女性人物的存在本身具有更大的感染力。这些女性在她们周围创造出与她们的内在悲剧相符合的氛围,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步步展示自己的内心。三部作品都是以死亡为结局的,但死亡的事实并没有构成戏剧表演的高潮,作品的悲剧性体现在舞台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没有像传统戏剧那样让观众在高潮中停留在剧中所表现的悲剧时刻。新郎和莱昂纳多的死、胡安的被杀、阿黛拉的自杀只不过构成了戏剧发展逻辑过程的一个部分,更具冲击力的部分发生在这些高潮时刻之后:新娘与新郎母亲的哀怨声,叶尔玛的“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儿子”,以及贝尔纳达·阿尔瓦那句“肃静!”,都成了三部曲直击观众心灵深处的最强音。
戏剧是一所充满哭泣和笑声的学校,它还是一个自由的讲坛,在这里,人们可以揭露出那些旧有的或者是错误的道德伦理,可以以生动的例子来解说指导人类情感和心灵的永恒的规范。……那些没有反映出社会和历史的脉动,没有表现出人们的生活和那些风景和精神的真正色彩的戏剧根本没有权利被称为戏剧。
1935年2月1日,在马德里“西班牙剧院”的舞台上,洛尔迦向刚刚观看完《叶尔玛》演出的观众们讲了上面这段话,道出了他对于戏剧创作的见解。在洛尔迦的眼中,戏剧舞台是艺术家与民众交流的最佳桥梁,他需要不断地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和实践,从中感受光荣、羞愧、欣喜、悲伤,为所有人“打开自己的血管”。
“戏剧的狂热爱好者”,洛尔迦这样称呼自己,这种对戏剧的热爱来自他对生活的独特认识,正像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的那样,洛尔迦认为生活就是一个戏剧的大舞台,一个将生活与戏剧融为一体的人,势必会将他对生活的热爱转化成对戏剧的狂热之爱,并且让这种爱持续一生。虽然1936年长枪党党徒的枪声为洛尔迦的人生戏剧残酷地画上了句号,但从他留给我们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位诗人和剧作家对戏剧创作的真挚的爱,这种情感也势必会随着他的作品流传久远、绵绵不绝。
本文收录于《洛尔迦戏剧选:插图典藏版》,原标题:《乡村三部曲:一个诗人的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