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的三重奏:自我与他者的博弈
1941年夏,西蒙娜·德·波伏瓦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小说原名《正当防卫》,后定为《女宾》。该作品的女主人公是复数——弗朗索瓦丝与格扎维埃尔,书名却是单数——一位女宾,究竟指谁?或许两者皆可。被邀请到何处?当然是现实中由萨特发起的“三重奏”关系。
在谈论这部小说之前,原型是绕不过的话题。奥尔加·D ——格扎维埃尔的原型,是波伏瓦的学生,她苍白的脸,常被耷拉的金发遮掩着,她迷恋着波伏瓦,后认识萨特。在波伏瓦的自传《岁月的力量》中,另一个名为玛丽·吉拉尔的女子——萨特一个学生的妻子,也有着格扎维埃尔的影子,波伏瓦这样描述吉拉尔:“(她)住在邋遢小旅馆里,经常几个礼拜待在房间里闭门不出,一个人抽烟,胡思乱想。她绝对不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活在一片迷雾里,只有无可回避的现实才偶尔让她清醒一点。” 小说中的热尔贝,原型为萨特亲近的学生雅克·博斯特。至于男主人公皮埃尔,则是借用了剧作家朋友杜兰的身份,人物的精神内核与脾性大体是按照萨特进行描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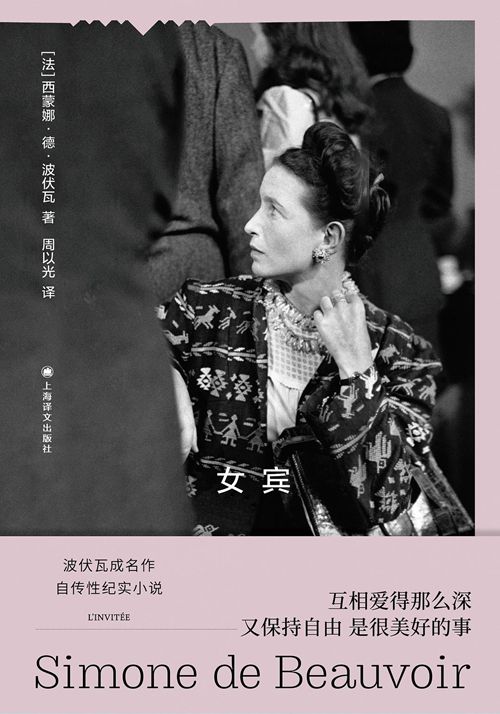
在回忆录《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还是少女的波伏瓦早早立下誓言,要写成属于自己的作品:“写成一部作品,我要在里面讲述一切,一切。”届时,她发现,这份意愿与贫乏的阅历形成奇特的反差。而数年后,她的阅历不仅不再贫乏,甚至称得上惊世骇俗。
波伏瓦坦白,她虽从奥尔加本人身上汲取了灵感,但“那是经过系统变形的”,为了让更多戏剧性冲突自然地生成,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创造了更为极端的情绪、复杂的人格;至于皮埃尔令人尴尬的行为——透过锁眼窥探格扎维埃尔与热尔贝拥抱,并非萨特的真实经历,而是取材自现实中的朋友马尔科。当时,马尔科热恋着作为热尔贝原型的博斯特,偷看了博斯特与奥尔加的亲昵场景。在《岁月的力量》中,以上信息皆有详细记录。当然,《岁月的力量》更多的是记录了二战前后整个法国的时代全貌,涉及的人物数不胜数:毕加索、朵拉·玛尔、加缪、贾科梅蒂等等。同时,该自传体现的是波伏瓦作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面向:更侧重自我思想的变迁、自己和萨特与时代的休戚相关。即使谈及上述的三重奏情爱关系,也是以保有距离感的客观来进行再述的。而一旦涉及小说创作,那便是另一种论调和姿态了。
当我们了解到艺术作品创作的各种虚构变形、挪用、再组合,我们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如果予以小说独立的空间,尽力忘却和现实对号入座,是否才是最大限度吸收作品的最好选择,是否才可以从文学述说的暴力中解救人物原型们?《女宾》的结构并不单一,波伏瓦试图以多元视角来构建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三重奏”,这是她作为作家的自觉。当然,各视角的比重悬殊,无法构成复调小说,但已有端倪。读者在共情人物弗朗索瓦丝的痛苦纠结后,眼见着皮埃尔的妹妹伊莎贝拉登场,该人物以自己独有的外部视角,冷眼旁观这段三角恋,我们将惊讶于这份有着深度内核的情感也可以是一文不名的,伊莎贝拉的虹膜质疑着,将其摧毁成最乏味的粉末。另一个人物热尔贝则以个人主义者的敏感察觉到这份情感中的“依赖金字塔”:皮埃尔依赖于自身的思想,弗朗索瓦依附于皮埃尔。他们要活在某种价值的世界当中。热尔贝虽没有提及格扎维埃尔,但富于联想的读者可以在他起的这个调子里,自行思索起格扎维埃尔与外界的关系:她不依附于任何价值。
谈到《女宾》的写作结构,顺延着上述的多元视角,我们将看到波伏瓦在众人物之间搭建了一个复杂精巧的关系网。皮埃尔、格扎维埃尔、弗朗索瓦丝的三人关系,与克洛德、伊莎贝拉、苏珊娜的三人关系,遥相呼应。格扎维埃尔在关系中显露出的嫉妒与排他性和伊莎贝拉类同,同时就人物的位置而言,她们两个都是插足旧情侣之间的外来者。
但波伏瓦的行文,又扰乱这种平行的镜像关系,她让伊莎贝拉和弗朗索瓦丝产生秘而不宣的关系:前者成为后者一个隐秘的影子。两人都在各自的三人组合中备受折磨,并与组合之外的第四个人产生关系,因此分别背叛了三人组合的某一个人。两个人物皆以第一视角袒露内心独白,都自问“自我”是否得到妥善的保护,也都惶恐地在自我的倒影中看到空壳的征兆。
弗朗索瓦丝在这段三人关系中察觉到早已存在于旧日二人关系中自我的消弭,她自问“我是谁?”,得到的是可怕的空谷回响,作者这样写道:“通过刚才透过她全身的白光,她所发现的仅仅是一片空虚。”没有什么是溶于她自身血肉的,甚至思想也只是挂件外物。长久攀附在皮埃尔身上的她,没有形态。格扎维埃尔的存在,很尖锐,它割开弗朗索瓦丝与皮埃尔长久共建的爱之堡垒,令弗朗索瓦丝在皮埃尔的脸上惊觉堡垒内部的衰败迹象。舞蹈家波勒的演出,折射出人物的处境:格扎维埃尔如痴如狂地沉浸其中,令弗朗索瓦丝羞愧于自身感知的麻木。伊莎贝拉也同样受困于这种虚空,她自感所有真实的情感都与她相隔,自己的画作乃至所有,都是一种对真实之物的模仿,她自觉是可悲的赝品。正如波伏瓦在《岁月的力量》中所述:“但是弗朗索瓦丝和伊丽莎白的关系更为紧密,后者对前者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质疑。”
面对这种空壳感,弗朗索瓦丝以审慎犹疑的态度接纳格扎维埃尔的介入,容忍后者不断扩大对三人组合的影响力。大量的内心独白,让她的动机在千丝万缕的思绪中如此模糊。波伏瓦曾写道:“在小说写得成功的几个章节中,意义变得含混,符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情形。我也不希望所有事件都循着单一的因果关系依次发展,而是希望它们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错综复杂地同时发生。”(《岁月的力量》)的确,弗朗索瓦丝温情与憎恨的反复循环会把我们弄糊涂。但别忘了,皮埃尔的处之泰然是他的外在表现,我们无法窥探其内心。在伊莎贝拉眼里,弗朗索瓦丝不也是一个冷若冰霜的人吗?自我在自己和他人的目光下,不断变换,未能拥有一个固定的形态。误解和反差似乎是真相本身。
他者,在萨特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中散发着寒气,在兰波的诗句“我是另一个”中展现自我建立的无穷尽。在波伏瓦的笔下,他者寻找到了完美形态——格扎维埃尔,有着不可支配的绝对他性。这个从鲁昂搬到巴黎的外省女孩,以卓绝的感受力、炽热的情感、对正统道德观的蔑视,成为皮埃尔眼中的黑珍珠,珍贵,也充满危险。她有一个大写的自我,她是完全自由的,胆敢摧毁任何看似珍贵的关系,她对线性的延展和保持嗤之以鼻,只活在此时此刻的炙热激情中。在长达近五百页的小说中,波伏瓦没有给予格扎维埃尔任何第一视角,她的内心是谜团,她的外在是混沌狂野,她以他者的强悍,入侵、蔓延、掠夺。有着极强主体性的皮埃尔能以自由的姿态承受格扎维埃尔这股凶猛壮丽的海浪,而弗朗索瓦丝则时常濒临溺死的境地,面临被剥夺固有主体身份的危机。对此,弗朗索瓦丝懊恼道:“她(指格扎维埃尔)突然变成主宰一切的唯一现实,弗朗索瓦丝则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她到了只通过格扎维埃尔带给她的感情来认识自己的境地。现在她试图同她合在一起,但在不现实的努力中,她的成果仅仅是自我消亡。”
无论弗朗索瓦丝内心有多么复杂、模棱两可,无可置疑的是,在她行为的延宕中,蕴含着她对于他者的容纳力,在自我完全被掌控前,在仇恨和恐惧尚未发展到极端境地之前,这种包容会一直存在。因为,任何消极事物中总有积极的营养等待被汲取。或许在这场关系中,弗朗索瓦丝渴望从中打捞隐秘的所得,填补自我主体性中干涸的空白,波伏瓦这样评论笔下的弗朗索瓦丝:“当她任由自己滑入激情的地狱中时,堕落中有一样东西给了她安慰:她的局限,她的脆弱,让她成了一个轮廓清晰、在地球上有明确归属的实实在在的人。”
各自割让一点主体性,维持优雅,提防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情感:嫉妒,是“三重奏”运行的根基,也是皮埃尔和弗朗索瓦丝秉持的“道德观”,他们以理性加以守护。嫉妒,是三人组合的命门,恰恰也是萦绕着的从未离去的物质。诚然,皮埃尔发起了这场微妙的跷跷板游戏,并设立了规则,但他无法主导:游戏能否继续,取决于三人能够以及愿意做到哪一步。格扎维埃尔尊重自己的人性,听凭直觉本能,任由嫉妒怨恨生发,并付诸行动打破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游戏在短暂的中断后能够延续,正是依靠着弗朗索瓦丝的理性和过剩的同理心。这种“监督作用”,如同一种强迫症,令她主动维持三人世界的运转,忍受碾轧,将自我退居其次。她的克制令皮埃尔的这场实验成为“杰作”,也让她衰竭。格扎维埃尔对弗朗索瓦丝所簇拥的这种旧道德(皮埃尔所赞许的道德)深恶痛绝,拒绝被驯服。两人的博弈来源于两种价值观的相悖,并各自争取着皮埃尔的支持。这绝非简单的争风吃醋。
整本小说描述的,是对自我与他者的观察:此消彼长,还是相爱共生?这是一场力学实验,也是人造理想国和原始人性的博弈:人性深处的刀尖在理想国的颓势中冒出头来,刺入这场实验的血肉中,让人毛骨悚然。为了接住这份惊悚,波伏瓦为结局安排了一场谋杀。这段暗夜谋杀,像是窒息之际的第一口呼吸,突兀且急促。它将近500页的纠缠、埋怨、进退维谷一笔勾销。《女宾》以大量的人物对话构建行文的韵律、情节的推进,人物内心的陡变,再以内心独白对对话进行分析、阐释、猜测或补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曾援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个概念非常适用于概述弗朗索瓦丝矛盾的行为轨迹:“黑格尔将‘绝对精神’定义为一个闭环(Schluss)。这不是指形式逻辑上的封闭性。黑格尔会说,生命自身就是一个闭环。……绝对的闭环是一种漫长而缓慢的闭合,闭合前会在他者那里充分停留。如果精神无法完全封闭自成一体,他者的负面性就会对它构成攻击,它会受伤,流血而死。”如同珍珠的形成与否,取决于扇贝是否愿意打开壳,是否有异质物滑入,扇贝是否能再度闭合双壳。弗朗索瓦丝将双壳打开的时间太长,自我贡献给皮埃尔再到格扎维埃尔,她回归自我的封闭行为已不再可能,当他者的恶意不断灌入时,她应激毁灭对方以便自保。讽刺的是,弗朗索瓦丝没能保全的,是她自始以来建立自我的根基——理性。最终,比格扎维埃尔更甚的疯狂贯穿了她。小说结尾有着不亚于安德烈·祖拉斯基名作《着魔》的力道——关于占有欲,对自我的,和对他者的。黑格尔的这句话,像雾气般弥漫在整个故事中:“每个意识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