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100多年前男孩心中的“日”与“夜”
来源:文艺报 | 行超 2016年07月08日17:54
 殷健灵
殷健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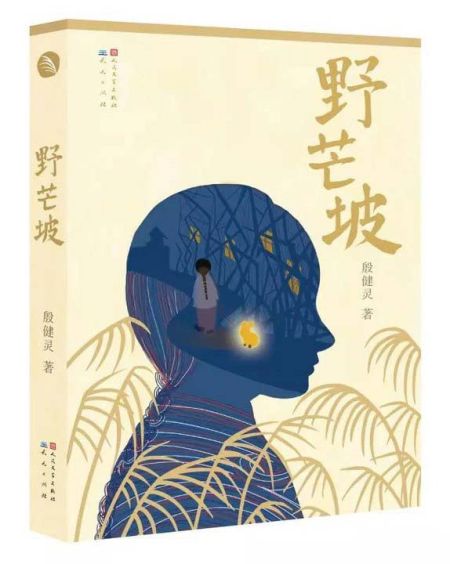
殷健灵新作《野芒坡》讲述了主人公幼安从小就失去母亲,在野芒坡找到了友谊和爱,而且显露出艺术天赋的故事。在作品中,殷健灵兼顾外在社会现实与内在心灵探索,以“土山湾”这一实际存在的孤儿院为背景,以直面人生的态度描绘了中国近代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加深了作品的历史深度。通过幼安的自我追寻,作者不单单描绘了一个孩子的心路历程,更发起了对于整个人类灵魂的追问。殷健灵说:“我想表现的不是主人公幼安的人生传奇,而是一个孩子在黑暗中寻找光亮、追索自我的心灵历程。”
记 者:大部分儿童文学致力于讲有趣的故事,吸引读者,而小说《野芒坡》却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细节描写,为什么这样处理?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好的儿童文学语言是怎样的?
殷健灵:《野芒坡》是儿童文学,但它首先是文学,得用文学性的要求来考量。那就不仅仅是需要故事的趣味,作品的结构、语言、立意、细节等等,都得符合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要求。这是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一不小心,就会让读者觉得生疏、单薄、隔膜。要把这样一个故事“撑起来”,必须有生活的质感。而营造生活质感最有效的手段,便是扎实的、与众不同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不是凭空臆造的,是别人无法想象却又合情合理、能引起共鸣的,是融入了作者自身或者他人的生命体验的。正是这样的细节,拉近了100年的时空距离,让今天的读者感同身受。在我看来,故事脉络只是小说的骨架,是枯柴一具,而细节是血肉,它们让小说真正“活”起来。儿童小说同样逃不开这个创作准则,丢失了生活质感,难免“符号化”“概念化”,何谈打动人的力量?
我私下有一个看法,语言是衡量作品可读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本身具有某种吸引读者的内在魔力,此种魔力可意会却难以言传。一部故事性不强却拥有“内在魔力”语言的作品,可以吸引读者读下去。而一部作品倘若语言乏味,缺少风格,空有一个好故事,也会令人难以卒读。因此,我写小说一向在意语言,每写一部不同题材的小说,都会更换一套语言体系。比如,早期写少女题材的小说《纸人》,注重营造神秘、缱绻、朦胧、清冷的调子,时用长句与比喻,与少女的独特心境相契合;写给幼童的《甜心小米》系列,则用平易朴素的“浅语”,一字一句都细细推敲,避用任何生僻字,也避用任何幼童感到费解的描写;以上世纪孤岛上海为背景的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是一个70多年前少年的独白,尝试了简洁有味的民国白话文风格;幻想小说《风中之樱》采用了宏阔华丽带有诗性的叙述调子……至于《野芒坡》,这是一部孩子能够看并且适合所有成年人的文学作品,她满足了我向经典文学语言致敬的愿望,当然,我依然会考虑少年读者的接受水平,尽量避免晦涩和繁复的叙述。
我想,好的儿童文学的语言是和故事、题材水乳交融、相映成辉的,首先是流畅的,是有亲和力的,也是有个性、有色彩的。
记 者:与一般儿童文学作品不同的是,《野芒坡》中探讨了信仰、艺术、苦难、死亡等深刻的人生问题,显示了作家的勇气和挑战精神。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是不是“难”了一点?有没有考虑过小读者的接受问题?
殷健灵:《野芒坡》出版一个月来,只要有机会面对小学生,我都会和他们分享这个故事。他们投入、专注的表情告诉我,他们喜欢这个故事,他们的心被主人公幼安的命运牵引,更从中感受到生命之光的力量。《野芒坡》探讨的主题是复杂的,我相信,不同年龄的孩子从中读到的东西自然有多有少,甚至有一些东西,他们现在未必能明白地感受到,却悄然埋藏于他们心底,随着年龄的增加,会一点一点显现。
儿童文学的主题不存在难易,更不存在主题的禁区,就看作者如何用头脑用心经营好这些主题。比如《活了一百万次的猫》这样的图画书,在短小的篇幅里,探讨了生与死、爱和被爱、爱的代价、自由与豢养、人生的虚无与有意义等诸多哲学命题,这些命题连幼儿都能在大人的启发下一一揭示,更何况《野芒坡》的读者呢?况且,我从来不低估孩子,他们是天生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的理解力、对人生的领悟力远在我们的估计之上。
记 者:《野芒坡》的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您在写作中也做了大量的采访考察工作,可否结合创作经验,谈谈作家应该如何处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
殷健灵:对于《野芒坡》来说,它所对应的真实就是那段清末民初“土山湾孤儿院”的历史,那段历史提供了纷繁复杂的史实材料,他们是有名有姓的神父、修士、嬷嬷、堂囝……几乎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人生故事,但是,他们只是“事实”而已,各自独立,存在于往昔,显得有一些苍白,缺少温度,更难以令人过目不忘。历史对于后人来说,往往仅仅意味着枯燥的年份、数字、事件……
但是,倘若历史的真实来到文学作品里就不同了,“土山湾”变成了“野芒坡”,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在这里,这一切元素掺杂在一起,产生了有关生命、有关人性的“化学反应”。小说这样一种体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容器,可以把那些真实事件放进去,进行鉴别、埋葬、挖掘、组合、分解、修饰、加工、扭曲、再创造。当然,首先要感谢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小说里的大量细节正来源于此。
在《野芒坡》写作准备的那5年里,我的头脑中长久地盘桓着土山湾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纷纷出场,又纷纷离场。他们彼此融合,又相互嫁接、重生。直到后来,他们渐渐脱离了原貌,却又带着旧有的印记,在我心中重塑成全新的人物。他们渐渐获得了生命,有了自己的呼吸和命运走向。我所做的,只是遵从自己真实的情感和体验去编织和架构它们。我想表现的不是主人公幼安的人生传奇,而是一个孩子在黑暗中寻找光亮、追索自我的心灵历程。幼安的身上,有张充仁、徐咏青、徐宝庆等大艺术家的影子,但是,幼安只是他自己,我更想写一个100多年前的男孩生命中的“日”与“夜”、“光明”与“黑暗”,是他内心世界可感可触的变化和发展。而这一切,只有文学才能够充分表达。
记 者:小说讲的是发生在中国上海的故事,但其故事背景设定在外国人创办的圣母院、孤儿院,在对于主人公幼安绘画才能的描写中,也加入了大量中西艺术的介绍。您认为,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该如何有效借鉴融合西方文化资源?
殷健灵:很多年以前,在集中阅读了大量国外儿童文学作品后,我写下过这样一段话:“这些书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异彩纷呈,它们是多么不一样,又是多么丰富和独特。哪怕是相似的题材,依然有各自的视角和全然不同的呈现方式。它们令我惊讶和满足。但在阅读原创作品的时候,我缺少的往往是这种体验。不是说原创作品不好,我们有很多艺术性和故事性都属上乘的作品,但我们选择的题材、表述的方式和视角是不是应该再多样一些?对儿童文学来说,实在是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写,可以挖掘,题材是取之不尽的。我们有那么深厚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那里,那应该是一座富矿。作为创作者,我们需要更多的积累,需要更多的修炼,自然科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哲学的、音乐的,努力让自己厚实一些,视野更宽广一些,才可能写出好作品。”
我平素喜爱欣赏艺术作品,凡是凝结了人类智慧的创造都有兴趣。曾有一段时期,我潜心研究了文艺复兴史、意大利艺术史,还追寻过米开朗基罗的艺术足迹,为他立传……《野芒坡》很自然地融入了我的那部分积累。其实,当初土山湾最打动我的,正是东西方文化在此碰撞与融合后淬炼出的夺目光芒,它打开了一片广袤敞亮的天地,足可以让写作者信马由缰。
记 者:小说中有很多儿童形象,比如主人公幼安,还有若瑟、徐阿小、卓米豆等,这些孩子都是有一定身体或心理缺陷的,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苦难。这样的儿童形象在目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对此您怎么看?
殷健灵:儿童文学里的儿童形象理应异彩纷呈,他们都是“独一个”,是生动的个体。《野芒坡》的描述背景建立在孤儿院,那些生无所靠的孩子几乎个个有着一段“辛酸史”。但相比当年流落街头冻死饿死的流浪儿,他们却是幸运的。而有一些孩子,即便被收容进孤儿院,却依然贪恋自由,谋划出逃。
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认识有着种种约定俗成的偏见。其实,儿童文学和一般的文学又有多大的不同呢?儿童文学里的人物形象也应该是立体的、多样的。在《野芒坡》里,我要写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野芒坡的独特氛围恰恰提供了文学创作特别需要的“复杂性”,在这样的氛围下,不同个性的孩子有着不同反应:若瑟是虔信上帝的,他在这里如鱼得水;菊生是一种麻木的顺应;徐阿小恃强凌弱,让弱者受害;幼安却是独特而敏感的,他渐渐发现了自己与这种氛围的缝隙和距离,试图挣扎和抗争,这也是小说情节的张力所在。
正如维纳斯的断臂、古建筑的残垣,残缺是一种美。而残缺美是一种幻想美、一种弥补美,也提供了心灵重塑的可能。
记 者:在小说第三十八章中,幼安说“感召我的不是上帝的力量,而是……美”。我以为,与其说这部作品是少年幼安等人的心理成长史,不如说是作家自我艺术观、人生观的书写,您认为呢?
殷健灵:写作20多年,我至今不敢夸口说我已经对文学的真谛了然于心。我所能了解的是,不同的优秀作家自成风格,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几十本书,这几十本书可能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很可能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而这几十本书,便是这个作家的“自传”,是他人生观、艺术观的投射,概莫能外。所以说,每个作家都有极大的创造力,而每个作家也都有其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