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奇谭二则
来源:文艺报 | 飞 氘 2016年08月02日10: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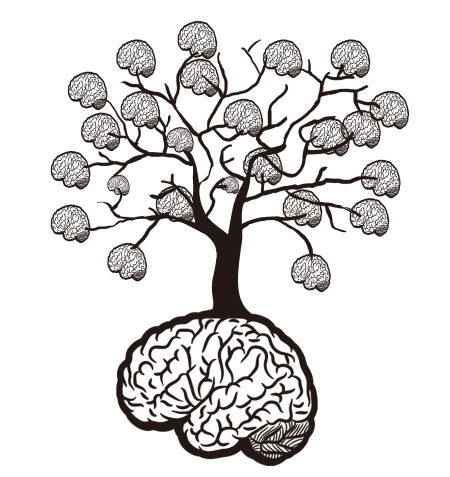
梦瘾患者
“脑连”技术的发明者怀着古老的信条:语言是不得已的蹩脚工具,效率低下,误会重重。通过“时空导引术”,有可能在一些非理性的区域绕开语言的围墙,进行某种直接的纯精神交互。在银河联盟进入“第一繁荣纪”时,惊人的物质富足滋生了颓靡奢逸之风,“造梦潮”便迎风而起。
现实主义的党徒们对此不屑一顾,斥之为高级毒品。确实,有不少“造境师”为了保持创造力而求助于违禁药物,而与瘾君子脑连是否违法也一直存有争议。即便是所谓“自然造境”,也一样有认知失调和“幻境成瘾”的危险,普遍的表现则是意志消沉的厌世情绪。此外,“梦瘾患者”亦普遍存在着对刺激强度的几何指数式需求,最终甚至铤而走险,去造访那些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梦境,最终折戟沉沙于幽怖玄冥的深渊,不能复返,变成行尸走肉。
不过,支持者们则宣称,只要准备充分,脑连技术是很安全的,且利大于弊。毋庸置疑,总有些人天赋异禀,对宇宙的领悟别具一格,脑连有益于智慧的共享——想想看,如果古代的至圣大贤们能直接通过意识而不是退而求其次地借助于语言以及更差劲的文字来传情达意,将会为后人省去多少无益的教派纷争?因此最高级的造境师被称为“引渡人”:在智与爱的海洋上泛舟徜徉,带造访者领略真理荡漾起的粼粼微光。更极端的看法是:万物皆受恩泽,一花一草都会做梦,而人类对此尚知之甚少,未来的终极将是所有梦想的融通。
据研究,即便是最刻板乏味的寡淡之人,也总有想入非非之时,那些无形无界的混沌憧憬,在每一个活过的人心中氤氲蒸腾,沐享其中的灵魂暂时跳脱了时空的绑带,在瞬间的永恒中体认存在之微妙的喜悦——据说,那些敌视脑连的原教旨主义个体崇拜者们道貌岸然的形骸中,正隐匿着最滑稽和油腻的重口味幻想,有一群“脑连黑客”一直在试图通过某种“击穿”技术进入这些清教徒的世界。更不必说那些活泼有趣的人,脑海中浮升过多少华彩庙宇,仅就其辉煌灿烂而言,不输于任何伟大发明,却因时运不济、缺乏训练、肢体倦懒,没有以哪怕最基本的口述或笔录方式化为“现实”,就那样肥皂泡般消逝,这不啻是一笔被浪费的巨大财富。而如今,人们终于有望建设一个广泛的精神共同体,这必将是比形式上的政治联盟更为深刻和有益的、真正的灵魂联盟……
官方的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智慧宝库,试图从万千胜景中寻觅创意乃至理想蓝图,并且不排除推动某种超级人格智慧体的计划。另一方面却又担心脑连会成为反动分子密谋的新平台,更忧虑人类会陷入迷幻的空灵世界,最终被梦榨干膏血,而这与联盟的开拓进取宗旨是相违背的。
确实有人说,宇宙进化出生命,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是为了最终能够做出一场华丽的膨胀大梦。不过,大多数人也没那么多的高级追求,除了基本的新鲜和刺激之外,他们只想寻觅消遣与安慰。随着“脑连”用户的暴增,一种被反对者斥之为“阴暗面暴露癖”的现象蔚然成风。人们将从前那些就连在忏悔室里都不愿说出而情愿烂在心里的秘密公之于众,任由造访者一览无余。尽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道德败坏,但诸多亲历者却信誓旦旦:看见别人的软弱和不堪,便终于明白大家都是凡人,也就更能够接受自己。怀有复古的人道主义信念的医师们证实:这确实大大有益于精神健康呢。
当然了,为了确保安全,有些不愿再面对现实的人——主要是那些“数字信号人”——担负起了“脱梦人”的职责。他们放弃了肉身,永远在一个又一个镜花水月中穿梭,不论是何等大光明都不能心生喜悦,不论何等大悲苦都不能为之怜悯。惟有如此镇定,才能在茫茫黑夜,乘着黑鸟巡视大地,见有掉入噩梦深渊者,便伸手将其拉回此间尘世。但有时,坠入者如飞蛾扑火,面露憨笑,拽着他一起跌向黑渊,他无论如何,只能断其手足,助其一臂之力。“这份工作是不是很刺激很辛苦很危险呢?”面对这样的世俗问题,一位脱梦人淡然地回答:“至少我们不用担心梦醒之后的事,而你们才更不容易。”
星潮防波堤
在可推测宇宙第2F次膨胀期,人类收到了来自银河系核心的神秘信号。新一轮的宗教热忱推动了奔向银心的朝圣之旅。怀着钢铁般的信条,真理探索者们穿过无涯的冰冷长夜,在虔诚和忍耐中寻找着可供居住的行星,沿途播撒文明之花。
殖民星之间过于遥远的距离使得即时通讯再次成为技术难题。星际浪人代表着许多定居者一生无法抵达的世界,因而总是受欢迎的。自称“第一朝圣旅”苗裔的萨玛纳札在“朝圣主干线”上的殖民星间游历,给人讲述他在人迹罕至的危险星域里九死一生的历险。除了口灿若莲、有模有样的“证据”之外,最能为他招徕信徒的是“高维探物”:当他的整只机械左手伸进拳头大小的黑口袋并消失不见,接着掏出人们遗失的童年玩具时,期待神迹的观众们便在怀旧的愁情中对大师顶礼膜拜了。
借助名流的推崇,大师的《论可推测宇宙第2F次膨胀期的跃变原理》在“最优信道”里也广为流传,引发了轰动,被认为“星潮”概念最早的出处。根据这一理论,银心的“暗世界”不光在持续地吞噬物质和能量,而且也会不时地将其消化吸收过的残片和汁液以粒子爆潮的形式释放出来,其辐射范围理论上可以波及整个银河,诱发“全域突变”。由此断定:本轮膨胀期的银河形态是由一系列星潮奠定的,小到火星从文明宜生态向排斥态的过度、地球与之相反的形态演变、智慧生命的出现,大到天穹第八象限的不可接近,乃至引领人类开启朝圣之旅的神秘召唤等等,皆可从中得到解释。
大师预言下一场星潮喷涌在即时,朝圣联盟正在光鲜的外表下酝酿空心化危机,朝圣委员会中激进的原教旨派主张继续向前,最终进入“暗世界”。务实的保守派以发展和巩固现有成就为第一要务,提倡暂缓前进的脚步,直到人类做好以自我祭献的准备。政治角力的结果便是防波堤的修建。尽管大师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实际操作的精确模型,防波堤最后还是作为献礼性工程,赶在纪念人类从地球启航一千世代的隆重庆典之前神奇地完工了。
决策者们宣称,这些距离银心大约1.9万至2万光年不等的触发点,会在星潮的激发下形成一道弧面场,将潮波反射聚焦到前方那些沿着光荣的路线挺进的先锋身上,强化他们浴火重生的程度。而那些对未知变故忐忑不安的人,则可以躲在防波堤身后,抱守他们固有的生活。
在渺小得可怜的银河里,渺小的妙不可言的人类划下了一条看不见的分割线,这是他们所能做过的最劳而无功的事情之一。
“时空曲率的异常突变,已造成了严重的物质分布不均。此乃一切不公不义之根。新一轮的星潮将校正这一大缪。”大师信誓旦旦,“如有必要,甚至连光速也将发生变化。”穷困的人们乐见大洗牌,决意放手一搏,纷纷迁移到聚焦区。即便此生短促,不能亲见改天换地,也要为子孙谋得长出三头六臂咸鱼翻身的机会。
而上流社会沙龙里悄悄流传的意见则认为,防波堤不过是一件超大号的皇帝新衣,是为下等人炮制的华丽安慰剂,是反动分子破坏秩序的可笑借口,如同任何一个古老的末日预言一样不着调。至于官方居然大力推进这一项目,那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联盟内部危机的注意,是挽救经济颓势的黔驴之技、放逐不安定分子的拙计、项目主持者从中渔利的妙招……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在聚焦区置办了居所,有备无患总是对的。
从开始到最后,对防波堤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这些恐怖分子,有的是极端的星潮信奉者,认为创造者的荣光理应平等地眷顾每一个造物,防波堤却阻碍其他存在领享恩惠的机会,体现了狭鄙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的则认定,星潮什么的压根儿就不存在,防波堤却人为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大分化,并阻隔了时空曲率的自然震荡,提高了“维度辐射泄漏”的风险,等等,总之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有些阴谋论者相信,防波堤只是将计就计的幌子,这些如小行星般的银白色触发点,其实是一张监控网。联盟的急速膨胀使它越来越难以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运转,分离主义正在各部落间滋长,因此委员会决定给大家拴上一条牵制链,以便时刻监视各星域的动态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叛乱分子实施精确打击。更有甚者,甚至宣称,联盟早已沦为河外星系文明的傀儡,触发点正在暗中汲取能量,以制造虫洞,为“河外人”攻占打开方便之门,目前的时空曲率异变正是“防波堤”造成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捣乱分子,纯粹是因为失眠症的困扰。在这些面对重大抉择总是优柔寡断反复再三的选择障碍症患者心中,防波堤的存在成为日益严重的焦虑源。最要命的是,没人说得清星潮到底何时到来。失去了必须做出决断的死限,重症病号们陷入了无底限纠结的烦恼中。根据一项非正式的调查,那些在防波堤两侧穿梭不已的星际走私贩中,有相当一部分患有此类不治之症。尽管联盟时紧时松的物能流通管控政策让这些不法之徒大发其财,但当他们迈入一个世界之后,回首望着刚刚离开的另一个天地时,天知道心里那滋味儿是有多难熬。
面对流言蜚语,朝圣委员会不屑于澄清。虽然偶尔会有些恐怖袭击,但朝三暮四的走私贩和上流豪门的涌入还是促进了防波堤两侧星域昙花一现的繁荣,这里一度成为联盟的第三大文明中心。时髦的学者们不断地为大家奉献出有关前一轮星潮存在的新物证,怪招层出不穷的商人们贩炒出类似“突变对赌协议”一类的概念商品——如此虚无缥缈之物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联盟的虚假繁荣到了何等程度,而防波堤亦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维实体造物。
萨玛纳札种种谎言的破产曾让防波堤一度陷入艰难的舆论处境。但官方在发布了通缉令的同时,也公告天下:不能因为骗子而否定防波堤的意义,毕竟已有初步的证据表明,“暗世界”正进入新一轮的活跃期,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大家更应团结一心,切不可破坏先锋探索者们的信心,惟信念与爱永存……直到有一天,走在最前面的“第一朝圣旅”与“零号方尖碑”相遇,引发了新一轮的哲学大繁荣和科技爆发,导致文明中心的前移。加上新型抗纠结震动疗法的发明等等,防波堤的光环终于脱落殆尽。
“大师”逃亡到联盟不愿涉足的荒僻之地后,他的私人星球充公,曾一度被改造成“防波堤博物馆”,供考古爱好者参观。虽然也偶尔会有些过客到那里短暂停留,希望能够发掘到那可以帮人找回遗失之物的神秘黑口袋,但颓势终究无可挽回。不管委员会怎么挖空心思想引导人们来填补这片空虚的星域,来此寻找机会的人们总是遇到种种挫折,最终不得不转身而去。一种说法慢慢流传:此地的“时空曲率”已遭到永久性扭曲,无法再为任何“活性存在簇”提供生机。总之,按照通俗的说法,不少人相信,那些大而无当的银色人造废物,破坏了风水。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剩下少数死硬的星潮崇信者还在那片风光已逝的鬼域里游荡,发展出种种不合时宜的信仰。有的通过“维度导引术”达到灵魂出窍,看见防波堤在五维时空中演化成一幅宇宙棋盘上的棋子,体悟了联盟在忍辱负重中与高维时空的敌手对弈的辛苦。有的则以模拟学高手的出身,在人造时空里再现出了“缩微星潮”,并见证了“微防波堤”将其叠映成莲花状星云,并从中打印出佛陀的全过程。还有的则在防波堤的“聚焦区”进行最危险的“维度递归”酷刑,最终把肉身缩减成了一个粒子黑洞,并在蒸发前发出了祝福:自己已开启了“超限跃迁”通道,瞬间抵达了创造者的怀抱,“所有的都会在一起,不要恐慌”。还有的以“长河穿行客”自居,声称在时空旅行中,终于明白其实整个宇宙本身就是一次“星潮”,而所有对防波堤的解释,实际都是这一根本真相在“维度变换”下的不同呈现而已……
总之,不论你是古典形态人、转基因人、机械强化人、非碳基人乃至纯粹的数字信号人,不管你怀有何等奇怪的想法,都尽可以到这片被废弃的世界,做一个自由的、纯粹的、脱离了人类趣味的人。联盟便顺水推舟,把那里打造成种种非主流实验的自由地。“总要有一个地方让人们胡思乱想,总要有人去替我们正常人做些疯狂或者毫无意义的事。”于是,把思维注入同一具载体以追求世界大同的“人格合并迷恋者”、研修能够导致“现在”崩塌的“历史修正分子”、将银心诋毁为被万劫不复的失乐园的虚无党徒、不顾“维度辐射”危险而意欲进行“维度镂刻”的先锋艺术家……全都在那里聚集、放荡、狂欢,官方派出的观念收集员则定期前往,从海量的垃圾信息中翻检些可能会稍有启发的新思想,尽管,据传说,联盟的首席膨胀学顾问团其实早已经推演出“不可能边界”,算定那些狂妄之举注定不会成功,尽可以由着这些可怜虫们放手去做。
而那一颗颗银色的触发点,不管人们欢喜或愤懑,依旧按照计划默默地运转着、调整着那看不见的弧线。更多的黑色方尖碑发现,让联盟再也无暇想念自己从前的宠儿,有关防波堤的技术迅速遗失了。所以,尽管它们注定要比许多存在都长久,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终究还是和所有事情一样,走向败坏了。
随着河外文明存在证据的接连发现,联盟不得不为可能的星系战争做准备,因此曾考虑将防波堤改造成一道能够进行维度辐射污染的“死亡防线”,但遭到了当地艺术家的激烈抗议,最后不了了之。小道消息称,这一结果和首席顾问团的成员被曝光与“自由地”有不正当交易有关,而备用顾问团借机上位,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死亡防线”毫无意义,倒不如留着防波堤,让河外的“强者”们知道,人类是如此一种会做出许多荒唐之事的文明,请阁下完全无需放在心上。
于是,防波堤最终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装置艺术,继续在那里飘飘荡荡、吊儿郎当。每当《可推测宇宙第2F次膨胀期艺术家手册》重新修订时,编者都要为怎么处理它而头疼不已。
至今,膨胀学家们对“星潮”是否存在尚无定论,一般的看法是:即便真的发生,也不必放在心上。说不定它早已悄然发生了而我们并未察觉,而事实上,就是渺小如我们自己,每一天也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那是一点也不比银河乃至宇宙的兴亡次要的大流转。至于防波堤,公允地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别的且不论,光是它给过人们以期待这一点,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了。毕竟,人生在世,总要有点什么盼头嘛。
飞 氘 “80后”科幻作家。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曾在《科幻世界》《天南》《文艺风赏》等杂志发表科幻、奇幻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纯真及其所编造的》《讲故事的机器人》《中国科幻大片》《去死的漫漫旅途》。作品多次被收入《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集》《中国奇幻小说选》等,并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剧本《去死的漫漫旅途》《巨人传》分别获得广电总局主办的第二届、第三届“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奖。
插图:孟 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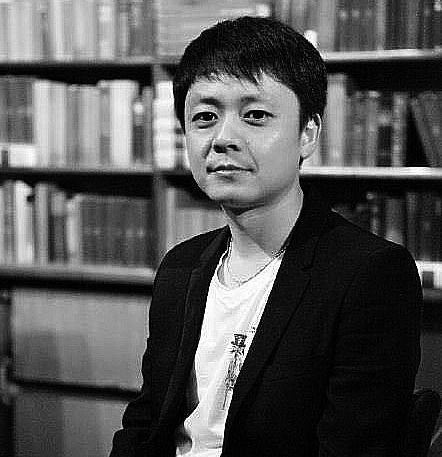
点评:杨庆祥
飞氘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青年作家,并被目为“新生代”科幻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迄今已经出版了《纯真及其所编造的》《讲故事的机器人》《中国科幻大片》《去死的漫漫旅程》等4部作品集。
飞氘的作品充满了奇思妙想,讲故事的机器人、唱歌的机器人、爱吹牛的机器人、永远不死的战士、冷酷专制的国王、从地平线上走来的巨人……安放这些“人物”的,是飞氘设置的无边无际的小说疆域:时空上可以无限延展。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飞氘的小说区别于我们通常认定的主流文学写作,而被贴上“科幻”的标签,虽然从“科技含量”的角度看,他的科幻元素似乎并不是那么突出。
但飞氘最让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组合这些元素的方式,虽然他承认从卡尔维诺和马尔克斯等现代作家那里汲取了更多的营养,但是,我同时也注意到,他喜欢用古老的说书人的方式来开始他的故事之旅,“从前”和“国王”总是联系在一起,而这是一切故事的开端。由此飞氘将它的故事置于一个普遍性之中,飞氘关心普遍性问题甚于关心具体的现实问题,科幻作家刘洋和郝景芳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几乎没有出现在飞氘的小说世界之中,他似乎是一个从现实世界里面跳脱出来的人,坐在高高的星球的上空,抽烟,垂着细长的腿,说,来,给你讲一个过去的故事。
在这些无年代、无历史背景也无现实映射的故事之中,飞氘找到了想象的飞地。这并非说飞氘的想象完全是天马行空,实际上,他的想象亦有其问题的指向,不过这些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类似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比如“死亡”,在《去死的漫漫旅途》中,国王说:你们去死吧。于是以服从为第一定律的不死军队开始了西西弗斯似的求死之旅。这部小说展示了迷人的哲学气息,飞氘以出色的故事方式呈现着“生死”的辩证法,他几乎是以符号化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哲学的反刍。
飞氘这些年的另外一个写作主题是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活灵活现,不过是人类的另外一副躯体,当这些机器人以机器的方式行动时,它并不可爱;但当这些机器人以人的方式行动时——比如当它在两种故事的讲法中犹豫不决的时候——它就变得可爱起来了。机器人由此获得了人性,而这也正是飞氘讲述机器人的目的之所在,它不过是由纯真所编造的人类关于自我的童话,但同时,也是讽喻和劝诫的寓言之书。
《银河奇谭二则》是飞氘近期完成的作品,这是两篇很短的短篇小说,一则写梦,一则写银河星潮,虽然内容遍布各种技术名词,指向的却不过是人类的颠倒梦想。中国的读者或许对此并不会觉得陌生,这两则小说会让我们想起古老的笔记体小说或者中国古代的类书,在那些作品里,神仙鬼怪构成了另外一重“幻觉”的世界。飞氘将这种体式挪用于未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一条通道。
飞氘拥有出色的架构故事的能力,这一点在其他一些科幻作家那里似乎稍有欠缺。这使得他能在一种流畅的叙事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念,但这可能也是飞氘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小说之所以为小说,恰好在于其有大片模糊和暧昧的地带,这些模糊和暧昧之地,需要的是细节、气息、回旋、停顿和滞留,需要有太极拳一般柔密的慢动作甚至是假动作,当然还有那些隐秘的心事,有时候,不说出来也是一种编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