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刘易斯:我心惊悦,为了抵达信仰
来源新京报 | 赵松 2016年12月27日12:36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又称C.S.刘易斯,是英国20世纪著名文学家、学者、杰出的批评家。他毕生研究文学、哲学、神学,尤其对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尤深,堪称英国文学研究的巨擘。

《惊悦》 作者:(英)C.S.刘易斯 译者:丁骏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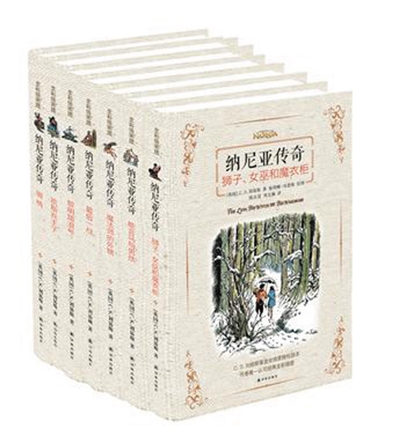
《纳尼亚传奇》(全7册) C.S刘易斯一生的著作包括了诗集、小说、童话、文学批评,代表作当首推七部描写“纳尼亚王国”的系列童话,这是一部儿童游历冒险的系列小说,将神话元素、基督教思想和现代精神融为一体。
20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的巨擘C.S.刘易斯,在55岁这一年写下自传《惊悦》,这是技艺精湛的散文体大师的杰作。无论是叙述的朴素生动,还是描写景物时的诗意,无论是对最初观念萌发轨迹的细致梳理,还是对后来思想演变进程的不断省思,他都处理得耐人寻味,对整体结构的设计也非常讲究,在保持行文的节奏感与紧凑度方面也游刃有余,甚至不时还会让人有读精彩小说时才有的那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阅读快感。我甚至可以直接拿它扉页上那行华兹华斯的诗句来概括我最初的阅读体验:“我心惊悦——如风,迫不及待。”
“喜悦”从来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快乐常常都是可以掌控的。
发现“喜悦” 叙述与反思此起彼伏
在我的印象里,C.S.刘易斯的魅力,一直不如其好友J.R.R.托尔金。主要原因是我读他的书比较多,而托尔金的,只读过《魔戒》。我喜欢刘易斯那冬日暖阳般朴素平和的文风,从他的那些涉及基督教思想的文字里,我也能体会到其信仰之虔诚与纯正。但在同样皈依基督教的托尔金的小说里,我感受到的却是恢宏壮阔而又奇崛的气场,让我想想就会激动。我总是把刘易斯的那些书散放在各处,以便随时翻翻,却把《魔戒》放在抬头可见之处,奉为引发幻想的象征物。
作为不可知论者,我虽然会不时被刘易斯的某些思想观念所触动,却更喜欢与之保持某种距离。或许正因如此,刘易斯的这本名为《惊悦》的自传给我的震撼才会是始料不及的。当我只读了不到一半时,就已开始迫不及待地想着要迅速地读完它然后马上把它再重读一遍了。五十多岁的刘易斯在写这部自传时,是深思熟虑的。此时他的写作技艺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与其说他是在回忆,不如说他变成了隐身人,穿越时空重返过去,与当年的自己一起重新体验成长的历程,梳理出曲折多变的思想路线图。
一路读下来,你会觉得就像是在聆听一部钢琴与大提琴的协奏曲——叙述与反思此起彼伏、交织动荡。他有过短暂而幸福的童年,在酷爱读书的父母影响下他养成了最初的阅读习惯。经历年少丧母之痛后,他跟哥哥陷入与性情急躁的父亲对立的状态,而读书成了他承受生活困境的唯一武器。在书中他发现了最初的“喜悦”——与他哥哥带进育儿室的玩具花园所引发的想象与渴望有关,跟“彼得兔”故事里小松鼠纳特金所诱发的对秋天的迷恋有关,也跟朗费罗的诗《泰格纳挽歌》所带来的“仿佛来自遥远异域的一个声音”的“非同一般的快乐”有关。他写道:“那是一种没有获得满足的欲望,而这欲望本身却比任何欲望的满足都要让人心神往之。我称其为‘喜悦’……在这里有必要同时与‘幸福’和‘快乐’作一个区分……‘喜悦’从来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快乐常常都是可以掌控的。”
“喜悦”消失 黑暗中重现“文艺复兴”
如果说读书构成了他青少年时代那光明的一边,那么学校就是阴暗的一边。在最初的私立小学里他经历的是集中营式粗暴专制的教育,在他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而在随后的英式公学里经历的,则是令他倍感屈辱的环境。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早在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公学里竟然有被称为“血青族”的各级学生“头目”奴役普通学生的现象,甚至还频现“血青族”鸡奸低年级俊秀男生的事情。正如他所批判的:“英国公学体系所制造的东西,恰恰是人们宣称要由它来遏止或者根治的。”在这所位于威尔文镇上的夏朵公学里,除了那些糟糕的体验之外,13岁的刘易斯还经历了一个重要事件:“我不再是基督徒了。”这跟他“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密切相关,它在磨损他的信仰,并发展成为“一种智力而非性情上的悲观主义。”“我那时一点儿也不快乐,”他写道。“反而非常肯定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宇宙基本上是一个不幸的所在。”少年的他,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在“黑暗的中世纪”般的少年时代,他还感受到“喜悦”在生命中的消失,“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甚至连关于它的记忆和欲望都丝毫没有留下。”同时他对于“喜悦”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喜悦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快乐不同,甚至与审美快乐也不是一回事。喜悦必须伴随着那猛烈的一击,一种剧痛,一份无法抚慰的渴望。”
当然,正如他引用的哥尔德斯密斯的那句“再悲惨的处境也有安慰”所意味的,即使在令他身心厌倦之极的黑暗时期,他也有些好的收获,比如北欧神话与瓦格纳音乐就让他获得了属于他的“文艺复兴”,“喜悦”也因此重现了,给生活“注入了一种双重性”。这意味着在黑暗中也有令他激动的东西:“那是怎样浓烈而动人心魄的阳光啊!仅仅是周遭的气味便足以让人忘乎所以——新割的草,洒满露珠的苔藓,香豌豆,秋日的树林,燃烧的木材,泥炭,带咸味的水。感官在痛。我病了,因为渴望;这病却比健康还好。所以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版本就全是谎言。我讲的是一出‘双生记’。”
刘易斯自认平生最幸运的是他总能遇到好老师。即使是在夏朵公学也不例外。但真正对他产生关键影响的,是布克汉姆镇那位“伟大的诺克”,也叫科克,是退休的中学校长,曾是他父亲的老师,“如果这世上有一俱接近纯粹的逻辑实体,那么这个人就是科克。”
这位朴实严谨的教育家“是个无神论者”,还“是个老派、严肃且不带偏见的19世纪类型的‘理性主义者’”,“精通《金枝》和叔本华”,他“最喜欢的箴言是‘花九个便士你就能获得启蒙,而你偏偏宁愿无知’。”在这里,刘易斯接受了最为独特有效的教育。科克先生用直接读《荷马史诗》原文并加以口译的方式教授他古希腊语,科克夫人以同样的方式教会了他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此外,他在这里结识的好友阿瑟还让他理解了“朴实”,这不仅意味着对英国经典作家们的“好看的、实实在在的老书”的再发现,还意味着对于日常事物的重新发现。
超脱“喜悦” 为了诞生真正的信仰
在看译者丁骏的前言时,我还有些奇怪:为什么这本自传只写到刘易斯三十来岁,而不是他的大部分人生?直到读了大半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部“精神自传”。虽然它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其曲折成长经历的回溯与思索,但越是接近最后,尤其是在他进入牛津之后,就越是能感觉得到,前面的一切,不管是痛苦、迷惘还是“喜悦”,不管是最初的放弃基督教信仰、变成无神论者,还是后来重新成为有神论者,都可视为他为自己真正信仰的诞生所做的某种酝酿。
他也坦承,这并不是一个自发自愿的进程,甚至还有极明显的被强迫的特征。一直以来“最希望不被干涉”、要“做自己灵魂的主人”的他,“已经不能再玩弄哲学了”,并看破了之前期待的“喜悦”的本质,“面向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它的对象……是别的东西,是外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自己的某个状态。”
此时此刻,对于他来说,理智与理性都已无济于事。他认为他能做的,就是“彻底的臣服,往黑暗中纵身一跃,这就是我面对的命令。”1929年,他31岁那年的复活节,“我投降了,”他写道。“承认上帝是上帝,我双膝跪地,祈祷;也许,我就是那个晚上全英格兰最沮丧、最不情愿的一个皈依者。”他将这一时刻称为浪子回家。
平心而论,他的整个觉悟皈依的过程,确实是个极具震撼力的阅读体验。尤其是当前面那些关于成长经历的生动描述所带来的直观震撼力与最后阶段信仰觉醒与皈依所带来的复杂震撼力合而为一的时候,我在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了冥冥之中某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他转变的作用。
由此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这部精神自传写到信仰确立为止了。因为在他看来,拥有信仰之后,他的人生有了全新开端,完全超越了此前整个“自我”,而在信仰中的生活,已根本无需再通过文字呈现了。当然,你可以不像他那样去觉悟,但你无法不被他的觉悟过程所触动。至少,他让你明白一个根本道理,正如他在最后一章引用的奥古斯丁的话所言:“凭栏远眺平安之地,是一回事……长途跋涉走向那里,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