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瑞典大诗人的中国想象 ——从埃凯洛夫眼中的林语堂小说谈开去
来源:文艺报 | 2017年07月10日06:47

埃凯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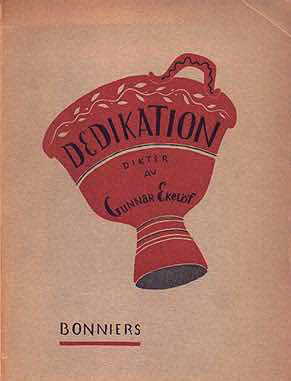
埃凯洛夫诗集《献词》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瑞典文版
“平滑的林语堂”
1954年,瑞典数一数二的出版社伯尼尔斯出版了瑞典翻译家卡尔· 松代尔由英文译出的林语堂小说《朱门》,瑞典文版书名为《血红的门:来自那遥远国度的浪漫故事》。同年8月27日, 瑞典《每日新闻》刊登了瑞典经典雅文化代表、作家和诗人贡纳尔·埃凯洛夫的书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
作为一个使中国的生活智慧得到普及的作家,林语堂赢得了世界声誉;他的成功与其小心迎合了美国及美国化了的欧洲中产阶级读者对东方世界的要求有关,那浪漫的想像须是古怪的、装饰性的、可读的,同时又充满神秘性。这其实和18世纪的中国热一模一样:带着一丝无害的势利的现实逃避。就像是你可以有个中国雕像在柜子上,目光于是逗留于此,记忆中得以有个微妙之处,偶尔让想法与之来一番戏耍。带着确定的直觉和轻松的手法,林语堂以这种模糊的浪漫笔触向他的广大读者诉求;可要是他抓住了许多人,他就可能激发出几个有进一步深入其中的兴趣的人来。因此,这些人在深入后对林语堂表露出轻蔑实在有些不公,虽说林语堂并不是一位更深刻的天才。
林语堂作为一个作家的弱点在其试图成为小说家时更为明显。他说不上是擅长刻画人物的那一个,也并非描摹环境的好手。甚至在这部作品中,他的目的也主要表现为说教。他想给西方人一个体面的图景:传统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儒家的美德典范又是怎样的——甚至在其与西方有了接触,开始被修改和现代化之后。似乎林语堂最想向体面的美国中产阶级——那些常常适度地去教堂,并依然遵守道德和公约的“某些规范”的人们展示:中国人和他们实在是非常相像。
他的新小说《朱门》描绘了一出有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描绘了在中国国内政治腐朽而对外政策窘困的1933年,一名记者和一位富家女之间发生的一切。为在故事中加入更多生活和浪漫,林语堂让记者一度被战争的混乱吞噬,让富家女未婚便生下孩子,被她的叔父逐出家门,陷入“孤单”,惟有英雄的仁慈友人陪伴左右。作家特别是通过描述被稀释了的悲惨的田园牧歌的背景,透露了他对传统主义的挽救。因为,很显然,他不能不提及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腐败以及贫穷、饥馑等所有的恐怖——这些恐怖被原始的信仰战争在其经过的每一条路上抛于身后。相似的主题,比如革命时期的俄罗斯人是被处理成了一种让人震撼的方式,在林语堂这里,却有好莱坞现实主义风的抽象、遥远、半失真的光芒。概括地说,你甚至没法相信这种平滑、当然也很有可能的爱的情节发展在这出戏的最前沿。
短评题为“平滑的林语堂”。“林语堂”之前的定语是多义词,除“平滑”外,有扁平、无趣之意,埃凯洛夫的表态既不动声色更立场鲜明。
《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三部小说成就了林语堂的战争三部曲。终曲《朱门》有家族的兴衰史,有战火中的颠沛流离,主线是上海《新公报》驻西安记者李飞及大家闺秀杜柔安的爱的传奇,呈现了古城西安在历史过渡时期的社会画面。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1940年由美国作家赛珍珠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同时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赛珍珠更在1950年再做举荐。惜林语堂无缘诺奖。1950年的埃凯洛夫还只是一位著名诗人,不过他在1958年成为瑞典学院院士,直到1968年辞世,坐学院的第18号椅。林语堂两度被提名时,埃凯洛夫自然不能发表意见、影响评选,不过他的观点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瑞典学院的标准和审美。
早在1948年,埃凯洛夫就发表过对林语堂作品的看法。这一年,埃凯洛夫评点了刚由瑞典北方出版社推出的黄祖瑜的《开花的石榴树》。这本从黄氏远祖写起的回忆录是作者用英文写出,请友人译成瑞典文的;它的中文扩写本至2001年方由河南海燕出版社推出。黄祖瑜1912年秋生于河南信阳的家族老宅。一度由工程师父亲接到京城,再因父亲职业变动跟回河南。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算学系,于1937年自费留学英国伦敦大学。1939年,学习即将结束时,他因为看了一部瑞典风光片而对瑞典的自然生出向往,适逢免费去瑞典参加一场国际学生活动,就在8月坐船抵达瑞典哥德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他成了滞留瑞典的难民。作为第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又住在瑞典的中国人,他曾给不少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瑞典人提供协助,一方面是糊口需要,另一方面,瑞典人也看重中国文人的力量。他曾帮喜龙仁阅读中文、打理家务;帮助高本汉整理《字书》 索引。他还曾从事大量演讲和写作活动,宣传抗日和中国文化。《开花的石榴树》出版时,他在当时的中国大使馆谋得一份差事。埃凯洛夫的书评刊于《伯尔尼文学杂志》。其中有一段:
就是说,队列式的安排会显得干巴巴的,显得一般,但这也让作家带出了丰富的事实,做出了清晰的呈现。特别是,虽然作家并未投入多少笔墨烘托氛围,读者还是可以得到关于中国农村和村庄生活的出色图景。那个从浮夸的美式书写,也许特别是新闻式书写中学得有些过多的林语堂可以是个比较。黄祖瑜没有迎合他的西方读者对“罗曼史”和“渲染氛围”的要求,而更可能的是,那种对长辈的尊重和对真实的尊重有些一致。但奇怪的是,其实一直存在着氛围,它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用汇入的细节逐步构建的, 是那些留存在记忆中的东西砌成了一排麻将。这归功于作者是个艺术家,一个严谨的学校的艺术家:冷静、惜墨如金、一心只选择诗意的内容。
这里,埃凯洛夫给林语堂贴上一个“美国式书写”的标签,更把林语堂和黄祖瑜对中国的书写相对照。黄祖瑜的书写绝非无懈可击,然而植根在记忆中的东西往往弥足珍贵。在一面是迎合与装饰,一面是细致与洗练;一面是好莱坞式的烟幕、布景,一面是土生土长的真情、实景间,埃凯洛夫选择了后者。平心而论,埃凯洛夫的评点并非文人相轻式的嫉妒,也非门外汉的浅薄之谈。虽说中国距瑞典十分遥远,但埃凯洛夫对中国文学确有独到的体会。
埃凯洛夫的中国想象
1930年代末,欧洲又一次掀起对古老中国和其道家哲学的兴趣。不少唐诗译本面世。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译本《吾土吾民》)正是在1937年由伯尔尼斯出版社推出瑞文版,书名为《一个中国人谈中国》。该社于1940年又推出林语堂的全球畅销书“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译本《生活的艺术》)的瑞典文版,书名为《享受生活的艺术》。
曾有不少瑞典作家研读中国诗文并从中获得灵感,埃凯洛夫也是其中一个。在埃凯洛夫及不少处于战争风云下的欧洲知识分子看来,老子、庄子这两个几乎和苏格拉底、柏拉图同时代的道家哲人似乎指引着一条令人向往、通往和谐的路。道可在自然中寻找与接近,道静止而无名,有深刻的、不能轻易懂得的内涵——这一切让他们着迷。埃凯洛夫在1930年之前就修读过有关中国哲学和诗歌的课程,1930年代末更阅读了《道德经》。1938至1939年间,他所创作的诗歌明显带有中国痕迹:“是那么优美她们在一起/那黝黑的着红/那淡白的着绿——/叫求爱者怎好选择?/假如她们没像姊妹般坐在一起/黑的看来无聊/白的显得单调/像天和地所呈现的,/如果失去彼此”。
1941年出版的埃凯洛夫诗集《渡船之歌》中收录了题为《宋》的一首诗,“宋”指中国历史上的“宋朝”:“今夜充满星光/空气洁净清凉/月亮试图和一切同在/那些它丢失的遗产//一扇窗,一条开花的枝干/那就足够/没有花开无泥土/没有泥土无空间/没有空间无花开”。
早在1927至1928年间,埃凯洛夫的笔下就出现过“今夜充满星光,空气洁净清凉”的句子及月光挥洒的意象。经过唐诗和老庄哲学的熏陶,他的句子生长了、成熟了。静夜、月色、窗棂、开花的枝干,完全是一轴宋元文人画;诗歌末尾三句的辩证统一不消说充满老庄意味。埃凯洛夫笔下还流淌过其他深受中国文化启发的诗句,如在1955年出版的诗集《一派胡言》中有一首题为《中国刺绣》:“一只火鸟的巢是心脏/用血管的枝条构筑/用火焰来封闭。可那鸟儿/栖在更高的/温度里。从胸脯到侧腹/火焰好似都碰它不着。一动不动地/它孵在看不见的蛋上/翅膀扑闪,尾羽/沿巢边挂下。羽翅偶尔鼓动,似要捕捉/思想和图景的昆虫/振翅时它便立刻消失在空气的丝绸里/重被看见/当它再度栖息/于火焰里,用喙梳理着自己的毛羽”。
中国刺绣中的火鸟该是凤凰。凤凰和其他文化中的不少火鸟一样,有不死或在烈火中重生的传说。鸟巢如心脏指示外形;而心脏是供血中枢,心脏有搏动,血是火红的。“丝绸的空气”是个特别的比喻,形容既包裹得熨贴又轻盈无压力的质感。特立独行的鸟在火焰上稳坐又不为火焰所伤,真是令人赞叹的姿态。
学习过波斯语、设想过印度之旅、一直向往东方的埃凯洛夫对中国也有自己的想象。在埃凯洛夫心中存在着对“中国式”的某种可意会而难言传的定义。日常中的温馨一刻,他会称之为“中国时刻”。在给情人玛依的信中有这么几笔:“我刚出去从信箱里取出你的信,却没打开。现在它躺在茶杯旁,早晨的茶水刚沏上。我把信省下来,省到这小小的中国时刻里。”在1937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诗人写到:“我刚出去了一会儿,太阳刚升到一半,山上有灰色的长长的雾的轻纱。如果这风景更垂直,就会像一幅中国画。” 1939年给友人的信中,埃凯洛夫说: “要是过于干净就不好。好的是自我的生长和运动。” 埃凯洛夫甚至写过这样的诗句:“她在每一个眨眼间死去,所以她活着/她在每一个眨眼间飞去,所以她留着/她接受威力和反威力,所以她摇摆/她摇摆,所以她在平衡之中。”
据《中文瑞译目录》披露,1937年,埃凯洛夫从法文转译李白诗一首,题为“关于秋天”;1939年,又从法文转译李白诗一首,题为“少年“。然而,另有资料提示,埃凯洛夫说过,“关于秋天”一诗参考了翟理斯和克莱默·宾的英译本,“少年”是从俞第德(朱迪特·戈蒂埃)的法文译本转译。从埃凯洛夫的译文不难看出,“少年”其实是《少年行》,“关于秋天”到底是哪首作品呢?仔细甄别才能看出是《悲清秋赋》。
埃凯洛夫译本的字词排列确实高度接近克莱默·宾的译本。他读的李白不能说是假李白,字词说不上有多少谬误、添加或遗漏,却仿佛弹簧变了形,曲幽与凝练被拉成了平铺直叙。仅以“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千”为例,英文为:“I am now in the foreign regions of Tsin and U; and countless are the miles of the trackless way, brushed by the wings of birds alone, lying between me and my native land.”变形并不能阻止埃凯洛夫对李白的激赏。他认为李白是中国山水画大师,是激情的自然浪漫主义者和悲观的梦想家,应在瑞典人中找到知音——因为瑞典人无论是国民气质还是后来出现的瑞典诗人,都说得上是李白在后世的亲戚。埃凯洛夫和李白“攀亲”叫人莞尔,李白的情形无须多言,而自然浪漫主义和悲观的梦想确实是瑞典人、特别是瑞典诗人的主要气质。
埃凯洛夫还翻译了《诗经》中的 《汉广》《将仲子》《绸缪》,他热情洋溢地赞颂《诗经》:
假如借福楼丁的定义来说,诗歌是用一种可贡献于读者之共鸣的语言来表达温暖和深切的情感,换言之,它诠释的是最人性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宇宙论、宗教和教条理论的空洞复制。于是,中国的《诗经》可能是世上最古老的诗歌记录。它包含有名有姓及佚名作者的作品,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和那些回荡着民歌音色的佚名诗歌挨得特别近。
读这些诗歌,不仅会觉得世界很小,还会觉得时间很短。穿过三千年的黑暗,它们触碰到日常生活中的关切,和我们自己从中世纪到虔诚的18世纪的民歌传统一样。两种情形下都有一种对照,不同的季节,穷苦劳动者单调的生活和对远处的幸福的梦想,这些都给诗歌添加了沉郁。但还要注意到,中国的民歌有着对无尽的平原、河川和时间的反思。
埃凯洛夫翻译中文诗文的主要资源是中国留法学者徐仲年(Sung-Nien Hsu)1933年的法文版《中国诗文选》)。这部书被看作早期留法学人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中,门类最齐全、选本时间跨度最大、篇幅最长、篇目最多的一部,从《诗经》一直介绍到鲁迅。于是,瑞典读者也有幸读到埃凯洛夫翻译的王昌龄、韦应物、王士慎、赵翼等的诗作,甚至徐志摩的诗及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值得一提的是,埃凯洛夫对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情有独钟,译有全篇。
此外,埃凯洛夫在1948年对瑞典文版《琵琶记》发表过书评。元代戏剧家高明的《琵琶记》改编成英文的《琵琶歌》于1946年在百老汇公演。这个美国版剧本在1948年由瑞典北方出版社推出埃瑞克·布罗姆贝里的译本。埃凯洛夫认为剧本展示的问题,在当时的瑞典也有,没有牺牲就没有社会,这是无法摆脱的恶。而擅长诗歌艺术的中国人既能描写近处的残酷,也能刻画远处梦一般的蓝色,比契科夫早了很多年。
第二年,吴承恩《西游记》最早的瑞典文译本面世(据亚瑟· 伟利的版本翻译)。埃凯洛夫也写下好评。他尤其喜欢对孙悟空成为唐僧徒弟之前自在生活的描绘,认为每一页都让人忍俊不禁,是自然和模仿、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交织和转换,变幻无穷,永远不知下一个到来的会是什么。
可惜埃凯洛夫终究觉得转译捉襟见肘,由此对译介中国诗文慢慢消减了兴致。他其实没必要对自己的转译作品自惭形秽。到了1940年代,在瑞典,除了高本汉等少数汉学家可直接通读和译介汉语外,其他如埃瑞克·布罗姆贝里、约翰内斯·埃德费尔特等都是从英、法、德等文字转译了大量中国作品。即便是转译文本,也都促进了瑞典汉学的发展。有一点无法否认,埃凯洛夫是中国诗文的知音,更是将中国诗文译介到瑞典的先行者之一。
有庄子的《道德经》,有徐仲年的《中国诗文选》,有多种法文、英文和瑞文版的中国诗文垫底,埃凯洛夫对林语堂的把握就不是盲人摸象。埃凯洛夫一闻就嗅出和李白的亲缘性,一听便认出《诗经》中的音色和“我们的”挨得很近。这嗅出的和认出的,也许不可名,就像道;也许可名,就像人性。“世界很小”,“时间很短”,好莱坞式的举手投足总和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脱节——恐怕这就是埃凯洛夫不很欣赏林语堂的根本原因。而用犀利目光鉴赏过中国诗文的大师埃凯洛夫若能直接阅读中文,与中国思想和文学直接交流,他的作品又会放射出怎样的光芒,真是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