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作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他在井里打捞回忆
来源:文艺报 | 刘可欣 2017年07月21日06:45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

《盆栽》西班牙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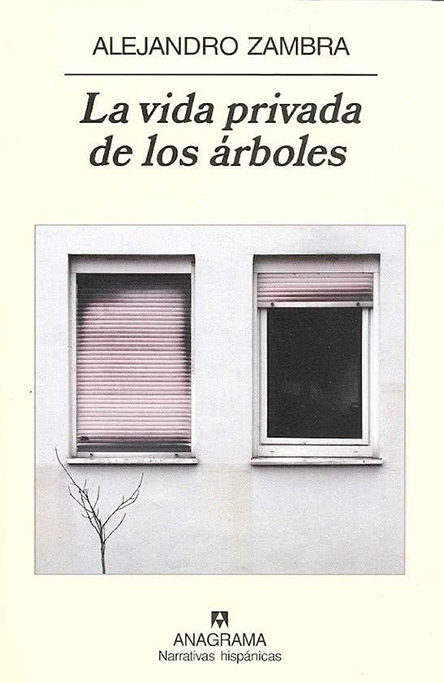
《树的隐秘生活》西班牙文版

《回家的路》西班牙文版

《我的文档》西班牙文版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是个烟鬼。这位智利作家在2013年出版的《我的文档》一书中花费了很多笔墨写了一篇有关戒烟的故事,取名为《合格烟民》。这部短篇里应该包含了他所能想起的所有关于吸烟的诗句、歌词、小说、冷笑话,小说中的“我”东拉西扯、颠三倒四,就好像契诃夫笔下那个被老婆逼迫而不得已进行“论烟草有害”演讲的倒霉蛋。作家桑布拉本人也正如故事中所写的那样为偏头痛和烟瘾所折磨。而就在《我的文档》出版仅仅数月之后,一名智利《诊所》杂志的记者在采访稿中宣告桑布拉戒烟失败——“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像过去那样,每天三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每隔半个小时就要点上一支烟”。
桑布拉是一位非常坦诚的作家,他喜欢写和自己有关的故事,尤其擅长自主虚构的后现代叙事。不同于传统的自传,在他的小说中,现实与虚构、记忆与想象、主观与客观,总是同时出现,拉伸拓展、盘结交错、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的边界都被涂抹得模糊不清。
在短篇小说《我的文档》中,桑布拉几乎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放风筝时第一次抽烟,皮诺切特遇袭、1988年进入国立中学,民主时期的到来、1994年开始在智利大学学习文学专业,毕业后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和在写作上对家人的排斥,妈妈的打字机和保罗·西蒙的海报……在之后的《长途电话》和《国立中学》里,他还分别将自己的接线员和中学经历扩展成一个新的故事,虚构了一个并不喜欢读书却花钱请人教授自己文学的老头和一个预测所有人都通过考试却惟独自己留了级的学生的故事。
在桑布拉的小说中,读者常常能看到雷蒙德·卡佛的影子。文学评论家华金·阿尔纳伊斯曾在玻利维亚《真理报》上发表评论:“桑布拉的小说语言受到了卡佛的影响:同样精准、忧郁、残酷、又轻柔。”这两位作家起先都从事与写作无关的底层工作,桑布拉是夜班接线员,卡佛是卡车司机。他们都喜欢进行冷静的描写,简洁到位,不拖泥带水,不做过多修饰,像一台摄像机冷峻地记录着发生的一切。甚至在桑布拉的短篇集《我的文档》中有一篇名为《家庭生活》的小说,讲述一位男子帮助一对夫妻看家并由此开始了一场充满谎言的恋爱的故事,它开头的情节与卡佛《请你安静些,好吗?》一书中收录的《邻居》如出一辙。在卡佛的极简主义小说里,无论怎样的虚构都有现实的影子,他自己也曾表示对小说写作而言“一点点自传性和大量的想象是最好的方法”。这样的写作理论在桑布拉这里也同样适用,只不过真实与虚构的配比可能有些许不同。桑布拉笔下的一代是全球化后的一代,与卡佛笔下的美国居民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一切都令读者似曾相识:书中的人物沉迷于科技和电脑,男男女女们上网冲浪,用电子邮件交流,依赖Facebook和色情电影网站,急于知道每个地方的WiFi密码。
对于这一代的拉美中青年作家而言,他们对拉美文学的继承更多地来源于罗贝托·波拉尼奥——这位生长在墨西哥、死于西班牙的智利作家,经历了屠杀、政变、暴力、独裁、国家恐怖与政治流亡,作为所有可以形容的和无法形容的历史性时刻的亲历者,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作家让世界读者彻底完成了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别,开启了拉美文学全球化和后现代化的新纪元。
波拉尼奥之后的这批作家通常被称为“子辈一代”,代表群体有:2007年在哥伦比亚举行的HAY文学艺术节中评选出的波哥大39社团,以及2010年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评出的22位35岁以下的杰出西班牙语作家。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本身并非是残酷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却在政变、战争、独裁和暴行尚未消散的阴霾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除了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这一代的代表作家还有:从小与流亡者一起生活的墨西哥女作家瓜达卢佩·内特尔(Guadalupe Nettel),死于白血病的妓女的儿子朱利安·赫伯特(Julián Herbert),阿根廷左翼军人的后代帕特里西奥·普罗(Patricio Pron)等等。这些拉美文学爆炸第三代作家有着共同的特点:在他们的作品中,对“我”的探讨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私密的个人记忆替代了国家层面的身份认知,无关意识形态的政治思考,对于历史的微观化、片段化、个人化叙述,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充分关照。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是同代作家中走得最远的那一个,他的第一部小说《盆栽》就轰动文坛,获得了当年的文学评论家奖最佳小说奖和国会图书大奖,被称为“智利文坛的一次放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要知道上次有文学评论家说出这么严重的话,还是对举世瞩目的波拉尼奥。截至目前,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1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去年,他还应邀参加了上海书展,宣传他三部作品的中译本。
桑布拉小说中的内容常常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在他的主要出版作品——圣地亚哥中产阶级生活小说三部曲《盆栽》(2006)、《树的隐秘生活》(2007)、《回家的路》(2011)以及一本短篇故事集《我的文档》(2013)之中,读者都能找到作家本人的影子。
如同这一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桑布拉的童年在独裁的阴影中度过。1975年,他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而后举家搬迁到距首都10公里的迈普小镇。在他出生前两年,皮诺切特发动了轰动世界的军事政变,而后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军事独裁,国家机器疯狂运转——严格管控意识形态,审查新闻媒体,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制造国家恐怖,实行高压政策,无数的人被暗杀、被折磨、被失踪。在桑布拉的小说《回家的路》中,懵懂的少年把这位军事独裁首脑形容为“皮诺切特大嘴王”,那时候他讨厌他,不过是因为“他的节目播出时间随心所欲”、“总是打断精彩节目”。孩童时期的他无法理解,那个他吃过几只冰激凌的体育馆看台,曾经是1973年那场波及无数人的政治风暴的中心。在这部小说里,“历史中的缺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儿童时期的桑布拉错过了国家最苦痛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他也曾在采访中承认,这让他有了某种“缺失感”、一种被排除在时代认知之外的被遗弃感。
他曾经认为小说是描写父辈的:“他们似乎注定难逃厄运,一无所知的我们则被庇护于阴云之下。成人们互相残杀时,我们躲在角落里涂涂画画。这个国家土崩瓦解时,我们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叠着纸轮船和纸飞机。最后,当小说成为事实,我们却玩起了捉迷藏,消失不见。”(《回家的路》)
在记者帕特里西奥·费尔南德斯的采访中,桑布拉曾表示,《回家的路》是一本向他的童年还债的书:“过去很长时间里,我认为我的经历无足轻重。那时候最重要的是揭露罪行,让那些备受折磨的受害者发声。怎么也轮不到我们这些生活在郊区,出身于不问政治的中产家庭的小孩。在我成长的迈普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我经历的那些就显得没什么必要去记述了。但是我逐渐认识到,我所感受到的这种疼痛是一种集体的体验。事情已经过去10多年了,这已经不仅仅有关受害者,绝大多数的智利人都被牵扯进来。所以即便还有很多罪行没有暴露,还有凶手逍遥法外,但至少绝大多数的智利人已经认识到了这种集体性的创伤。”
在皮诺切特统治时期,一群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留美经济学家大行其道,他们师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诺德·哈柏格,并在回国后将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直接运用于智利——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压榨工人福利,放任恶性竞争,致使失业率骤增,整个国家沦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在以此为代价的繁荣里,新的中产阶级逐步形成,他们大多缄默不言以明哲保身。就像《回家的路》中的那位父亲,他“从小就懂得没人能拯救他们”,他承认皮诺切特是一个独裁者,但他选择置身事外,因为“至少那是个有秩序的年代”。
桑布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有着幸福完整却在长大后不甘愿承受的童年——“试图理清童年时我们无法理解的一切,仿佛在围观一场罪行。我们不是罪犯,只是恰好路过又抽身而去。因为我们深知,如果置身其中,就会被泼上污水。”(引自《回家的路》)桑布拉这一代,作为父母的子女、历史的配角,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他们无法站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位置上去评判父母,另一方面又无法苟同父母在独裁时期的所作所为;一方面他们可能感到庆幸、庆幸自己并不处于那样一个需要被后代审视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得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斥责上一代“置身事外就是支持独裁”。
1988年,桑布拉进入国立中学。在短篇《国立中学》中,作家详尽介绍了这所智利最有声望的公立学校和独裁时期的中学教育,这所学校培养了几名智利总统,却在提起他们的时候,“总是略过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在这里,智利的民主时期同桑布拉的青春期一同降临。但正如《我的文档》中所说的那样:“青春期是真的,但是民主是假的。”一样的独裁和一样的皮诺切特,这是高喊胜利的智利,即刻到来的民主和充满恐惧的领导人,愤怒而无所事事的青年成天听着Radiohead,人们在被问及对经济制度的看法时,被迫露出虚假的断断续续的笑容。
这是一段无法再感知的经验,皮诺切特军政权逐渐稳固下来,整个国家走向一种畸态的繁荣,开始再度形成中产阶级群体,然后理所应当地开始下一个民主时代。独裁者以各种理由和无赖嘴脸胁迫一个法治社会,各方角斗、权力斡旋,最终竟寿终正寝。对于智利的流亡者和受害者而言,新时代的开始恰恰意味着一个永远无法翻案的人生,一段无法被真正审判的历史,那些细碎的瞬间无处告解,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要么选择遗忘,要么选择成为历史书上一个群体性的悲愤的表情,他们甚至渐渐变得卑微、荒谬、可笑,成为在欧洲兜售政治伤痛的一群流亡商人。如果说这些在波拉尼奥那里表现为一种“历史与现代性承诺的坍塌”,在桑布拉这里则表现为“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坍塌卷起的尘埃飘进每一户人家紧闭的房门。
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中,而非历史中,如果有人把记录大事件的历史书逐行放大,就能看到黑压压的人群里每个人脸上茫然无措的表情。过去的动荡和流血留给孩子们的就好像1985年的那场智利大地震,他们对大地失去了信任,但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由此懂得了“一切都可能在瞬间轰然倒塌”,但是生活还在继续。在普通人那里,历史像被隔住了磨砂玻璃,一切都没那么清晰,正如智利诗人、批评家费德里科·施普夫所说:“我们在麻木中生长,我们已无法感知世界。我们是一棵又一棵被抑制生长的树。”在《回家的路》中,第一次远离家乡的主人公意识到:“人们空怀一腔热忱,在狭窄的道路上埋头前进,仿佛惟一能做的,只有被迫隐姓埋名,一路向前。”
费德里科·施普夫的话还有后半句:“我们想要醒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昏睡。文学会叫醒我们。”无论如何,现在轮到他们了,这些在80年代还处于变声期的孩子们,现在轮到他们来书写这些属于配角的个人记忆。就像《回家的路》中所说的那样,“为了填补空白”,为了回答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是谁、他们还能是谁、以及他们本该是谁。这些不是历史的假设或者自身的开脱,这是对过去的重建、对缺失的填补,为了让过去的没那么轻易过去,为了照亮一些记忆的角落,为了“穿着父辈的衣服,认认真真打量一下镜中的自己”。
桑布拉几乎在所有的小说中都设定出一个特定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叙述者提及的具体的年份、与皮诺切特有关的历史事件、传声头像乐队某张专辑的发行时间、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和2006年的科洛科洛足球队(桑布拉本人是该球队的忠实粉丝)。如同《回家的路》那样,《我的文档》中,桑布拉也试图将成长在民主过渡时期的智利人的共同意识和集体回忆形象化,他要重塑一个次要角色的世界。正如他欣赏的卡佛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主义”的小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无足轻重,但是值得叙述。
这个过程并非是苦涩的。桑布拉本人是一个有趣的作家,他在迭戈·波特尔斯大学教授文学课时也经常跟学生们开玩笑。这样的态度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元小说的写作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十分常见,作者不断地出现,走到读者面前:要么像《盆栽》里那样,在小说开头就恶作剧似的告诉读者结局是女主角死了;要么像《树的隐秘生活》里那样,抱怨一本小说的创作过程有多么艰难;要么像短篇小说《追忆》里那样,角色像一道道食材那样被作者摆布,然后在读者面前毫无保留地展现所有的烹饪过程;再要么像《回家的路》里那样,写出两个平行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里的作家写着另一个故事里的作家的故事……自我反省、自我意识与自我指涉,使桑布拉在读者面前游刃有余地进行着他的文字游戏,他不仅进行有关真实和历史的思考,也同时进行着对文学的思考,他亲手刺破写作的边界,让真实与虚构,读者与作者,在文字中相遇,丰富并拓展了记忆与文学的可能性。
在《回家的路》的开篇,桑布拉引用了法国小说家罗曼·加里的一句话:“我没有呐喊,而是写作。”这个从小就对母亲的打字机着了迷的小男孩,从没为他的写作编纂出什么惊人的理由。当他的前辈在海难过后的海面上划着小船打捞一具具尸体时,他只是站在一口水井边帮已经忘了或者再没回来的人打捞起一小段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