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逝世一周年:感受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
来源:澎湃新闻 | Dzolan 2018年01月03日14:36

约翰·伯格 资料图
留住一切亲爱的。
这是伯格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的书名,它取自加雷斯·埃文斯献给伯格的一首诗,诗的题目正是《留住一切亲爱的》,这首诗的最后几行是这样写得:
词语
面包
探寻着门外真理的孩子
一切重新开始的渴望
动物机敏,在世界议会里
屋里的人,街上的人,这许多人
留住一切亲爱的
要如何理解词语和面包?它们一个象征着语言和行动的自由,另一个代表着基本的物质需求,对于伯格笔下的部分群体而言,两者都是奢望。在《留住一切亲爱的》——这本不足两百页的散文集里,伯格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失去“词语”和“面包”的人的故事。加雷斯·埃文斯,这位不知名的诗人或许就是伯格笔下的人物之一,一位生长在巴勒斯坦或者阿富汗的普通民众,还是某场解放运动的领袖,我们无从得知。
巴勒斯坦,伯格集伤痛与愤怒的目光所望之处。相比他可以在1962年选择离开英国,用双脚做出自己在政治理念上的选择,他却无法在地理意义上永远长存于巴勒斯坦,唯有在精神上,对这块土地进行长久地思付。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只有一个词的含义未曾消减:Nakbah,灾难日。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7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乡流亡,这一天被巴勒斯坦人称作民族的灾难日。在2005年写就的那篇《不败的绝望》中,伯格将这个国家概括为“瓦砾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巴勒斯坦的面貌被归属于,道路和房屋的残骸。每一个巴勒斯坦家庭都曾被迫逃亡,就像每一个巴勒斯坦城镇都曾被占领军一次又一次地铲平。
瓦砾还表现为“语言的瓦砾”。当联合国和海牙国际法庭裁定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以色列居民和八米高的隔离墙属于违法建筑的时候,这些建筑依旧在被修建。所有义正辞严的外交辞令和官方对话都成为了瓦砾,它们的存在就像是那些实实在在散落在巴勒斯坦土地之上的瓦砾,除了进行讽刺般的见证外,毫无用处。这是身为行动主义者的伯格所无法容忍的。
“对我们而言,”一位巴勒斯坦母亲说,检查站里她的身后正跟着一名抱着催泪瓦斯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她朝装甲车点了点头,“西方的沉默比他们的枪弹更为恶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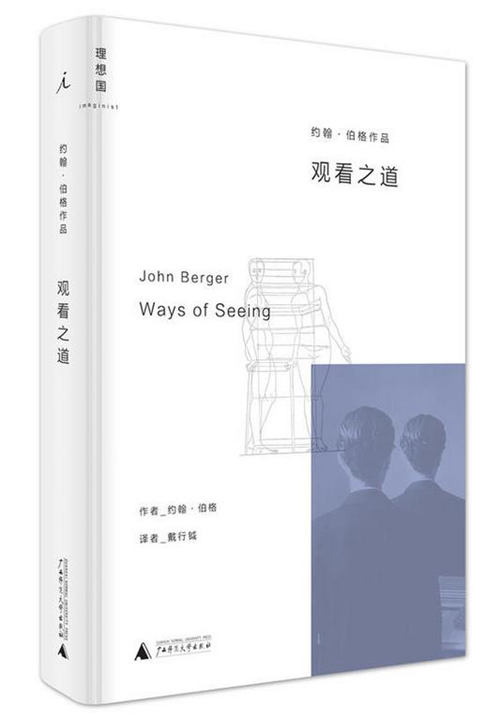
那么,《不败的绝望》中,“不败”在哪里?《石头》一文中,伯格缅怀了自己的朋友埃格巴尔·艾哈迈德,一位投身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革命者,伯格称之为“见过生活全部面目的人”。在伯格探访拉马拉——巴基斯坦民族权利的首府时,埃格巴尔的照片“主动”找到了他。他们一同看到了,市镇中心周围一道道贴满死者照片的墙壁,其中包括那些决定舍弃生命反击以色列的人。
伯格没有告诉我们埃格巴尔是如何死去的。他提到自己写过一篇关于埃格巴尔在印巴分治时期的经历,埃格巴尔曾在阿姆斯特丹的一间酒吧里告诉了他这些故事。伯格写了下来,埃格巴尔读完之后,恳请伯格改掉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他已亡故,我将他的名字归还给他。
埃格巴尔,遗留在墙壁上的牺牲者们,他们被伯格留在了自我对记忆和思考的温柔训诫里。他们共同归属于“探寻着门外真理的孩子”。那么,失去伯格的这一年,我们又要如何留住他?
2017年1月2日,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画家,被誉为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真正传人的约翰·伯格在法国安东尼去世。
伯格最开始为人熟知,源于他对艺术独特而胆大的见解。1946年从英国军队退役,伯格先后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个人生涯,在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1948年至1955年,他以教授绘画为业。在此期间,他开始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
《关于地点的通讯十则》的结尾,伯格写到:“是的,在种种身份之外,我依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标签贯穿了伯格的整个艺术评论生涯,他对艺术评论的取向与此息息相关。在为《新政治家》撰稿期间,他很快就成为英国颇具争议性的艺术批评家。1972年,伯格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时出版配套的图文册,遂成为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于今看来,《观看之道》和当下的“政治正确”、“女性主义”、“营销经济”等热词背后的说辞颇为相似,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伯格的艺术批评依然表现出超前的敏锐和反思。他本人被认为,“改变了几代人的观看方式。”
观看先于言语。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
伯格为“观看”而着迷,他以一种接近动物本身的原始性来完成观看。而伯格对世界的感触也由“观看”而来。在《看》一书中,伯格告诉我们如何在观看动物,或是与动物进行凝视的过程中来确定自己的存在,确定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动物看人时,眼神既专注又警惕......唯有人类才能在动物的眼神中体会到这种熟悉感。其他的动物会被这样的眼神所震慑,人类则在回应这眼神时体认到了自身的存在。
伯格的观看触及四分五裂的中东,流离失所的难民,工人,波兰地区的农民,被驯服为奴隶的动物们。“对待动物的方法通常预示了对待人类的方法。对动物工作能力所采取的机械式观点后来被应用在工人身上。”而当我们“观看”伯格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就是世界变得怎么样了?苏珊·桑塔格为伯格这样写过:“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受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当我们“观看”伯格的时候,必须要做的是,从伯格以道德感和悲悯之心书写的,我们时代之前的世界中抽身出来,去思考:世界变得怎么样了?
在《本土的素描簿》里,伯格借文字和素描与自己钟爱的十七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完成了一次超越时间和死亡的对话。斯宾诺莎与伯格都热爱素描,这位受到伯格仰慕的荷兰哲学家曾以研磨镜片为生,用人生最璀璨的几年写出了《伦理学》和《知性改进论》。伯格把那些“主动要求进入画面的事物”画了下来,通过对素描的实践来达成他与斯宾诺莎对事物共同的感悟。这是一次不可见的对视与观看。
一切都是不可见的。
伯格于192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父亲斯坦利是一个匈牙利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格全家迁到伦敦。在《约定》中,伯格为自己的母亲画了两幅素描,他把对这两幅母亲的肖像的看法隐藏在了文字里:“她噘着嘴唇,眉毛拧成一团,盘算着、思索着。下定一个无言的决心。”伯格的母亲出生于伦敦南部,在伯格看来,她是一位在艰苦生活中逐渐成长为堂吉柯德式骑士的女人。
从五六岁起,伯格就在担心父母的死亡。他把父母晚睡前和自己说过的最后一句话看作是,退潮后岩缝中捕获的一条鱼,用来抵御着黑暗。当伯格写下这篇《母亲》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年,母亲也在一个月前去世。
这是写作一部自传的天赐良机。我对自己一生的叙述不会再伤害到他们。这书若完成了,摆在那里也就有点像我的父母似的。自传始于一种孤独感,它是孤苦伶仃的文学体裁。
伯格并没有完全屈服于这种孤独感,《我们在此相遇》是这个“擅长讲故事的人“的最接近自传的作品,《昆西四季》是伯格留给世界最后的影像。
1926年离开英国后,伯格将自己余生四十多年的时光都交给了法国阿尔卑斯大区一个叫做昆西的村庄,而这部全称为《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的电影拍摄于伯格八十多岁的时候。在《观看之道》粗糙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伯格身穿花纹衬衫,卷曲凌乱的长发,当镜头给到他特写的时候,他锐利的眼神,线条明朗的脸颊,富有力量的声音,仿佛一个被画作包围的嬉皮士。

然而,时间没有给予任何人仁慈。在昆西的冬天,伯格与自己多年的好友蒂尔达·斯文顿围坐在桌子上,伯格向斯文顿讲述自己的父亲如何教他削苹果,他们一起削苹果,为一只苹果画下一幅素描。伯格老了,依旧卷曲但已是灰白的短发,脸庞显得有些臃肿,他开始长久地忍受关节炎带来的疼痛。他坐在那里,抬头望向天花板,点燃的香烟发亮,伯格思考着如何将自己再次托付给下一个故事。
爱不受时间愚骗……
爱不随分分秒秒日日月月改变
爱直到世界末日不断绵延
若此言于我身上证明为错
则我从未写过,亦无人曾真爱过。
这位老人依旧在轻柔地诉说着自己的爱。《A致X: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是伯格在八十二岁时创作的小说。伯格虚构了一对身处苦难时代的情侣,全书的内容由爱妲写给狱中情人泽维尔的信件组成,伯格借爱妲之名,透过冰冷的高墙,无望的压迫,书写了这封献给希望,自由与爱的告白书,献给革命年代的理想者和从自我生命中消逝的人。
在《昆西四季》的结尾,伯格重新骑上摩托,带着斯文顿的女儿去兜风。画面里,一老一少逐渐消失在路的另一端。
伯格已经离开一年了,但发动机的声音似乎还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