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文学就是介入
来源:文学报 | 刘小波 2018年01月08日1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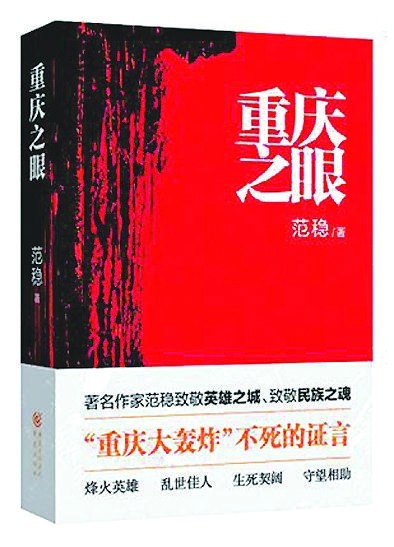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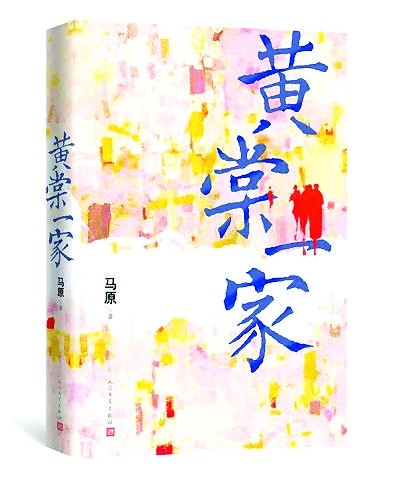


现实主义传统曾一度在新潮小说的冲击下式微,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疏远。这种弊病引起不少作家的警觉,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深度介入生活与现实主义复兴的态势,拉近了文学与生活的距离。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总体特征是以现实书写为主,作家深入生活,深度介入现实,对人类面临的现实处境有着细微深刻的描摹,这种书写态度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磅礴力量,这也正是作家对普遍被诟病的当代文学创作脱离现实的有力回应。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争书写有了新的动向,出现了很多新的篇章,战争历史题材书写既缅怀历史,更回应当下;二是批判现实主义依旧流行,作家们不光介入现实,还对现实进行批判,具有新的力度;三是对城乡空间进行深入挖掘,城乡书写有了新的思路;四是除了对现实物质世界的关注,作家们对心灵世界的探幽进行了新的尝试,出现了很多探讨灵魂世界的作品,通过对心灵世界的观察,写出人性的多样和复杂;五是主旋律书写有了新面貌,对重大现实事件都有文学的表达;六是一些反现实的现实书写也通过作家创造的现实对时代予以表达。总之,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题材纷呈,但都深深扎根土地,处处介入生活,全面围绕现实展开,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问题、新出路、新面貌。在现实描摹中体现了人性书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一,战争历史书写有新的切入点和视角。2017年战争书写集中爆发,以战争为主题和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集中呈现。战争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大宗,2017年的战争小说在延续之前的书写模式基础上有所突破,很多作品写出了战争小说的新篇章和新高度,与一般作品单纯的仇恨情感抒发和平铺直叙的描写有了很大差异。战争书写融进爱情、人性、历史、文化等多重元素,内容更多,叙述线更密,韵味也更丰富。赵本夫的《天漏邑》中的主要线索是民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爱恨情仇;张翎的《劳燕》以战争为切口书写女性命运,探寻人性的复杂性;范稳的《重庆之眼》则在直接书写“重庆大轰炸”的大背景中展现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以及当下对待历史的态度。王雨的《碑》、李明忠的《安居古城》与之相仿。严歌苓的《芳华》从侧面写到了战争,战争书写与人性反思结合在一起。战争书写还出现了新的切入点和新的视角。叶兆言的《刻骨铭心》、陈正荣的《紫金草》、陶纯的《浪漫沧桑》都是如此。除了战争书写,很多历史题材的写作也有新的突破,这些作品大都是透过历史回应当下。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刘庆的《唇典》、宗璞的《北归记》、修白的《金川河》、肖克凡的《旧租界》等都将历史经验予以重写,对当代生活有警示作用。总体来看,这些战争历史题材的书写较之以前的书写达到新的高度,尤其是宏大叙事中的小情致等细节描写十分精致。
二,现实批判体现作家对社会的关切。深度介入现实仍然少不了批判,现实批判书写是2017年度长篇小说的特征之一。介入现实并不仅仅是呈现,很多作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现实进行了批判。2017年的长篇小说对官场腐败、高校怪相、社会乱象都进行了深度书写,对现实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将反腐小说提高到新的阶段,随着同名电视剧的播出,关于反腐题材的作品也火起来了,从高官到底层官员腐败落马都有所展现,进行人性的深度开掘;李佩甫的《平原客》、杨少衡的《风口浪尖》、钱佐扬的《昙花》涉及高官腐败;马笑泉的《迷城》、李骏虎的《浮云》、红日的《驻村笔记》则涉及基层腐败;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将笔触伸向高校,揭示高校的腐败现象。马原的《黄棠一家》、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都用文学的方式对时代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的写作无论是采用现实的直接描摹,还是用荒诞、反现实、非自然等艺术笔法,抑或是使用黑色幽默、非虚构等技法,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现实,深度介入现世生活的。小说不可能是绝对的零度风格,而是具有叙事伦理,无法摆脱道德说教的一面。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实际上也显示出作家们的一种叙事伦理,批判也好、启蒙也罢,都是对生活美好一面的期许和向往。
三,城乡书写探寻统筹协调发展之道。一直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都是作家笔下关注的对象,城乡空间变奏成为21世纪以来文学表达的重要母体之一。这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书写既有矛盾展现,更有和解之道。近期的城乡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并非呈现二元对立,而是描绘各自的优劣,探寻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之道。城乡空间书写既有乡村风俗的生动画卷,也有大都市的纸醉金迷带给乡村的冲击,既有日常生活的描摹,也有人性深处的反思。2017年的长篇小说中有多部作品涉及这一书写。《平原客》既是反腐小说,也是一部探寻城乡关系的作品。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塑造了梁光正这一中国普通农民形象,通过他的寻亲之路,回顾中国农村的变迁史,也书写了农村面临的现状,特别是对中国式父子(女)关系的书写极具典型性。陈仓的《后土寺》延续其农民进城的书写。赵献涛的《村官》反映农村历史变迁。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以乌托邦的形式书写了一个虚拟城市的种种故事。城乡生态环境是城乡空间的基本立足点,城市化进程中对乡村生态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小说对生态环境恶化带给人类的伤害也有所体现,钟正林的《水要说话》、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对此有所表现。
底层写作是城乡书写的另一选题。底层是城乡一个重要的空间场域,关于底层的书写也是关于城乡空间的探讨。贺享雍的《盛世小民》、李亚的《花好月圆》、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李师江的《中文系2:非比寻常》、陈彦的《主角》、姚鄂梅的《贴地飞行》、麦子杨的《可口与可乐》、贺享雍的《大城小城》等作品,既是关于底层的书写,也是关于城乡空间的书写。许多新作品聚焦到这一点上,通过书写婚姻关系来透析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精神层面的变迁。王旭东的《复调婚姻》、张五毛的《春困》、鲁敏的《奔月》、陈庆予的《我是你的谁》、马拉的《思南》、乔叶的《藏珠记》等都是这样的文本。此外,还有很多文本不是以此为主题,但也涉及婚姻关系的思索。城乡空间书写细致描摹了一幅幅众生生存百态图,既有生存空间、生存环境、生存状态描写,也有情感、伦理、精神的书写。芸芸众生的生存空间、奋斗打拼、情爱婚恋、精神面貌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这也正是文学拉近与现实的距离、深度介入生活的最好例证。
四,心灵探幽探询个体心灵密码。除了对物质层面的现实关注,很多作品关注人的精神层面,探询灵魂深处的秘密,很多作家对心灵世界的探寻关注进行了新的尝试。不少作品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探询个体心灵密码。上文提到的城市小说《游戏是不能忘记的》里很多内容涉及心灵救赎与忏悔。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在这一领域的书写较为典型。陆天明的《幸存者》讲述了一代人在时代浮沉下的追求与探索,更是一部关乎心灵世界的小说,李陀的《无名指》探询人的心灵问题。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则将笔触伸向佛法。默音的《甲马》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更是一部心灵史。在交叉叙述的三段时空中,谢晔一路找寻,既是找寻逝去的时间,也是寻求当下的心灵慰藉。很多心灵探幽的作品走向人性探寻的纵深处。几乎所有题材的小说最终都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还有很多小说直接立意于此。安昌河的《羞耻帖》最重要的主题是对人性的忧患和呼唤。庞余亮的《有的人》有多条故事线,最终复归到人性这里。作者用多种手法多种人称以及多种身份的交叉叙述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充满人性的悲凉,也丰盈了人生的光华。须一瓜的《双眼台风》用精致的细节构筑起精彩绝妙的故事,同时也不断伸向人性的深处,将人性探询纵深化。
五,主旋律书写呈现新态势。宏大题材的主旋律书写在2017年也出现了较多作品。对“一带一路”、“香港回归”、“精准扶贫”等重大现实事件都有文学表达,主旋律书写呈现出了新的态势。巴陇锋的《丝路情缘》是中国丝路题材长篇小说的先声之作。朱秀海的《乔家大院》(第二部)描绘了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深刻发掘中国商道诚信经营、以商救国、以商富民的文化精神。张强、李康的《我的1997》反映香港回归后20年的岁月变迁。精准扶贫书写是2017年主旋律书写的一大亮点。红日的《驻村笔记》将笔触伸向具体的精准扶贫场面。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讲述毛志平一行人驻村扶贫的日程,反映了如火如荼的扶贫面貌。小说有矛盾、有冲突,有思索,更有千方百计解决问题的决心与努力。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讲述青年干部李光荣下乡进行文化扶贫的故事。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既是生态主题的小说,也是一部扶贫题材作品,描写了白羊峪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生动画面。后现代社会削平深度,文学仍在坚守,具有时代感的宏大书写是最具深度的表现,弘扬主旋律,讴歌正能量的作品不断涌现。
六,反现实书写体现作家的艺术探索。现实主义的源流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关注和焦虑。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也会有“反现实”的书写,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可以创造出艺术层面的现实。2017年的很多作品是现实主义题材书写,但也都呈现出了反现实的一面。《劳燕》的叙述者是亡灵;《藏珠记》的女主人公从唐朝活到现在;王旭东的《复调婚姻》出现了刘光华现世的一家三代婚姻爱情故事和他死去后在阴间的“一生”这两条线索;《太阳深处的火焰》仍有红河一贯的神性书写。
反现实的书写往往以寓言的形式呈现。赵本夫的《天漏邑》情节奇谲、人物生动。整个故事悬疑丛生,充满了非自然叙事与反现实书写,创建了一个关于自然与文明的寓言式作品。卢一萍的《白山》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寓言式书写。非自然叙述虽然有反现实的一面,但仍是立足于现实的书写,是艺术创造的另一现实。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无论是战争历史、城乡空间、现实批判,还是心灵探幽、反现实的现实主义题材书写,都指向现实、指向人性,是人性探询的多样化、纵深化书写。这些书写都是深度介入的姿态,将文学从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渐渐拉回现实。对现实的描摹自然是作家们最主要的功课,这是希望文学履行它的介入功能。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深度介入现实的就是成功的作品,文学不是社会学文本,很多作品成为了社会学文本,失去了美学性和艺术性。部分作品踏上主题先行的老路,人物类型化脸谱化,社会性盖过了文学本身的属性。现实书写并非对生活的原样复制,而是提炼出生活性。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同时都是伟大的形式主义者。这种生活性,让作家超越生活,成为生活自由的仆人。当一大批作家进行文体实验、技法创新、模仿西方之后,开始了自我更新与完善。后现代小说远离生活,陷入自娱自乐、虚无缥缈的怪圈,现实主义正是对此有力的反驳。2017年的小说全面介入生活,现实主义并非只是一个文学术语、一个理论概念或者一种文化思潮,而是对现实、对生活、对社会,包括对精神层面的深度介入与直接打量。无论如何,这些作家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始切入生活,进行具有本土意识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接地气的写作态势。现实书写渐趋常态化,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与关切让现实主义文学渐渐走上正途,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