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瑞:复原非洲形象 探讨非洲道路
来源:文艺报 | 朱振武 2018年05月04日0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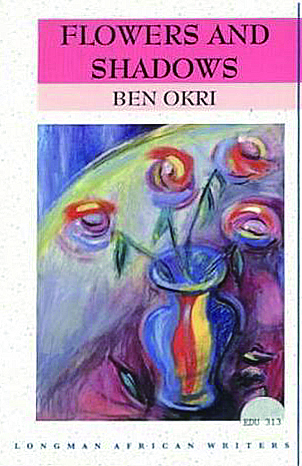
《花与影》

《迷魂之歌》
近年来,非“主流”英语文学渐进主流,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虽起源于英国文学,但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刻画地域生活、书写民族历史以及彰显多元文化等诸多特点。其中,尼日利亚英语文学是非洲英语文学的典型代表,作为非洲的发声者,非洲作家用英语刻画出生动而真实的非洲形象。踏着图图奥拉、索因卡以及阿契贝等第一代尼日利亚作家的足迹,作为第三代尼日利亚作家代表的本·奥克瑞,以其独特的非洲美学,凭借小说《饥饿的路》向世界呈现出一幅虚实交融、气势恢弘的非洲画卷,实现了对非洲精神的文学书写。
本·奥克瑞(Ben Okri,1959-)用英语写作,被认为是非洲最重要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尼日利亚中西部城市明纳,两岁时随父亲搬到纽约,9岁时回到尼日利亚。19岁时重返英国并在艾赛克斯大学研修比较文学。21岁的时候,他凭借处女作《花与影》(Flowers and Shadows,1980)在国际文坛崭露头角。之后,又凭借《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1991)获得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奖,成为最年轻的布克奖获得者。他还获得过英联邦国家非洲文学奖和阿加汗小说奖等其他重要奖项。他的作品《饥饿的路》与《迷魂之歌》(Songs of Enchantment,1993)以及《无限的财富》(Infinite Riches,1998)构成了以“鬼孩”阿扎罗的生活缩影反映战后尼日利亚以至非洲社会与政治动荡局面的三部曲。
奥克瑞笔下的非洲形象
基于诸多历史原因,白人作家的非洲形象描写引起了读者对非洲形象理解的偏见。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乔伊斯·卡里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等都先后对非洲形象做出过或多或少的不实描述。英国作家乔伊斯·卡里曾以尼日利亚为背景创作出《艾萨得救了》《非洲女巫》和《约翰逊先生》三部小说。其中,《约翰逊先生》曾被认为是最好的尼日利亚小说。对此,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就曾指出“我们讲的故事绝不能为外人所道”。阿契贝认为主流的英语小说对非洲的描述“大部分是情节简单的故事,有着善良的白人和邪恶的野蛮人”。无独有偶,英国作家约瑟夫· 康拉德在其代表作《黑暗的心》中曾对非洲形象进行了“非人化”描述。“就在这棵树的旁边,还盘起腿坐着两把瘦棱棱的黑骨头。其中一个把下巴撑在膝盖上,视而不见地瞪着眼睛,一副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样;和他同在的另一个幽灵则是前额浮在膝盖上,仿佛被一种极度的困倦所压倒;四周散开的其他人,有着各种各样不成形的瘫痪姿势,恰像一张描绘大屠杀或是大瘟疫的图片上所画的那样。”对此,阿契贝以《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脏〉中的种族主义》为名,提倡非洲人自己书写非洲新形象。
在阿契贝等先驱作家的影响下,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呈现出真实的非洲风貌速写,贫穷的非洲生活特写以及落后的非洲人民之声,并通过机器对生态造成的破坏、政治给生活带来的混乱和白人对非洲人民生命的迫害,还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非洲形象。奥克瑞对非洲形象的刻画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中已经成为典型范式的非洲形象。通过对非洲的传统食物、祭祀活动以及具有显著地方性的非洲风俗迷信等日常生活的细节刻画,奥克瑞揭开了非洲形象的神秘面纱。非洲人的生活贫穷落后,但并非是“疾病和饥饿的黑色阴影”,非洲大地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并不是殖民者开采自然资源的目的地。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以崭新的人物形象和民族形象颠覆了以往白人作家笔下黑人的刻板印象,并从黑人作家的视角刻画出白人殖民者的真实形象,从而打破了被英美文学长期垄断的局面。
从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开始,非洲作家的写作方向便从重现历史转向了揭露深刻的社会现实。奥克瑞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呈现出非洲原貌写生图,从而颠覆了以往现代西方世界眼中原始野蛮的非洲形象。西方殖民入侵对原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非洲的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生产模式由传统的农业转向务工。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对西方政治体制的邯郸学步并没有使他们实现民主,也没有使人们摆脱饥饿与贫穷,反而造成了权力之争。与白人作家笔下“非人化”的黑人形象不同,奥克瑞真实地揭露了白人殖民者的伪善与残忍,呈现出一个贫穷落后的被殖民荼毒后满目疮痍的非洲形象,揭露了殖民者利欲熏心、残酷无情的卑劣行径,表达了对非洲人民悲剧人生的深切同情。
奥克瑞笔下的非洲梦
非洲作家肩负着非洲民族书写的重任,对古老非洲梦的建构体现了非洲作家的民族情怀。在《饥饿的路》中,奥克瑞将约鲁巴民间传统的神话传说通过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了以幽灵世界、梦境世界和多重幻像相融合的虚幻空间。通过幽灵世界的美好和梦境世界的预言表达对原始非洲梦的坚守和对未来非洲梦的憧憬。
“在我成长的传统中,对现实有着多维度的解读,其中包含着神话、传说、祖先、灵魂与死亡。”奥克瑞说。在非洲,死者的灵魂可以借助动植物等重返人间,并通过梦境等征兆影响现世的人们做出选择,帮助其脱离危险。《饥饿的路》中,幽灵世界是非洲人心中的一方净土,象征着非洲人对原始非洲文明的崇拜与依附。幽灵世界的贤王象征着非洲祖先;鬼孩阿扎罗象征着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亚;贤王在冥冥之中给阿扎罗提供的保护,体现出古老文明对新生国家的指引与帮助。通过幽灵世界中贤王对阿扎罗的多次指引与庇护,奥克瑞实现了对古老非洲梦的回望与追溯。“非洲神话是非洲文化艺术的土壤,它不但培育了非洲的传统宗教和文化,而且孕含着一种非洲民族精神。”(李永彩)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借鉴了许多古老的非洲神话传说,其中最关键的则是关于“路之王”的传说。这个神话传说正是“饥饿的路”的由来。路之王是贪婪的统治者的化身,从西方殖民统治到各路政党统治,非洲人始终无法摆脱统治者贪婪的血盆大口。统治者不断索取,导致了人们一直无法摆脱饥饿的命运。阿扎罗是非洲古老文明和西方文化双重浸润下的结合体。爸爸是阿扎罗的守护神,因此奥克瑞通过爸爸的梦境来预示非洲未来的出路,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的非洲梦的憧憬与探索。
幽灵世界、神话传说以及梦境与幻像等具有浓厚的约鲁巴文化色彩,呈现出一定的魔幻性。奥克瑞将民间宗教、民俗和口头神话与原始传统文化的巫术、仪式、文化遗存和符号结合,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虚幻空间,象征了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亚在发展中对古老非洲梦的坚守和未来美好非洲梦的憧憬。在这条艰难的诞生之路上,古老的文化与传统仍然是非洲人民的信仰所在。他们坚持着自己原始的非洲梦,相信祖先可以庇护他们。同时,他们又期待着未来美好非洲梦的实现。然而,任何文化都具有两面性。对非洲部落传统的偏执坚守会导致故步自封和愚昧落后;西方殖民入侵带来破坏的同时,也有着先进文化影响的一面。多元文化可以弥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缺陷。
奥克瑞笔下的非洲路
殖民前的非洲之路是一条“饥饿的路”。随着殖民入侵,对原始之路的继承与对西方殖民的模仿并未使新生的尼日利亚走向理想之路。长期被殖民的历史,使非洲处于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复杂环境中,因而形成了一个杂合体。《饥饿的路》中,奥克瑞通过寇朵大婶的分叉之路、爸爸的迷宫之路和阿扎罗的循环之路来探寻民族的出路。
新殖民主义时期,西方文明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非洲人。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殖民的双重影响下,非洲的未来之路走到了迷茫的分岔口。寇朵大婶的分叉之路体现了一部分非洲人逐渐摆脱非洲传统,开始接纳并崇尚西方殖民文化的过程。寇朵大婶在杂糅的第三空间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文化认同的失衡让她在分叉之路上渐渐走向了文化边缘人的尴尬窘境。
阿扎罗的爸爸代表了大多数从农村到城市,由务农到佣工,在阶级剥削和殖民影响的双重重压下忍受着不公和屈辱的非洲底层人民。在《饥饿的路》中,他走了一条迷宫之路。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杂糅的尼日利亚发生着巨大而快速的变化,原本简单的路也变得错综复杂。非洲人民对未来出路的探索也一度迷失于混乱中,未来的出路像迷宫的出口一样难以寻觅。西方殖民的机器、原始文明的毒药以及政客与百姓的自私都会给非洲家园带来毁灭。人们要想摆脱当下充满饥饿、贫穷、暴乱的路,就要打开心门,用新的目光打量世界,尊重一切生灵,不滥用权利,既不走愚昧落后的路,也不走腐败贪婪的路,坚持爱与正义,为陷入苦难的非洲找到出路。
阿扎罗的循环之路反映出了生命的周而复始,这与非洲传统的生死观不谋而合,万事万物都在循环往复中生生不息。阿扎罗的漫游经历就是对非洲原始之路的怀念惋惜,对非洲现实之路的深切体会以及对非洲未来出路的摸索探寻。固守本土文化与抵制西方文明并不会摆脱饥饿的路,只有保留本土文化的精华,顺应历史潮流才能为未来之路找到出口。
奥克瑞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结合尼日利亚悠久的历史、异域的文化、民族特色和日常生活,并通过英语这一文字载体呈现了非洲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弘扬了非洲精神,完成了民族精神的书写。他真实刻画出了殖民前原始的非洲形象和具有西方殖民烙印的非洲形象,打破了白人作家笔下刻板的非洲印象,改写了白人作家笔下非洲大地是蛮荒之地,非洲人是野蛮人的偏见,从而打造出了丰富多元的非洲形象。借幽灵世界、梦境世界以及非洲神话传说来完成古老非洲梦的追溯和未来非洲梦的憧憬。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与碰撞中,以个人出路的摸索来表达对现实生活中非洲路的探索。通过对非洲原始文明之路的回望与坚守,对非洲现实之路的揭露与抨击,以及对非洲未来出路的思考与探索,并结合多样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题完成了对发展中非洲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