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藏文版翻译出版往事
来源:中国民族报 | 降边嘉措 2018年05月24日1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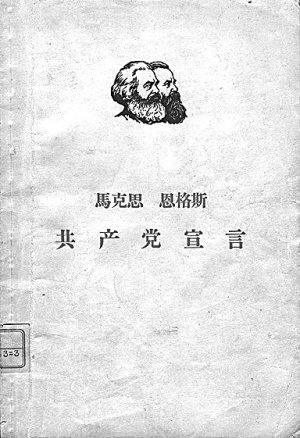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汉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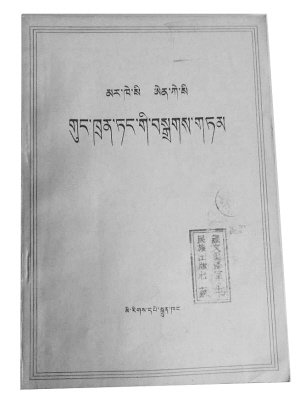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藏文版)
今年是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回顾藏文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情况,对于我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试译开始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就非常关心和重视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事业。藏文的翻译出版工作是从翻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始的。
当时,中央还没有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共同纲领》蒙古文版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翻译的;朝鲜文是在吉林延边翻译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是在新疆翻译的。而西藏尚未解放,中央就把翻译藏文版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中央民委(现国家民委)参事室。
参事室人不多,只有昂旺格桑、黄明信等几位同志,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翻译家。
那时还是铅字印刷,北京连藏文的铜模也没有。民委领导了解到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下设有翻译印刷机构,有藏文字模,遂请示紧急从南京调运。曲洛拉就是带着藏文字模从南京到北京工作的。
195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颁发命令,决定成立民族出版社,任命萨空了(蒙古族)为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民委翻译局,任命朋斯克(蒙古族)为局长。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翻译局和出版社的经常性任务。
1956年,以苏共“二十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分歧,发展到公开论战。中央提倡读马列的原著,笔者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接触藏文翻译工作,最初主要是核对和校对。
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亲自向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了马列主义的30本书,并出版了16开的大字本,还有线装的珍藏本,供老同志学习。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宁选集》一至四卷。中央要求民族出版社翻译马列的30本书和《列宁选集》。但当时民族出版社藏文室连《毛泽东选集》都未能出齐,根本没有力量翻译马列著作。社领导就决定试译《共产党宣言》,并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和白登。
召开“理论务虚会”
为提高翻译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整体水平,经国家民委党组批准,民族出版社召开了“毛主席著作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座谈会”。这次会议在民委副主任兼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萨空了亲自主持下,从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初,先后开了4个多月。
会议分两个阶段、两个部分:第一阶段,中央领导、民委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就翻译毛主席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报告,会议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举行。田家英、陈昌浩、姜椿芳等领导到会讲话。
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后到莫斯科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当时,他正在主持翻译《共产党宣言》第28版。
陈昌浩说,从陈望道翻译第一版《共产党宣言》至今,几乎所有著名的翻译家、理论家都参加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连郭沫若也不例外。即便如此,包括即将出版的第28版,也不能说“尽善尽美”“到此为止”,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
陈昌浩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发出这样的感慨:“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翻译工作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懂两种文字,那起笔照着翻译就行啦!有什么难的?其实不然,个中的甘苦,只有经历过的人自己最清楚。”
陈昌浩以《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为例来讲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导师,而且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具有语言天赋。开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句话中,“幽灵”一词就很难翻译。
在德语里,“幽灵”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它是一个新出现的事物,让旧世界感到震惊和恐惧;第二个层次,它还没有变成现实;第三个层次,它必然会变成现实。它与《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相照应,即“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陈昌浩解释说,汉文用“幽灵”,其实没有能够准确地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共产主义如果仅仅是“幽灵”,那么,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只有可能性,而没有现实性。但根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必然变成现实,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
陈昌浩说,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最准确的词汇。这次修订第28版,他们组织了几次专家讨论会,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汇。随后,他又鼓励我们说:“你们第一次翻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能要求尽善尽美,更不能求全责备,只要态度认真、严肃、负责,达到现有的最高水平就可以了。”
陈昌浩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所以放得开,思想也很活跃,结合我们提出的实际问题,讲得生动活泼,使我们感到很受教育、很受启发、很“解渴”,能解决具体问题。
在谈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时,陈昌浩说,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解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送来的呢?是通过翻译。因为中国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不懂外文,尤其不懂德文和俄文,他们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是依靠翻译。因此,翻译工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同样的道理,做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陈昌浩还叮嘱我们,经典作品是用心血和生命写的。你们是普通的翻译和编辑,不是经典作家,但你们在翻译、编辑经典著作时,一定要用经典作家写作经典著作的精神和态度去进行翻译和编辑,才有可能逐渐接近和理解革命导师和经典作家的博大精神和深邃思想。
陈昌浩、田家英和姜椿芳等领导同志的报告,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发。仅“幽灵”一词,就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议论。对于各种民族文字怎么翻译“幽灵”,大家进行了交流和比较。
民族出版社没人懂德文,都从汉文转译。于是查阅了很多资料,在《辞海》等权威的著作中,对“幽灵”有这样的解释:幽灵,谓人死后的灵魂,以其生前的样貌再度现身于世间。还有一种说法,幽灵泛指鬼神。从这些解释来看,“幽灵”一词还不能充分表达德文原意。汉文中的“幽灵”,属鬼魂一类,它能够游荡,能够让人感到恐惧,但永远变不成现实,不可能到现实生活中来。
第一句话,就把各种民族文字的翻译者们难住了。萨空了特别提醒我们藏语组说:“藏语里宗教词汇很丰富,关于灵魂的表现形式也很多,你们应该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他还特别指示我们把翻译稿拿去,向喜饶嘉措大师和阿沛副委员长等人请教。
为帮助我们释疑解惑,民委领导还请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曾世英等人,以及文字改革委员会、马恩列斯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给我们作指导。他们从马列著作汉文版和毛泽东著作的特点来分析汉语文的结构和特点,然后返回来进一步讲解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和特点,比较汉语文与外文、少数民族语文的不同。
就我所知,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全面、深入地讨论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它不仅对做好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民族出版社的翻译工作有了质的飞跃,也对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磨一剑,《共产党宣言》藏文版问世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增强识别假马列主义政治骗子的能力。毛泽东亲自开了书单,向全党推荐6本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民族出版社决定,立即将这6本书用5种少数民族文字翻译出版。
此前,民族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藏文版(修订本)《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等。通过这些著作的翻译,上级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翻译能力也有了基本的认同和信任。因此,在接到毛泽东推荐的6本书的翻译任务时,我们有能力、有条件进行翻译了。
从1970年开始,我们把这6本书作为一个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来进行。经过努力, 1971年,《共产党宣言》藏文版第一版正式出版,向全国发行。
“文革”10年,我主要就是完成毛泽东著作、马列著作等的翻译出版工作。因此,我不但没有丢掉业务,而且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重点著作,汉文水平、政治理论水平和翻译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终生受益不尽。就这一点来讲,与同时代的很多人相比,我是很幸运的。
与别的文种比较,藏文的翻译工作更困难。因为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都有较为完善的工具书。惟独藏文没有这些条件,必须从头做起,从零开始。很多名词术语,都要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创造。
翻译家林琴南在谈到翻译的艰难时,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林琴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传统文化的功底很深,汉语又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词汇最丰富、表达力最强的语言之一,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词汇,林琴南尚且要“旬月踟躇”,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和发展,更为艰难。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藏文室一面翻译,一面编辑《汉藏对照词汇》,搜集整理了4万多词条,并编印成册内部发行,供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文翻译出版部门使用。
“文革”结束以后,民族出版社在我们编辑的《汉藏对照词汇》基础上,汇集各地翻译的新词术语,由高炳晨负责,于1991年编辑出版了《汉藏对照词典》,共收录8万多词条。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丰富和规范藏语新词术语,发展现代藏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民族出版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