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澳大利亚剧作家戴维·威廉森
来源:文艺报 | 高萍 2018年06月22日0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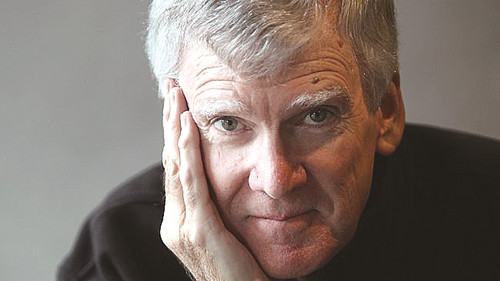
戴维·威廉森(1942-)是澳大利亚戏剧史上最高产、最具影响力的“新浪潮”剧作家。他在作品中讽刺当代社会各种现实问题,塑造各类小人物,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他运用澳大利亚习语,关注具有澳大利亚特点的主题,为作品贴上了鲜明的标签,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戏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戴维·威廉森出生于墨尔本,自小酷爱戏剧、文学,在数学和物理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天分。上大学期间,威廉森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为学生杂志和剧院撰写讽刺小品文。1964年,他获得莫纳什大学机械工程学学士学位,从事过汽车设计、机械工程讲师等职业,兼职攻读了墨尔本大学的社会心理学硕士。60年代他积极参与反越战运动。1972年,在《唐的聚会》(Don’s Party)(1971)和《搬迁者》(The Removalists)(1971)两部戏剧大获成功后,威廉森成为全职作家。除了创作戏剧,威廉森也越来越多地撰写影视剧和改编剧本,经常赴英美等国参与作品在海外的制作。近50年来,威廉森共创作了50多部戏剧作品,创作和改编了2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剧本。他被视为澳大利亚最成功的剧作家,2014年,创下单在悉尼就正式上演8部剧作的记录。威廉森不仅在澳大利亚本土取得成功,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对澳大利亚戏剧的认知。
戴维·威廉森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同观众一起思考人性,探索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各类社会现实问题,包括警察、家庭暴力、性别主义、政治大选、政党政治、学术界、法律司法界、体育界、艺术圈、社会公平、办公室政治、工作场合性骚扰、完美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文学节、商业化、传统、对权力的欲望等。
《搬迁者》是威廉森最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剧作之一,呈现了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存在的社会问题,包括警察暴力和权力滥用、家庭暴力、法律秩序以及反权威等。话剧开场,西蒙德警官在对新警员罗斯训话,此时凯特和菲欧娜两姐妹前来报警,指控菲欧娜丈夫的长期家暴行为。抱着趁机占两姐妹便宜的念头,两名警察答应帮助她们。菲欧娜回家打包东西时,她的丈夫肯尼忽然回家,随后搬家公司的人和警察也到了。当姐妹俩先行离开后,警员罗斯关上门将肯尼暴打到失去意识。当他以为自己杀死了肯尼,正感到害怕时,肯尼爬出了屋子。他们坐下一起喝啤酒,西蒙德警官试图收买肯尼,让他不要将事情声张出去。正当一切似乎安排妥当时,肯尼突然倒地身亡。《搬迁者》精准刻画了当时澳大利亚的社会现实,凭借此剧,威廉森先后获得英国戏剧专业大奖乔治·迪万奖、澳大利亚作家协会奖最佳舞台戏剧和最佳剧本奖等。
在创作与同年的作品《唐的聚会》中,戴维·威廉森对政治的探讨较多。1969年10月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之夜,唐·汉德森夫妇在家中举办了一场聚会,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期望当时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赢得大选,但选举结果使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参加聚会的人不停地喝酒,男人们满口澳式粗鄙下流的语言,还有人趁机调戏年轻女性。醉酒的人们开始坦白自己失败的梦想,探讨婚姻问题,争论阶层划分以及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分歧越来越多,人物们愈发怅惘郁闷。剧作中充斥着针锋相对的争论,火药味十足。批评界认为威廉森将戏剧背景设为联邦大选的做法相当激进,政治倾向太过明显。有评论家认为该剧反映出了澳大利亚郊区生活的无聊使人的行为变得极端,讽刺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道德状况。威廉森自己则认为,《唐的聚会》主要讲人过了30岁,梦想遭遇冷酷现实检验的经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悲剧。
《足球俱乐部》(The Club)(1977)将关注点转向体育界,尖刻地描写、讽刺了澳式足球联盟球员交易的幕后阴谋和管理者争权夺势而不择手段。故事发生在一家历史悠久却好几年没有拿过联赛冠军的顶级足球俱乐部。俱乐部新任主席特德任命格里担任管理人,以排挤俱乐部的英雄人物乔克。特德和乔克各自使出浑身解数争夺权力,而格里静观其变。与此同时,俱乐部里其他人物也互相争斗。最终,俱乐部同整个时代一样发生了变化。在威廉森的笔下,这家足球俱乐部就是7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和工作场所的缩影,人们在传统、忠诚与金钱、野心之间权衡。在《足球俱乐部》中,传统与进步和成功相对立,即在当今世界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抛弃传统。只有传统不会阻碍进步和成功时,人们才会支持、尊重传统。《足球俱乐部》还涉及人们对待商业主义的态度。俱乐部逐渐丢掉传统,随着富有的企业家们赞助大量资金购买球员,俱乐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商业化进程,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体育商业化的接受。除了在澳洲本土大获成功,1978年,《足球俱乐部》也在华盛顿、纽约百老汇成功上演,被誉为“ 百老汇第一部成功的澳大利亚作品”;该剧在中国也广受好评,至今仍定期上演。
威廉森80年代的剧作所关注的问题更加广泛。《完美主义者》(The Perfectionist)(1982)描写在澳大利亚女性积极争取权利的背景下,婚姻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女权主义。《凯恩的儿子们》(Sons of Cain)(1985)探讨的是媒体在社会公平中的角色。《翡翠城》(Emerald City)(1987)描述了一个家庭从墨尔本搬到悉尼的经历,刻画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语言苛刻、充满讽刺,讨论了商业化的影响和现代都市中人的贪婪。《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s)(1995)是威廉森少有的几部回避自然主义的作品之一。该剧探讨了人性和社会文化问题,颇具哲学意义。威廉森在剧中针对诸如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进行了讽刺,引发了学术界的批判,认为这些是他政治保守主义的表现。《灵魂伴侣》(Soulmates)(2002)所涉及的主题与《死去的白种男人》有类似之处。剧中两位作家——伟大的文学作家麦克斯和成功的流行作家卡蒂针锋相对,在批评、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两位作家就文学和金钱、流行性等话题争执不下,戏剧在一个文学节上关于艺术与商业小组的讨论中收尾,尽显虚伪、信仰缺失和谎言等现实社会问题。
戴维·威廉森还创作和改编了25部影视剧本,赢得了国内外各类奖项。由他担任编剧的《加里波利》被视作最伟大的澳大利亚电影之一,由彼得·威尔执导并共同担任编剧。在1915年的澳大利亚,出身迥异的两名西澳短跑运动员亲如兄弟,决定一起应征入伍。这两名年轻伙伴后来被派遣到埃及训练,又来到了土耳其的加里波利——一战中一个至为重要的战场。该影片讲述了战火中的伙伴情谊、对军令的盲目服从及其致命的破坏力。作为编剧,威廉森的创作并未完全遵循历史史实,他想要表达的似乎是,这些澳大利亚青年士兵拼命战斗的真正原因或许只是不愿让同伴失望。
戴维·威廉森认为人类共同拥有某些深刻的情感。他在作品中探讨的主题、塑造的角色各有不同,但所表达的情感超越时代、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这或许是其作品长久以来受到各国观众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威廉森创造的角色都是能与观众们自身产生联系的人物,例如“搬迁者”代表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普通人。威廉森剧中人物所具有的爱恨、忧愁、愤怒、贪婪、勇气、希望等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不分国家、文化或时代。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缺陷,他们展现出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随着故事发展,他们表达情感、暴露缺陷,激发出观众的同理心。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即使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种种缺陷,仍然会努力挣扎着去追求更好的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而这无疑能够极大地鼓励观众。与威廉森有密切合作的戏剧导演桑德拉·贝茨所认为,威廉森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能让普通观众产生认同感,从各种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相信自己也能变得更好。正如许多观众的感慨:“这就是我的生活,真不知道戴维如何做到如此真实地描写我的生活?”威廉森的作品加深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的理解。其核心是对自己、对他人更加包容的渴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戏剧界的“新浪潮运动”宣扬澳大利亚文化不再由殖民传统定义,“新浪潮”剧作家们在创作时不单单挑战传统的文学形式,还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及学术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新浪潮”剧作家之一,戴维·威廉森的作品无论在语言还是内容中,都表现出鲜明的澳大利亚特色,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本土戏剧和电影的崛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戴维·威廉森成功地运用了本土化语言,他的作品中大量出现颇具澳大利亚方言特色的习语,甚至包括粗俗下流的语言,能让观众听到真正的澳大利亚的声音。在内容方面,威廉森着眼于当地社会,在作品中关注例如反权威主义、伙伴情谊、竞争精神等具有澳大利亚国民性格特征的主题。他象征性地通过澳式语言、有缺陷的角色、富有当地特色的主题、幽默和讽刺的写作手法等探索了澳大利亚社会。威廉森通过作品塑造了独特的澳大利亚身份,让澳大利亚观众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了他们自己,也提升了澳大利亚文学、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正如布鲁斯·贝内特所说,“澳大利亚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象征符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本地特性、地区意识、国际主义和文化丰富性或至少文化潜力的存在。”
戴维·威廉森的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还在于威廉森对时局深刻且超前的理解和判断。威廉森创作时对澳大利亚社会众多观念和问题所做的描述和呈现可谓精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不显得过时。例如创作于70年代的《搬迁者》所描写的家庭暴力至今在澳大利亚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足球俱乐部》和《翡翠城》等所反映的商业化问题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更多讨论。《唐的聚会》虽然是基于1969年的联邦大选创作,但角色们对澳大利亚两党政治制度的看法,对政府政策的评论在今天都未发生改变。许多观众仍然认为,每逢重要的选举时都适合再看一遍《唐的聚会》。在解读威廉森在澳大利亚戏剧发展史中独一无二的成功时,导演桑德拉·贝茨称,威廉森的成功与他对澳大利亚时局的深刻洞察,甚至在创作中对未来富有先见之明的预判密不可分。他的作品如史书一般准确且有趣地记录了澳大利亚在过去50年里的发展和变化,也见证了澳大利亚本土戏剧的不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