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 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王婉 2018年11月19日08:22
1982年,24岁的阿来发表诗歌《振响你心灵的翅膀》,从此踏上漫长的文学旅程,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乃至世界渐渐认识了这样一位穿行于汉语和藏语之间,将富有魅力的自然情志与心灵景观传达给读者的优秀作家。
11月1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四川省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承办的“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主持开幕式。中国作协副主席、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瑞典汉学家、翻译家陈安娜等出席活动。

铁凝在开幕式上致辞
“民族、自然、文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进入阿来文学世界的路标,但是,我以为,阿来的意义绝不限于此。”铁凝在致辞中说,阿来的作品,真正的落脚点,仍然是中国,以及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普普通通的人。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中国作家穿越纷繁复杂的信息与各式各样的观点的洪流,以文学的方式建立与中国的血肉联系、创造史诗的努力。铁凝认为,举办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的意义就在于此,借阿来的作品重新认识生机勃勃的中国,也可以由此讨论种种重要而有趣的话题,譬如,地域、民族给一个作家的写作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史诗在今天的文学书写中有着怎样的新的可能性,一个中国作家可以给世界文学提供怎样的经验等。她相信这样的共同探讨和相互学习,定会取得丰硕的收获。

莫言在开幕式上致辞
莫言尤其赞同研讨会的题目“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认为这三个名词比较完整地概括了阿来的创作和他大半生的生涯,但同时强调,文学上没有边地或中心之说,阿来把一个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变成了在文学上引人注目的地点。“中国很多作家都经历了同样的创作实践,就是从写自己的家乡那一方土地开始,由此慢慢深入、扩大,最终让这个地方通向世界。”他认为,研讨会的召开非常必要和及时,“我们对这个作家阅读了几十年,批评家对这个作家研究了几十年,翻译家翻译了几十年,确实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希望通过研讨让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阿来,让批评家从更新更独特、更深入的角度来理解阿来,让翻译家从更准确的角度翻译阿来。

吉狄马加主持开幕式
吉狄马加认为阿来是一位在精神层面上和文本形式上都具有创造性的开拓者,一位给我们提供了精神建构的作家,一位跨文化的卓越写作者。他说,“今天阿来作品研讨会没有在他的故乡阿坝举办,而是选择在北京召开,这明白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不对称的世界,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似乎永远存在,只是对于文学和精神创造而言,与时间的搏斗不会轻易结束,若干年后总会发现,某一个人的文字将改变我们对边缘所下的定义。”

陈安娜在开幕式上致辞
陈安娜代表与会外国专家学者致辞,直言相比于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获得世界范围关注的“大作品”《尘埃落定》,自己更偏爱阿来的短篇小说。“读阿来的短篇小说集《阿坝阿来》时,印象最深的是‘静’。这种‘静’使读者能专注于文本,读得更加细致,而不像阅读喧嚣、激烈躁动的文本那样。”她感觉阿来作品对自然的关切,特别适合北欧的口味,“因为我们也是跟大自然关系比较密切的,而印象里中国作家好像大多不够关注自然。”她呼吁与会翻译家同行,多翻译阿来的短篇小说,而不止盯着长篇、历史小说,让世界上更多读者看到阿来的那份特别的“静”。
阿来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坛,作为小说家被广泛关注和喜爱,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散文作品。近日,阿来的《成都物候记》《一滴水经过丽江》《大地的阶梯》《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和《让岩石告诉我们》5部散文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开幕式现场举行了五卷本《阿来散文集》揭幕仪式,铁凝、莫言、麦家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社长刘东风共同为阿来新书揭幕。
开幕式后,贺绍俊、孟繁华、陈晓明、张清华、潘凯雄、施战军、何向阳、邱华栋、谢有顺、穆涛、何平、陈思广、张莉、季进、张学昕、梁海、刘大先、丛治辰、岳雯等近20位评论家,与来自13个国家的翻译家、学者山口守(日本)、李莎(意大利)、墨普德(印度)、娜佳(乌克兰)、李点(美国)、金泰成(韩国)、林幸谦(马来西亚)、鲁博安(罗马西亚)、马海默(德国)、凤玲(俄罗斯)、罗宾(英国)、月月(法国)等展开研讨,从鉴赏、感悟、理论、直觉等不同路径进入,共同探秘阿来的文学世界。

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现场
从奇异经验到普遍感受
“36年来,阿来以《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机村史诗》等一系列作品为我们深描了一个美好的所在,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藏区和那片土地上的风光、人民不再是作为奇观,而是作为实在的人世风景来到我们的文学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说,“优秀的作家应当具备跨越民族、地域、血脉和文化,抵达人类的普遍感受、构建情感共同体的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尝试用二元悖反的结构来理解阿来的创作,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大文明的视角与藏地的独特眼神”,“比如机村,它是大文明展开中的一种情状,是非常特殊的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村落,在消失前最后岁月的那么一片时光。”陈晓明认为,阿来一直从非常大的文明视角来看待故乡生活,看待嘉绒地区、阿坝地区,这种文本上的大文明视角,不止是一种主题性的理念,重要的是一种时间和空间在叙事中形成的氛围。
诚然阿来有着天然的族群和多元文化背景,阿来的写作也从不回避他的族群性或地域性身份,“但是显然,他的写作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共通性或者公约性的情感、观念和普泛化内涵。”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感觉,这在阿来的创作语言上多有直观体现,“他的语言排除过于地方性的少数民族成分,是经过自我翻译的,这种携带异质文化元素的可译性语言,甚至悄然丰富了现代中文的表述,形成了可以普遍接受的清通流畅的美学风格。”
“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是阿来很多年前在一个小说家论坛上的演讲题目,而这句话在本次研讨中被反复提及和引用,成为解读阿来的一个入口。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梁海说,“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阿来感受世界的目光,也是阿来一以贯之的叙事策略。在阿来看来,藏地这样一个远离先进文明中心的地带,其历史进程都是在世界扑面而来中完成的,这些变化包括自然、生态、传统文化、伦理,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没有选择也无法逃避。”由此他认为,研究阿来必须要腾挪出藏地这个定语的桎梏,在世界的辽阔空间中审视这位作家,“毕竟一位作家的全部努力是为在整体的文化脉络当中获得他的意义。”
阿来中篇小说集《遥远的温泉》德文版译者马海默,引用阿来自己的表述 “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异类的人生”,他表示,阿来可以代表全人类声音的藏地书写,在西方社会能够找到很多“没有偏见的或者说愿意克服自己偏见的读者”。
几位西方学者、翻译家不约而同地谈到,阿来作品以充满生命多样性又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藏地世界,祛除着西方对西藏的符号化想象,提供了另外的参照,这个意义超越文学本身,同西方对西藏的惯常想象产生抵抗、悖反与博弈,为西方世界理解西藏带来了突破。
藉由历史和自然的不朽力量,从现实中超拔出来
如果说“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的文学书写,是阿来作为小说家自觉、理性的部分,那么从感知层面又该如何感受阿来的文学呢?“黄色的报春、蓝色的龙胆、红色的点地梅,野百合、蒲公英、小杜鹃、李树、樱桃数、油菜花、土豆苗、豌豆花,我们的文学中有多久没有这些鲜活的形象了?”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从阿来小说的自然观切入,阐述自己的观点,“‘万物有灵,且平等’,这是打开阿来文学之门的另一把钥匙。”何向阳谈到,穿越了“自觉”达至“自在”之境的阿来,是拥有完整世界观的诗人小说家,进行着人与万物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深层对话。她朗诵起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的古老诗句,感慨其与阿来的《机村史诗》仿佛是一次相隔两千多年的邂逅,“这两千多年来,人类和自然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但是当中总有些不变的东西,如果一个作家触到改变中的不变,并虔诚地呈现它,那就是他用他的文字对这个涌动而恒久的宇宙法则的尊重。”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对此有同感,“文学如果迷信一种变化,光有世俗性而没有超越性,写作就会匍匐在地上,站不起来。”在谢有顺看来,历史与自然的不朽,是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不变的价值根基,阿来的写作记下了这个世界所具有的这种不朽的品质,他写历史中的人、自然中的人,这两个角度的建立为阿来笔下的人物构建起一个超越性的背景,所以他笔下的人有一种从现实中超拔出来的力量。这个超越性的力量,恰恰不是宗教的力量,而是人文的力量。
“阿来小说的开头常常有意无意地表述他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有点类似于历史循环论,不是进化论,和古老的中国式运命之道遥相呼应,内容上与古今之变心有灵犀,那种进化论认识基础上的现代性对阿来来说只是容纳囊括。”《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提出,评价阿来的创作应该着眼于两个维度:一个是百年新文学中近些年才被重新擦亮的传统,即非线性、非进化的时间认知系统,这一传统从周作人到沈从文到汪曾褀一路而来,可以追溯到老子、庄子的时间观念,是对人的现世和未来更宽厚的审视和担忧。第二个维度,是世界文学中的大生态关切,即人在其中的自然文学。不是西方自然文学里面的荒野,也不是传统的中国山水画,而是今生今世的生命与中国先哲曾经定义的自然相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这就是阿来的小说。
研究、译介与传播,共同成就“经典”
从《瞻对》的非虚构文体意义,《机村史诗》中的风景政治,《尘埃落定》中的女性书写,阿来文本的现实主义、现代性、怀旧抒情性到如何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中考量阿来小说、阿来对我国当代文学东西格局平衡的贡献等,都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其中不乏观点的交锋。
“不能认为阿来是地方主义者,也不能认为他是古典主义者,他不是传统主义者,也不是现代主义者,多种线条构成了复杂的网络,他的游移恰恰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反映思考的深度,也真实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如是说。这样的研讨又一次告诉我们,作家的创造跟批评的阐释共同建构起文学的世界与生态。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介绍说,鲁迅文学院每年培训800到1000名写作者,一直把阿来的多重文体作为范例来教学、研究,“我就问学员们能不能从中获得启发,打开自己的写作,让更多文体在笔下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邱华栋表示,他自己也猜不到阿来的文体边界还有多远,总觉得阿来还会在文体上带来更多的惊喜。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广回顾了他编《阿来研究》杂志这些年的体会,他编了九期的《阿来研究》,粉碎了很多唱衰论调,这本刊物可能是唯一一个仍在出版的有关某一当代作家研究的专门期刊。
今年是《尘埃落定》出版20周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回忆说, 1998年阿来写出《尘埃落定》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学出版开始走向市场的时候,当时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对它的市场前景存在分歧。但事实证明,这部作品初版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当年即加印5万册,现在这本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共有15个版本,同时被将近30个国家翻译成不同语种传播到世界各地。“经过时间检验,优秀文学作品借助好的出版和传播,同样能够有非常好的读者市场。”《尘埃落定》从畅销到长销的成功之路,让作为出版人的潘凯雄对缺乏畅销特质的经典品质文学创作充满信心。
意大利翻译家李莎、韩国学者金泰城、乌克兰翻译家娜佳等都谈到了阿来作品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其国家的译介情况,发现中国的文学作品通过英文或者法文等其他语种作为中介再翻译的现象不是个例。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对此也有担忧,“当代文学通过不同语言的相互转译之后,能够保留多少中国元素、中国经验?”但他同时不无欣喜地谈到,当代文学的传播由政治性向审美性转变,很多专业性、审美性的评价也越来越多,“《尘埃落定》的海外传播中有很多报道文章关注作品的可读性、文学性和文本价值,也为本土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应该充分尊重海外研究,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西方对话的关系,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与接受。”

阿来在研讨会上倾听大家的研讨
“我用写作回答我自己的问题”
在研讨会最后,作为主角的阿来作了答谢发言,真诚地感谢大家的研讨。“在13岁之前,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文学、作家这些词”,至于为什么要写作,阿来坦言,他的文学书写就是进入空白的没有经验的地方,藏族人虽然有藏文,可是藏文过去主要是在寺院使用,普通老百姓并不掌握这种语言,对于文学来讲它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地带。
阿来追忆自己在家乡进行历史文化调查的细节,以及写作《尘埃落定》《瞻对》《机村史诗》的缘起。他透露,“我写这些作品是首先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比如西藏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现成的知识系统没有提供可以解决我的那些问题的办法,我自己通过写作解决更简单,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对于研讨会上专家、学者针对文体的剖析,阿来回应道,自己脑子里面没有文体的分别。“写诗、写小说、写非虚构、写散文,那是我当时的情绪、当时的思考,要表达这些情绪跟思考,拿到的材料,它适合用什么体裁就用什么体裁,可以讲故事就变成小说,讲不了但能抒发某种情绪就是诗歌,如果想做更理性的分析就是散文。”
阿来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在写作中对世界和事实的尊重之意,“就像非虚构写作所代表的一种更缜密的、对基本世界跟事实保持的庄重态度,我特别喜欢‘庄重’这个词,这种书写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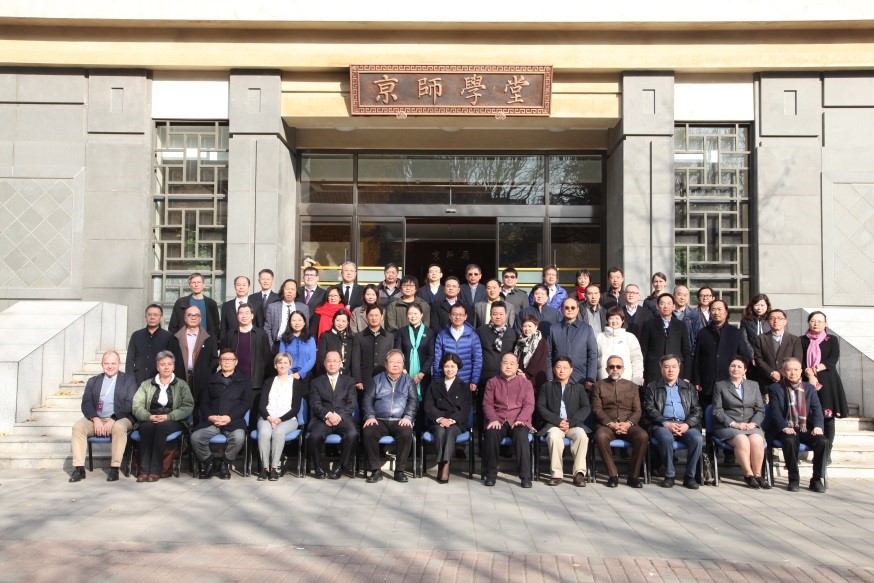
与会人员合影
(摄影:李幸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