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爱》:不知情为何物,只能彼此窥探爱的无尽之底
来源:深港书评(微信公众号) | 书评君 2019年02月14日08:58
2月14日是西方情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互诉衷肠,表达爱意,期待爱情的长久。但现如今把什么节日都过成购物节的时代,节日的意义也随之轻浮起来。
一个节日是如何由来的,它有哪些传统,又表达了怎样的观念与哲思,想必许多人都不会细细琢磨。这些不知道也就罢了,但为什么要过情人节,是将其当作获取爱情的手段,还是爱意绵绵需要一种盛大的仪式感来表达,可能许多人也不太能(敢)说清。正如说不清“爱”到底是什么一样。
英国作家C.S.路易斯在《四种爱》一书中解释了“爱”的缘由与发展,也为我们呈现了人类之爱中的某种虚妄。本书提到的观念放在当下来看或许并不算新颖,但却是我们常常无视的,又应该不断去思考的——爱,也需要学习,尤其在爱的膜拜者和拆穿家主宰了爱的言说的时代。
现代知识曾将亲爱和情爱推向神坛,高扬“爱就足够”,这是爱的膜拜者。
现代知识又曾断言,所有的爱无非是性欲的包装或伪装,这是爱的拆穿家。
在路易斯眼里,膜拜者和拆穿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将爱推向神坛,其必然结果便是惨遭拆穿;瑞士作家M.D.鲁日蒙说:“只有当爱不膨胀为神,方不沦为魔。”路易斯疏证道:“爱一旦膨胀为神,就即刻沦为魔。”这是属人之爱或人爱的铁律,因为,人不是神。人爱杀死神爱,也就等于同时颁布了自己的死亡令。《四种爱》所要破除的,恰恰就是林林总总的爱的心灵鸡汤之虚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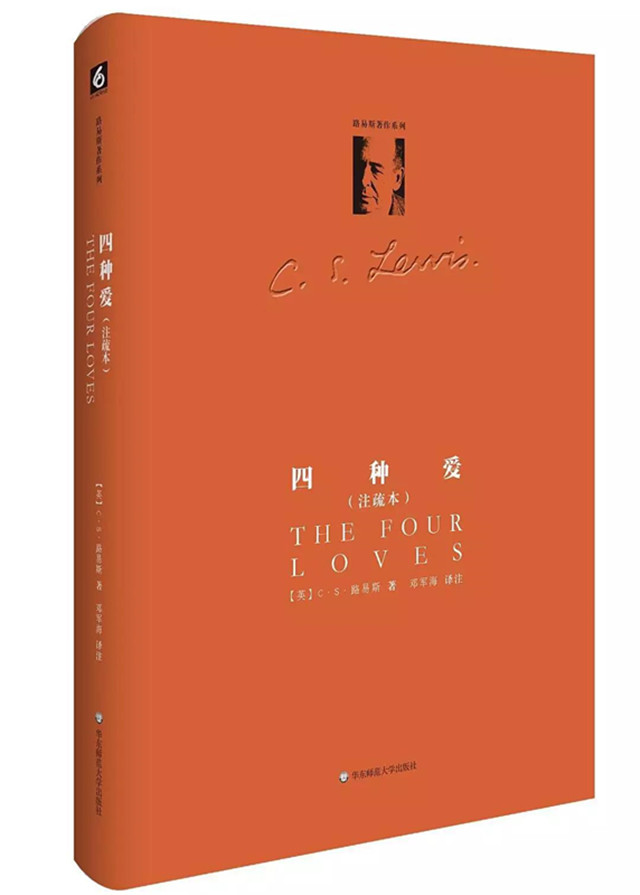
《四种爱》 (英)C.S.路易斯 著
1
在《四种爱》中的《情爱》一章里,路易斯首先用Eros一词来指我们所谓的“相爱”状态(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罗马神话中名为丘比特),或者要是你乐意,就是恋人“沉浸其中(lover are “in”)”的那种爱。当然也有人会说,情爱等同于性爱;自然也有人会否定这样的观点。在情人节里,我们谈论这些,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也不是在分辨“纯洁”与“不洁”的情爱,而是探讨一下情爱与性爱的关系。而且只能是当性欲成为“相爱”这一复杂状态的一个因素时,它才会成为我们议题的一部分。
当然,情爱之所以复杂,也关乎与先“性”而“爱”的过程。路易斯在文中也提到:婚姻取决于情爱的时代及地域,是极少数。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先祖都早早成婚。伴侣由父辈挑选,挑选的根据与情爱无关。他们发生性事,可以说除了直直白白的动物欲望,没有别的“燃料”。
对进化论者而言,情爱(即人类性爱的变体)是从性爱中生长出来的某种东西,是远古茫昧的生物冲动后来之复杂化及发展。而在个体意识里,这也是必然发生的。因为势必会有人起初对某女人只是感到一丝欲渴,后来才跟她“坠入爱河”。不过,路易斯对此是有疑虑的,这是否就是通则?颇为经常的倒是,起初只是欣然迷恋着心上人——对她整个人的迷恋,笼而统之,混沌未分。处此心境的男子,哪有空去想性。他忙着想这个人还来不及呢!
或许,对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性欲是小于“爱”本身的,他可能会告诉你对某个人渴欲的主调不是性,而是思念,正如那句被大多数人说过情话“思念到永远”一样,沉浸在爱河中的人,既是爱的静观者,也是爱的渴求者。尽管有朝一日人体里显见的性因子苏醒,这样的人也不会觉得情爱之根基就是性因子。他更有可能感到,情爱之潮来袭,冲掉了许多沙堡,冲积岩石成岛屿。或者情爱本身更像是个“伪装者”,对于单体来说,或许知道它是伪装,又或许装作(不自知)不知道它的伪装。

2
在乔治·奥威尔的作品里,这一点就极其简洁明了,他不喜欢情爱之潮占据高地,情愿性欲处于其原如状态,不沾染情爱。在《一九八四》里,他的主人公在乱搞女主人公之先,还要个保证。“你喜欢这玩意吗?”他问,“我不是只指我;我指这件事本身。”直至得到“我热爱这件事”的回答,他才满意(这是主人公最想听的话。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段小对话定义了情爱在人性中的演变。离开情爱,性欲想要的就是它,那事本身;情爱要的则是心上人。
那事,是一种感官快乐;也就是说,发生在一个人体内的一档子事。从他完事后五分钟的态度,就可以推断他在多大程度上在意那个女人本身(抽完一支烟后,谁还留着烟把呢)。而情爱,则使得一个男子真心想要某特定女人,而不是一个女人。虽难以名状但却毫发不爽,恋人渴欲的是心上人本身,而不是她所能提供的快感。这世界上,还从没有过哪个恋人寻求心上人的拥抱是出于算计——虽不经意,却算计着得到她的拥抱,其快感强于任何别的女人之拥抱。
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就曾提出过上述的问题。正如他在《物性论》第四卷劝人们不要受爱情蛊惑一样,他认为因为迷恋一个人带来的是痛苦。他说,与其迷恋在远方的恋人,不如寻欢作乐:“到处去猎色/那无所不可到处游荡的维娜丝;/或者能把你心灵的骚动引导到别处。/避开爱情的人保暖不就缺乏/维娜丝的果实;他反而是会/获得那些没有后患的快乐。”这个严苛的酒色之徒,竟出高论说,爱有损性快感。爱情,是个干扰。它破坏了他那冷静而又挑剔的分辨力。
当然,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寻欢取代情爱的观念。或许情人节不乏游走于街头的所谓浪子,但真正比节日更重要的是,对于情爱的理解与珍惜。
正如C.S.路易斯所表达的那样,情爱本身应出于“相爱”的冲动。尽管性爱是它复杂状态的一个因素,也是对于爱本身的占领与某种“伪装”,但情爱是将典型的需求之乐,转化为最地道的欣赏之乐。需求之乐,其本性就在于,让我们在对象与我等需求的关系里看待对象,哪怕是转瞬即逝的需求。而在情爱之中,需求最炽烈之时,也是将其对象最炽烈地看作本身值得称赏,她之重要远远超出她与恋人需求之关系。
在此,我无意去评判什么是真正的情爱,人之于爱是需要学习的,无论年少还是白发苍苍,爱都是毕生的课程。而在情爱的课题里如何看待性欲与爱的关系,还需要学会去关乎我们自身的事实。性欲应在情爱之中,它既是一种感知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它感受到了客观;感受到在此世界上,我们之外的某种东西。正如索洛维约夫在《爱的意义》中指出的,爱是对利己主义的否定。
情爱,尽管是快感之王,(登顶之时)却总有一种气概,视快感为副产品。思虑着快感,会将我们重又投回自我,投回自己的神经系统。路易斯说:“情爱所做的首要之事就是,泯灭赠予与接受之界限。”
3
读完《四种爱》中的《情爱》一章,想必情人节之夜该孤独的人还是会孤独着,该与爱人共度良宵的人也一刻不会耽误。但对情爱的思考也不应该停止,因为对欲望盲目的追求也只是霎那间的快感。
本文再推荐诗人丝绒陨的几首关于“情爱”的诗,在丝绒陨的诗作中,对于情爱的观察视角是独特的,他既不颂扬情爱本身,也不刻意批判个体的盲目,只是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将爱情的现象付诸于诗行。
在他的诗中,个体在爱情里就是“洋葱”——“层层剥开自己/让观看这一切的人/泪流不止”。在《爱情寓言》里,他将爱情的色彩本质比作红、黄、蓝,但最终只能是一团灰。在《你》中,你是“发热的你;露珠般的你;赠我一座深渊的你”,“你”是情爱渴求对象,却不再是某种快感的延续。在《恋人必须分手》里,我们看见“两座疲惫的深渊/一对互不相识的失眠者/彼此窥探着爱的无尽之底”……丝绒陨将情爱中的欲望、挣扎写得既冷峻又鲜明,这里所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也同样说明了“情爱在现实中的虚妄”,爱情就像是活在两个人的泳池里,我们徘徊于窒息的快感,又恐惧上岸后的孤独终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