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感谢萨拉马戈的时候,我们在感谢什么?
来源:澎湃新闻 | 杨初 2019年06月18日08:46
九年前,2010年6月18日,若泽·萨拉马戈逝世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的家中,享年87岁。葡萄牙总理若泽·苏格拉底亲自向萨拉马戈的遗孀发去唁电,对作家的离去表示“深切哀悼”,感叹:“他的消失使我们的文化更加贫瘠”;葡萄牙街上到处张贴了萨拉马戈放大照片制成的海报,上面用雪白的字写着:obrigado, José Saramago,谢谢,若泽·萨拉马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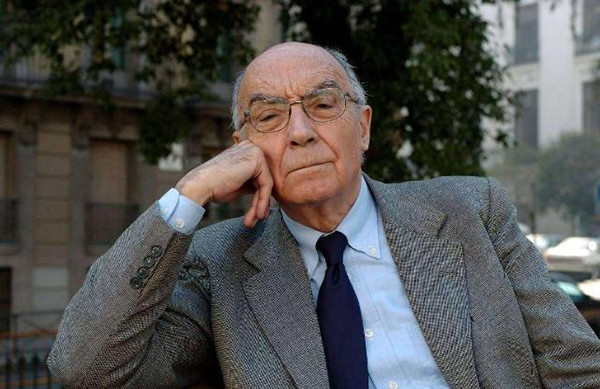
萨拉马戈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我们不能做出决定,而是那些决定自己找到了我们。对萨拉马戈来说,这话并不是指他相信某种既定命运的存在,而是指他相信,当我们无可避免地深陷于这个世界的物质中而企图看清万物的本质之时,会立即发现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是多么天真;我们会认识到,我们拥有的自由远不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多,任何决策的边界总是被我们恰巧生活在其中的历史、政治、社会环境小心翼翼地圈定,我们只能任由自己被它们发现,被它们统治,被它们定义。
这恰巧是萨拉马戈在其作品与真实人生中不停探讨与求索伟大主题:决策,自由与必然之间所存在的广泛范围,随机将我们困在其中的生活之网,人生自由和责任的边界。
在创作的无数故事中,他总是在这主题的基础上书写书中人物的命运,可爱的角色们在情节中聚散生事如浮萍,不知生命的重压几时休止,不知自由是否真的能如约到来,不知那真实的自由与想象的自由相较如何;小说的笔调、线索与讲述方式也照此进行:一个外来而富有感情色彩的叙事、解释的声音无处不在且无所不知,就是无法干预其中,只能在那既定的生活之网外,看着深陷其中的芸芸众生在法律、权力、灾难、信仰、战争和种种不公中挣扎,做出或批评,或同情,或怜悯,或愤慨的简单评价。
在真实的人生中,萨拉马戈不断在文学中所寻求的也正是人生重担中适度的自由,持续不停地写作则是这自由带来的责任。
若泽·萨拉马戈、伊比利亚半岛与拉丁美洲
1922年,欧洲大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阴霾还未完全散去,拉丁美洲仍受革命与发展的动摇战栗不止,梵蒂冈教廷正与墨索里尼谈判斡旋,葡萄牙共产党方才成立不久,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西班牙剧作家哈辛托·贝纳文特-马丁内斯,而里斯本北部名为阿金尼亚加的小村庄里,刚刚诞生的若泽·萨拉马戈则与这些历史事实缔结了神秘的联系,从那时开始就被困于这被他本人评价为“不是很好的世界”的生活之网当中。
看似荒谬的联系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写作”这个决定无声无息地找到了此位穷困潦倒无地农家的儿子,让全家搬迁阿根廷又折返里斯本;让他目不识丁的祖父在困乏的物质中以民间故事充斥他的童年回忆并将死亡前与院子里无花果树告别的诗意带入他的生命;让他文盲的母亲在他十五岁时送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让费尔南多·佩索阿和塞万提斯走入了他的生活;让他从高中辍学的技术工人变为“写作学徒”、校对工、记者、编辑到全职的著名作家,在清寒的生活中去文学中寻求自由,担负着在不公的社会中用犀利笔触进行批判的责任。
想知道这联系是如何成立,则需仔细研究若泽·萨拉马戈自诩及被贴上的种种标签。首先,最重要的,他是凭《失明症漫记》于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作品极富想像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使人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作为唯一获过此奖的葡萄牙语作家,庞大的葡语世界为此欢腾。讽刺的是,这国宝级作家绝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且是个葡萄牙人中罕见的无神论者。他整个的写作生涯都致力于批判祖国的历史、社会黑暗、虚伪的保守主义和宗教生活过大的影响,1992年,因为在小说《耶稣基督福音书》中将耶稣描绘成不具神性的凡人,萨拉马戈惹得梵蒂冈教廷震怒而斥其为异教徒,在葡萄牙这个百分之九十以上人都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无疑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政府迫于梵蒂冈的压力最终拒绝他的小说入围欧洲文学奖。萨拉马戈则选择了自我流放以示抗议,搬迁到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直到逝世,仍有一半骨灰留在岛上家中,另一半则返回故乡的一棵橄榄树下。选择西班牙,除了因为那是第二任妻子的祖国,更是因为他是一个伊比利亚主义者,认为葡萄牙长久地作为欧洲大陆后园的状况应有所改变,甚至曾在采访中提出了他的“伊比利亚乌托邦”设想,声称葡萄牙应该成为一个自治区融入文化相近的西班牙,形成一个泛民族主义联盟。仿佛以上这些还不够令人印象深刻,萨拉马戈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说:“我于1969年正式入党,那时我57岁。我一直是个基层党员,写的东西很少……我过去是,现在是,我想直到我的岁月结束我将仍然是共产党。”
种种标签叠加在一起,这位有趣的二十世纪末的伟大作家似乎不可能不与拉丁美洲产生联系,拉丁美洲也如约选择了他。关于殖民地的思考在作品中频频出现,萨拉马戈的人道关怀能直达与古老欧洲大陆相对的最遥远的新世界。作为可能是最具拉丁美洲特质的作家之一,历史的意义或历史野蛮新生的隐喻在萨拉马戈平实流畅的语言中娓娓道来,内容包含了新大陆的历史与所有未竟的事业,触及拉美国家今日面对的、世界普遍存在的以及所有人类本质触及的最重要的问题,作家或警示或歌颂或讽刺或批判,这种拉丁美洲式的关切就连在生命的末尾也未止息。萨拉马戈另一种深刻的“拉丁美洲方式”则是将魔幻现实主义带离了它诞生的哥伦比亚密林,让它以一种不同的、萨拉马戈命名为“现实的超自然”(Real supernatural)的方式在大西洋对岸野蛮生长。萨拉马戈如许多拉美作家一样关注于祖辈与故土的血泪,使奇异的荒诞的沉重的梦与现实纠缠在一起,口述故事般脱离了标点符号的语言随着角色的命运与意识流动,直至引读者对他书写的隐喻进行最深刻的思考。正如《卫报》评论所说,没有人能够像萨拉马戈这样,如此热情周全,如此自由无拘。而自由的责任呢?萨拉马戈自己则说,一个作家属于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倘若他没有受到过去的锁链捆绑,他就必须知道他生而为人的这个时代当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那么,当今之世的问题是什么呢?……最根本、最要紧的是,当世界需要批判观点的时候,文学就不应该遗世而孤立。
如果……会怎样?
萨拉马戈作为一个记者、评论家、作家进行思考与阐述是如此独特而深刻,以至于他不论多么大器晚成,读者们终会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他自己身处的时代的证人,又能不被其束缚地自由描绘历史;他是现实的关注者,又能将小说当成他最宏伟想象的实验场域:他的作品常常是一个假设而非论题,一个仍未被现实的琐碎淹没的特例,将一个与科学规律不符的超自然现象无限放大,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让“不可能”变得合理……萨拉马戈自由地发问了:如果……会怎样?
萨拉马戈想,我们都是如此盲目,那么,如果失明症像瘟疫一样蔓延而只有一人得以幸免,人类社会会怎样?答案是《失明症漫记》。
繁忙的路口,一位司机突然失明,他的角膜、虹膜、视网膜、视晶体都完好无损,只是感觉自己“淹没在一片明亮的白色之中”,之后,第二个,第三个,这白色瘟疫毫无征兆又无解地侵入了这个国家,人们接连染上失明症,只有少数几人得以幸免。政府先是掩盖事实,将患病的人隔离在闲置的精神病院中,而那里越来越不适宜生存,渐渐成了一个暴露人性的盲人国度……
萨拉马戈想,人嘛,先是摔跤,然后会走,再后来会跑,那么,如果在十八世纪宗教与王权窒息人性的葡萄牙,一对社会底层对魔法尚未绝望的爱侣有一天竟掌握了飞行的秘密,他们的命运会怎样?答案是《修道院纪事》。
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为获得子嗣而许诺修建修道院还愿,光凭自己“国王的意志”和几句话语便驱动着整个国家、无数民众付出血肉甚至生命来成就这信仰力量的伟大见证——马夫拉修道院。与此同时,另一项国王心血来潮应允的 “异教徒”的工程也在进行。西班牙战场上失去右手的前士兵“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和拥有看穿事物与人体内部能力的“七个月亮”布里蒙达在宗教裁判所火刑仪式上一见钟情,成为最亲密的同伴与爱侣,他们与“飞行家”洛伦索神父竟一起窥见了那禁忌的、只属于上帝的秘密,在对纯粹的美与创造的追求之中,建造出了真正的飞行器,而火刑柱的阴影渐渐靠近……
如果……会怎样?萨拉马戈自问也拷问读者,今时今日,历史上,人性如何?宗教如何?社会如何?他也负责地回答了:当灾难降临,人们选择对自己的同类做出残忍的举动,实际上这是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的残忍。几乎所有人都成了盲人,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愿睁眼去看世界。人性是如此软弱,社会是如此荒诞,权力的腐败、意识形态的滥用、偏见、局限、虚伪不会消逝,历史会不可思议地循环,也许绝望,我们要看到真相。
今天,在他逝世九年后,即使我们觉得世界还是如他想象的一般糟糕,但多亏了萨拉马戈,我们得以从那一片白色的盲目中暂时恢复视力,看看周遭,看看自己。
Obrigado, José Saramago.
谢谢,若泽·萨拉马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