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的魅力
来源:光明日报 | 王干 2019年08月23日07:36
20多年前,我和高晓声住在南京肚带营18号的同一个单元里,他住201,我住501,我们在楼道里经常见。他因身体原因被抽去了三根肋骨,所以老扛着半个肩和人说话。我们私下里都称他为“陈奂生”。有一次我口误称他为“陈先生”,他也没有生气,自嘲道:“都当我是陈奂生啊!”作家和自己笔下的人物被人混为一谈,应该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说明这个人物的魅力很不一般。
陈奂生是高晓声笔下的一个小人物,这个人物最早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漏斗户”主》当中,但“扬名”却因《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不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大人物,也不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英雄,而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胆小软弱而又怕事,但他却深深地镌刻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在梳理70年的文学史时,眼前始终会闪现这样一位农民:“‘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陈奂生上城》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
《陈奂生上城》是一篇短篇小说,篇幅也不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陈奂生屹立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且光彩熠熠呢?他的魅力何在?时隔40年后我们来探讨回顾一下其间的奥秘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是人物的魅力。文学是人学,人物是文学的根基,也是顶梁柱。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各种思潮和流派不断演绎,各种手法不断更新,但文学塑造人物,尤其塑造典型人物的使命至今不可动摇。当代文学史能够留下的伟大作品,无一不是拥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人物形象,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路遥笔下的高加林、王蒙笔下的倪吾诚等,都是融合了时代特征和艺术个性的“这一个”。农民形象的塑造一直是现当代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从鲁迅开始,几乎所有的重要小说家都写过农民,因而留下了非常富有个性的农民形象,从闰土、阿Q、祥林嫂,到小二黑、三仙姑,再到梁三老汉、高加林。高晓声在传承五四新文学的文学传统基础上,又写出了新时期农民的心理特征。我在1988年发表的《苦涩的“陈奂生质”》一文中将这种心理特征称之为“陈奂生质”,“‘陈奂生质’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封闭的农业社会特定的文化基因传给今日农民的一种不健全的人格品格,也是中国农民复杂心理素质的复合体,它是苦涩的,也是辛辣的,它是冷酷的,也是温馨的,它构成了高晓声小说的整体精神脉动。”在《陈奂生上城》中,这一特性表现得尤为明显,陈奂生忠厚本分,不作非分之想,不求非分之财,碰到新的不适应的事情往往以一种阿Q的方式面对。陈奂生去看地委的吴楚书记,没想到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来,一个晚上花了五块钱的“大宗支出”,让他心疼。为了让这五块钱花得不冤枉,陈奂生变着各种法子糟蹋房间里能糟蹋的物件,但仍然感到亏了,忽然想到见识了吴书记的小轿车和五元一晚上的高级房间这些“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小说的结尾写道:“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高晓声把这种自尊自慰的精神胜利法以定格的形式放大以后,在冷幽默的同时传出了苦涩的讽刺和委婉的悲哀。高晓声无疑是当代作家中最有鲁迅精神的,但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高晓声那里变成了“怒其不幸,哀其不争”,他对农民的苦难是愤怒的,但对农民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又深深地感到悲哀。小说人物的塑造其实是凝聚着作家的主体精神气质的。高晓声多年生活在农村,与农民打成了一片,他的很多思维和农民之间其实是零距离的,因而人物身上浸透了他的血肉和灵魂,陈奂生一段时间也成了高晓声的另一个躯体,所以他后来又写了《陈奂生出国》等与他个人生活阅历同步的系列小说,这是某种“非虚构”,也是情感经验的自然流露。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高晓声的陈奂生在更多的时候也变成了陈奂生的高晓声,这种人物与作者的互文关系,也增加了人物的含量和覆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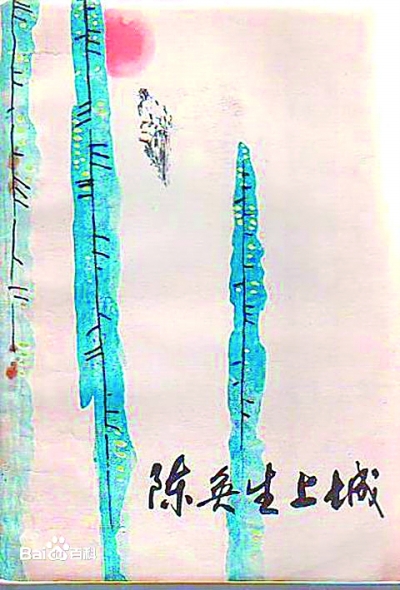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小说选,收入《陈奂生上城》并以之作为书名
其次是乡土的魅力。乡土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富矿,无论是多年以前旅居中国的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还是后来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这些在世界文坛获得巨大荣誉的作品都源自中国的乡土。乡土小说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刘恒、阎连科、迟子建等都是描写乡土的高手,高晓声自然也是乡土小说大军中的佼佼者,他的《陈奂生上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还没有来到之际,就率先写到了农民进城的困惑。陈奂生进城买“油绳”是农民最早进城的一种方式,也开启了千千万万农民进城打工的先河。陈奂生面对沙发这个“怪物”产生的困惑,在后来的作家笔下又换成了其他的“怪物”,城市和现代文明接纳了大量进城的陈奂生尤其是陈奂生的儿孙们。每每读到,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当年的陈奂生的身影,仿佛他依然在打工的现场,或在返乡的路上。这篇小说虽然写于1980年,而中国农民进城的人潮出现在1993年之后,但高晓声的这一小说模式没有过时。《陈奂生进城》依稀可以让人看到“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的痕迹,虽然木讷的陈奂生和能说会道的刘姥姥之间缺乏性格上的有机联系,但农民骨子里的某些东西在曹雪芹和高晓声的笔下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因为高晓声的小说扎根于中国的乡土大地,接通了生活的地气,所以后来上演的种种农民进城的悲喜剧都显得像《陈奂生上城》的“续编”。反过来说,乡土也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只要在它丰沃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就会带着乡土特有的气息和韵味,哪怕年轻的作家没有接触过、研读过高晓声的小说,乡土的力量也会自然地让他们向这样的经典看齐。
再次是写实的魅力。上个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曾经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但历经各种浪潮之后,风轻云淡,留下来的还是那些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写实作品。80年代末期《钟山》杂志发起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第一辑中就收有高晓声的小说,当时我没有觉得高晓声是“新写实”的代表性作家,只是新写实的边缘而已,如今我在写作本文时,重读了《陈奂生上城》,意外地发现这个短篇具备了“新写实”的全部元素。首先,小说符合新写实原生态的还原美学特征,陈奂生进城的过程近乎实录,以至于这篇小说发表以后《人民文学》要讨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因为这篇小说和当时的一些主题明确的小说不太一样,它写了陈奂生的生存状态,人物的生存状态就是小说的主体,这和“新写实”是不谋而合的。其次,作家叙述时采取了近乎“零度叙述”的客观姿态,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但又是从陈奂生的视角进行叙述的,避免作家主观情绪的介入,呈现出某种情感零度的可能,这也是当时的评论家找不到“主题”的缘由。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牵强?其实很多文学流派并不是开创性的,都是以前存在的文学元素的综合和放大,新写实也不例外。《陈奂生上城》之所以历久弥新,超越当时的写实主义,肯定具有某种超前性。

199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陈奂生上城出国记》,收入高晓声创作的“陈奂生系列”小说
有趣的是,1996年我应《文艺报》之邀,为“重温经典”写了一篇《难忘陈奂生》,文章最后,我写道:“高晓声写完陈奂生系列之后,便可以搁笔了。”这本身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没想到有好事者认为我对高晓声有什么意见,去高晓声那里打小报告。过了几天,我在《农民陈奂生》的电视剧策划会上遇到高晓声,他说:“王干,你最近写文章说我写完陈奂生就不要写了,是不是?”我当时一愣,以为老先生不高兴了,没想到他又哈哈一笑:“写完陈奂生是可以不写了,可还要生活啊,活着就要写作,你想不让我换稿费,是不是?”
果然很陈奂生啊。
如今,斯人远去,斯文流芳。
(作者:王干,系评论家,《小说选刊》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