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赵霞的儿童文学研究:艺术眼光与学术勇气
来源:文艺报 | 刘秀娟 2019年09月20日0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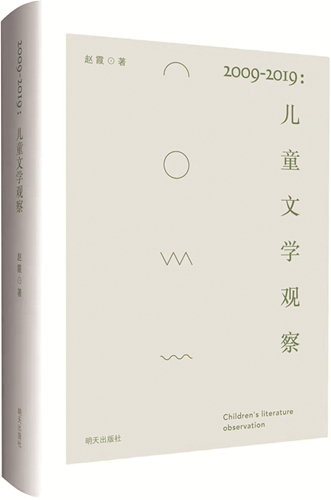
《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9月25日,与新中国同龄,今年迎来了70华诞。赵霞的文集《儿童文学观察》,就是要以一位年轻作者的立场,向一份历史积淀深厚的报纸,表达敬意与谢意。这些文章是一个青年学者10年研究与成长之路的履记,同时也是《文艺报》发现和培养青年学者、坚守“儿童文学评论”园地的见证。正是从《文艺报》开始,赵霞开始释放她积累多年的学术准备,以扎实的学识与敏锐的观察,以她特有的笃定与自信、羞怯与谦和,成长为儿童文学研究界令人惊喜并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学者。
赵霞在《文艺报》亮相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当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难度》。这篇文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宏观又精准,我甚至有点隐隐的激动,在当时话语疲弱、人才断档的批评环境中,她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让人欣悦,长久的地下储备给予她充沛的面向未来的力量。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建立起一种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即便在今天来看,10年前的这篇文章对于儿童文学批评仍然有很强的启发性,她所提出的问题既是当下性的,也是长期的问题,如若不是,也称不上是难题。从这个角度而言,10年的时间倒是给了我们去评断一篇文章的预见性、穿透力和有效性的恰当维度。
她提出的第一重难题便是无可逃避的商业语境对儿童文学批评的挑战。围绕儿童文化商业化的趋向,《文艺报》组织了一系列文章,王泉根、刘绪源、郑重、杨鹏等几位师长,包括我本人,都参与了这场争论。这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个叫赵霞的女孩一直在观察、思考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且犀利地指出,这场讨论,虽然热烈,却并没有进入理论交锋。赵霞虽然没有在当时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但是却在2009年的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触及根本的问题——商业语境,并且先见地做出笃定的判断:“这种语境的变化甚至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撼动着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价值评判体系,也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面貌和未来命运。”10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赵霞的判断,既为她的研究能力所折服,又为我们没有重视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改变而遗憾——到今天,这样的现实已经昭然若揭,无需遮掩。商业语境对于创造力的释放、对于文学评价标准的撼动,甚至对于作家和研究者文化使命的挑战,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越来越清晰的现实。
当我们敏捷而迅速地转向其他热点时,赵霞沿着这个方向深挖了下去。2015年,她出版了《童年的文化影像》,2017年出版了《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在儿童文学、童年文化、消费现象、视觉影像、新媒介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也是将西方文化研究成果和方法实践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虽然在学术界也一直有对泛滥的文化研究之有效性和工具化的反思,但对儿童文学来说,文化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也是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与“主流”学术研究始终缺少对话、难以平起平坐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在文化研究的视角之下,不存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隔,无论从童年文化的视角去研究成人文学,还是以社会语境的视角观察儿童文学,都会给我们提供新鲜的切口,便于我们走近这个时代儿童文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特意提及赵霞在童年文化研究上的用力,并非鼓吹以文化研究来替代审美批评,事实上,对儿童文学来说,两者不是此起彼消,而是都很薄弱。
赵霞的出场和我们大多数人不同。我们往往循着“单篇作品评论—作家论—现象论—总体性研究”这样一个路子,是从个体到总体的一个积累过程,在持续多年的批评实践和现场介入中我们才逐渐建立起(还不一定是完整的)个人的儿童文学观。赵霞恰恰相反,她并没有过早地介入儿童文学批评的现场,而是在完成了对儿童文学和文艺学的系统学习,有了整体性认知和把握,有了充足的文本阅读之后,才进入到批评现场,尤其难得的是,她一直保持着对美国儿童文学研究刊物的系统阅读与思考,她的知识结构、视野、方法足以支撑她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现状进行整体性的判断。越是从她早期的文章中,越能发现她的宏观性,发现她的学术勇气与野心——在她性格所带来的温和与周全叙述当中,仔细阅读,会发现她观点上的尖锐性,她其实是带着对现状的不满而立论的。比如在2010年《历史·现实·本土——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走向的思考》中,她提出了儿童文学批评如果不能将捕捉热点现象的热情有效转化成系统的、翔实的、周密的研究论文,儿童文学批评会在这样轻浅的滑动中,日益损耗着自身的理论能量。她还提出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儿童文学长期被视为“小儿科”,和儿童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整体水准较低有关系,理论批评在作品的“经典化”路径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赵霞的参照是《小红帽》《海的女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地海传奇》等西方作品的经典化之路,其实如果我们拉近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对我们的激励作用更直接。再比如,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她提出,新时期以来,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足够重视的问题:我们的童话写作承接和发展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童话幻想传统,却无法对应现代童话背后那个深厚的精神基底,这导致了当代童话在熟悉了现代童话写作的基本门径之后,却长久地徘徊在幻想技法的反复演练上。“在今天的一部分童话写作中,我们不难看到,随着童话的幻想被不断地精致化,它朝向现实的面孔也在不断地虚化,许多充满灵光的想象和语言,却始终切不到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深处。”这是关于当下童话(包括幻想小说)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精辟之见。
赵霞一直有种期待,就是学术研究与批评实践的相互支撑。她自己会有意识地针对作家新作进行文学内部的研究,侧重审美批评与文本细读。这部分文章中,虽然对黄蓓佳“5个8岁”系列长篇小说的评论发表时间更早,但更接近她批评理想的是对刘海栖《扁镇的秘密》的批评。在《当代童话的叙事革新与困境》中,她很有冒犯精神地对我们的师辈作家刘海栖童话的现代性探索进行了得失之辩,毫不扭捏地指出这部童话在艺术探索上,大量借用西方作品为潜在语境,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陌生而无效的经验,同时,它在后现代手法的使用中消解了意义,而没有重建起自己的价值。赵霞的勇气值得嘉许,但更让我感动的是刘海栖老师的宽容,无论对作者,还是对编辑。
在从事研究的同时,赵霞也开始了散文写作。虽是她的另一副笔墨,却始终围绕童年命题,其实是她研究的另一个入口,来自自我经验的、现实生活的入口。散文里的赵霞,细腻敏感,对童年生活、儿童心理有很强的感应能力和同理心。尤其是做了母亲以后,赵霞有了更丰富的、直接的童年感受,既有普通妈妈那种天然的幸福与沉迷,也多了一个直接的、耳鬓厮磨的研究与实践对象,这种爱与关切会触动她写下更多美好的作品,也会启发她更开阔的研究思路。
在散文《卡夫卡和小女孩》里,赵霞曾经写到,卡夫卡和小女孩这段传闻无论有多少个版本,但它始终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文学——以及以文学为代表的整个人类文化——对于孩子这样一种微小存在的深深关切。因为这种关切,“1923年的卡夫卡,怀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虚弱与绝望,走在柏林的街路上,他看见了一个孩子的眼泪。”这同样是赵霞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核心,也是我们所有热爱儿童文学、关心儿童文学的人们的核心——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时常自问与自省,最初的热爱与关切还在吗?我们的内在驱动力是否蜕变?
资本和媒介对儿童文学、儿童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现代化、信息化、商业化、全球化、智能化、贫富两极化、知识碎片化等不同维度的力量交织在我们的生活中,儿童文学研究者如何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发声?这是考验一个学者、一个评论家学术自律与艺术眼光的时刻。赵霞有天分,更重要的是她有执著而坚定的目标。她既是儿童文学一个时刻在场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她又很疏离,疏离于很多热闹之外。她不怕“失去”和“耽搁”,直到今天,她仍能做到不使用微信,起码不用它来进行社交。这是她的自律和自我认知。她不使用不代表她对最新的文化语境、文化传播方式不关心,一部老式的非智能手机并没有阻碍她对最新的媒介文化的观察,她只是比我们更加警惕、更有决心避免“陷入”。这种态度是她对待很多事情的态度,她会把有限的时间精力,全身心地专注于一件事:感受和研究童年以及儿童文学。
和赵霞一样,《文艺报》对我来说同样是启航之地。从2005年开始,我开始担任儿童文学版的编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份职业。儿童文学评论版创办于1987年1月24日,她的诞生得力于束沛德老师等前辈的极力促成,并受到整个儿童文学界的热心支持,冰心老人亲自题写了刊头。30余年来,她曾有过经济上的危机,有过编辑人才的断档,有过办刊思路的调整,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岌岌可危,但是无论处于怎样艰难的境地,《文艺报》都没有放弃她,并且在2010年增设了“少儿文艺”专刊,使得这块园地成为儿童文学界最持久、最稳定、最具风向性、最有凝聚力的理论和评论园地。因此,在她迎来70华诞的时刻,赵霞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这部献礼之作,是替我们所有人道出了心中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