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提醒我们,文学不一定就是日新月异的
来源:澎湃新闻 | 罗昕 徐萧 刘欣雨 2019年10月16日09:02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IC 资料图
当地时间10月14日,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纽黑文的医院去世,享年89岁。他一生出版了40多部著作,代表作有《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如何读,为什么读》《西方正典》《小说家与小说》《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等。
诗人王敖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曾上过哈罗德·布鲁姆的课,在他毕业时候,布鲁姆还给他写过推荐信。“他(布鲁姆)跟我聊过中国诗。他了解过朦胧诗,评价不高,说太政治化了,所以没兴趣。他专门问过我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有没有能够继承伟大的儒家传统的诗人。’”王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布鲁姆是天才加勤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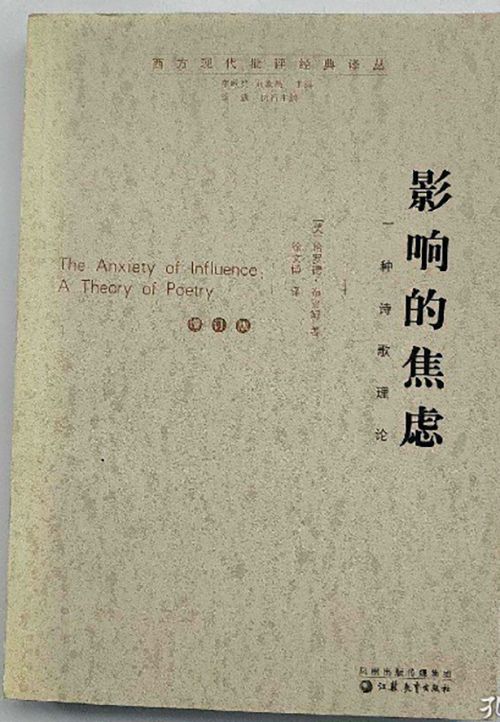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
捍卫最原初、最奠基性的文学理想
在作家弋舟眼里,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个比较偏向老派的文学批评家,但恰恰是他身上那种老派的气度,与今天“求新、求变”的文学观形成了反差,因而更加令人折服。
“他在批评中建构自己对于文学的认知,以强烈的主体性笼罩作家和作品,用一个个文学作家和作品去搭建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比如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姆甚至大过了莎士比亚。而我们今天的批评家更多的是被作品笼罩。”
“他对西方世界文学精神的塑造也值得我们借鉴。”弋舟说,哈罗德·布鲁姆从18、19世纪的文学传统中塑造出了某种极为重要的西方精神。前苏联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与布鲁姆一样,他们身上好像都有某种共通性——塑造着某种俄罗斯精神。“而我们今天还缺乏有总体性、归纳性的批评家。”
“布鲁姆的总体性非常强大,也许他给出的一些结论大家未必能够认可,但他身上那种强悍的力量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那种力量感的来源就是,在我们人类的文学世界里捍卫最原初、最奠基性的文学理想,比如对传统文学精神的强调。”弋舟感慨,但是到了当下,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价值取向实际都在逐渐与布鲁姆所提及的那个西方文学传统分道扬镳。
“在这种趋势之下,我们永远觉得进步是好的。但是布鲁姆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同样要关注 ‘反动’的价值和力量。所谓 ‘反动’,是指文学不一定就是日新月异的,新的不一定就是最有价值、最好的。文学与其他的社会元素不太一样, ‘保守’有时候甚至会成为它的重大价值。”
阅读是解决人类困境的唯一的高效途径
作家鲁敏说:“哈罗德·布鲁姆在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力很大,他大概是我在中国批评家作品中看到被引用最多的外国同行。所以他也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界批评的立场、态度和力量,以及批评家对文本本身的重视。他对文本的尊重在批评家里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如果不透彻阅读文本的话,是绝对没办法做出深度批评的。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严厉,有点刻薄的批评家,既会不遗余力地赞美,也会无比犀利地批评。”
从写作者、阅读爱好者的角度来说,鲁敏感慨哈罗德·布鲁姆在阅读方面简直是神。“他自称 ‘阅读狂魔’,据说他一小时最高纪录可以读400页。他特别喜欢莎士比亚,甚至还有 ‘能把《莎士比亚全集》只字不错地记得’这样的传奇。传奇可能有点夸大,但足以可见他不仅阅读高速,还有博闻强记的能力。”
鲁敏最喜欢布鲁姆的一句话是——“我们阅读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够多的人,而是因为友谊是如此脆弱,如此容易缩减或消失,容易受时间、空间、不完美的同情和家庭生活及感情生活种种不如意事情的打击。”
“他觉得阅读是解决我们人类孤独、隔阂以及文明堕落的唯一的低成本又高效的途径。我希望今后不管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他对阅读的这么一种基本态度会一直延续下去。”鲁敏说。
思考他作为一名文学教育者行动本身的意义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魏朝勇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等作品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到大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学界关注是因为他和所谓的解构主义捆绑在一起,但他本人对于流行的各种理论口号是不屑的,是不合作的。尽管他在学界广为知晓,但学界没有真正对待这个人,这个个体。比如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引进中国,并没有引起中国学界像他那样去重视西方经典。大家更多对名号感兴趣,而不是 ‘重视西方经典’这种行动本身。”
“在哈罗德·布鲁姆的生涯里,阅读第一,教学第二,写作第三。但是在中国,我们更鼓励论文发表,经典阅读教学在文学专业领域里素来重视不够。所以在这点上,我认为哈罗德·布鲁姆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思考他作为一名文学教育者行动本身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表示:“作为作家,我们纪念他对文学的信心,尤其是相信文学在处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时所表现出的不可代替性;作为读者,我们纪念他为传播文学经典所做的贡献,也纪念他在批评中所表现的感受力、想象力与同情心;作为研究者,我们纪念他为文学批评这一行业所建立的标准,即不管我们抱着何种诉求从事批评,都必须对浩瀚辉煌的文学传统表现出最大的尊重,不以某一立场代替快乐的、不知疲倦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