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君:爬格子的意义
来源: 天天出版社 | 秦文君 2019年10月17日08:21
9月26日上午,第四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亚洲大洋洲地区会议在西安开幕,来自中国、蒙古、印度、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尼泊尔、日本、阿富汗、俄罗斯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少儿出版界人士,以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会委员近200人汇聚一堂,共议“儿童与未来”主题。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童年体验”分论坛上,金波、曹文轩、秦文君、白冰、徐鲁、董宏猷、王宜振、汤素兰、薛涛、陈晖、吴梦川、横田纯子、穆尔特·布楠塔、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桑丽莎等中外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评论家、出版人在论坛上发言。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秘书长伊丽莎白·弗朗西斯·佩吉等IBBY执委出席,IBBY中国分会主席、中少总社社长孙柱,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齐雅丽在活动中致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担任本次论坛主持,并在总结中充分肯定了论坛的学术水准,衷心期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孩子变得更快乐,让作家画家们的作品更接地气、更有魅力、更有冲击力,让全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为全世界的孩子们搭一座美好的、辉煌的文学大厦。”
爬格子的意义
秦文君

我投身儿童文学事业时间不算长,四十年左右。比起前辈差很多。
为何能四十年坚持,是因为儿童文学是孩子寻找美,寻找幸福的百科全书——世上超越物质和功利的是信念和创造,儿童文学给人这样的光辉 。
更何况,儿童文学作家这个职业,大有乐趣,忠于独创,写出东方情怀,写出有意思的文本,看着出版社将它们变成活泼的书。但是更有一种无形的责任,需要不断地折腾,在艺术上超越自我, 往往会一个人关在封闭的小屋子里,面对一面墙,孜孜不倦地写作。有了这一份对文学的痴迷和热爱,不然如何抵抗寂寞和惰性,抵抗无数诱惑的定力?
努力在儿童文学艺术创造领域跋山涉水的,向往写出精品力作的作家,无疑都是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爬格子的人,而不是跳格子。
从1982起,我出版了70多本书,获各种奖也是有80次,虽然现在用电脑了,在我心里,还是把写作叫“爬格子”。
当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普通的稿纸是方格的,每一个字写在格子里,一笔一划地勤恳耕耘,一格一格地爬格子。我最向往的生活是爬一辈子格子,所拥有的是笔,深度的眼镜,清贫的生活,一屋子书,但从不会松懈过,没有失去爱和勇气。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市场好,作品多的作家脱贫了,有的成为纳税大户,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但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社会风气功利化,作家自身的坚守很重要,能呵护美好的姿态,维护独有的价值,在多元文化时代的选择中,保持高雅的追求,沉下心,保持内心强大的宁静。
关于儿童文学是儿童重要,还是文学重要,这个争论从没有结束过,我想 其实都举足轻重。一个作家的造化,不是单一的,取决于作家对艺术的态度,取决于心灵家园是否丰富,艺术的造诣能否上去。而作为儿童文学作家,除了种种文学的创造能力,叙事能力,对人的描摹,情景描写,价值判断,美感,语言魅力,还要有对儿童叙说的举重若轻的能力,要有一个大有难度的综合能力。
我希望因为内心强烈的创作冲动而去爬格子,我2019年出版的《云三彩》就是一部慢慢积累而成的作品。

二十多年前我就已对这一题材产生浓厚的兴趣,那就是外来的女孩。我想要表达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城镇化对于女性的解放,因此,《云三彩》的故事着重展现小女孩李三彩的个人解放和心灵开放。
城镇化的过程必然涉及到人的迁徙,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迁徙到充满隔膜和距离感的都市空间,乡村社会结构和生活环境,比如多数农村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对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灵,观念都有着一定的束缚,而城镇化的迁徙过程对于女性来说,就像是从“潘多拉魔盒”里面被释放出来一样。
书写儿童,要根植于儿童的心灵世界,视角,审美,更要根植于社会,人性,探讨无限的可能性。
初到上海之时,三彩在学校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在家庭中,她的父母将一腔热忱都倾注于弟弟身上,她因而缺失了父母之爱、手足之爱和朋友之爱。在上海这个形形色色、你来我往的都市空间中,三彩与爸爸、妈妈和弟弟之间的隔膜,与同学、老师和社会人际的隔膜,促使她的内心世界产生了质的变化。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社会空间中,三彩带有“女侠”的个性和特质,有着对于自我身份的明晰认定,但她作为外来者,面对社会的转型,城市中的现代生活,现代服务业的兴起,必须要融入城市、理解城市,因此三彩进入城市空间以后需要做出许多改变。
上海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花费了较多的功夫,我曾经在面对每一个采访对象时抛出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次从家乡来到上海,什么感受让你觉得最为深刻?”因为我想去了解外地迁徙而来的,特别是农村来的孩子,他们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印象,这可能是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无法体会到的。
我记得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饮食,有人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传说中的豆浆、油条,有人说第一次到上海吃的是进口的橡皮糖,也有人说在上海第一次吃蛋黄不烧熟、可以用吸管吸食的煎蛋,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就像一脚已经踏进上海来了一样,生活方式突然间变得洋气了。
我收到过一个读者的来信,这个外地的男孩子来到上海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对于上海很熟悉,原因是他当年看到过我写的“贾里”系列里面的一本书《小鬼鲁智胜》,这本书虽然没有刻意去描述上海的风土人情,却让他从中感受到了上海的风情和三教九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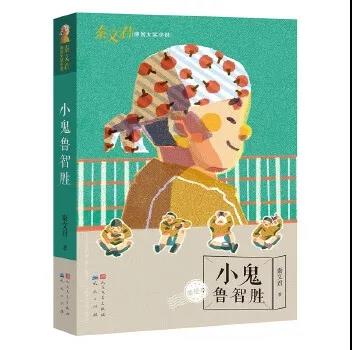
我还曾经到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女性家中去采访,从外表上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上海化的女性,无论是她的上海话,还是做事、穿着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风格。直到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在家做了一盆“乱炖”,突然意识到她虽然想融入上海,但是内在的基因还是更喜欢自己家乡的饭。人不可能完全脱胎换骨,也不需要脱胎换骨,一样也可以融入这个城市,这就是上海。
回想起来,图画书文本《我是花木兰》也是根植于童年,显现社会新形态和传统文化力量共存的社会。它是个女孩成长,东方审美的作品,落笔写被很多人诠释过的,存留心灵深处多年的人,更是一个挑战。期间我不厌其烦地找了100个孩子,请他们说说心目中的花木兰。精准把握当代儿童的审美视角和语言叙述。在我选择用什么艺术形式表现花木兰的时候,一个新鲜的念头冒出来,能不能让1000多年前的花木兰和现在的孩子有对话,用新颖的双重视角,双线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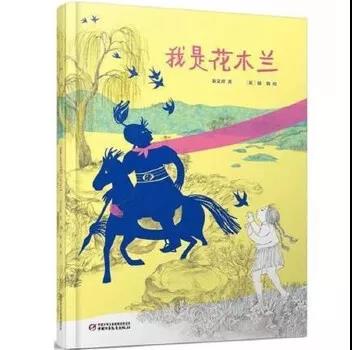
有了当代儿童的视角和审美,还必须有历史视角和文学陈述,艺术造诣,忠于当年的社会风情和文化关联。我去荒漠,古战场,山川,体验花木兰上战场的感受。很多遗迹已消失,去甘肃,河南的一些地方,从不断挖掘出来的铁甲,兵刀,长矛,能推断这里曾是无限空旷的古战场,如今只能看见生生不息的小花小草。我在那无限空旷的地方,看飞鸟的影子,浮动的云彩,从浮想联翩,升华为文化想像。
北魏时期的,民风是比较开放和彪悍的,木兰家乡的妇女都会骑马,射猎。为了探索花木兰的特质和天性,我还尝试从富有特色的地方戏着手。我信赖花木兰的家乡人,她们用豫剧演绎花木兰。即使是豫剧,还有细分。公认的木兰故里,河南商丘虞城县一带所唱的豫剧和常香玉老师唱的豫剧不同,是豫东调,吸收大量的山东梆子唱腔加以融合。听着豫东派马金风老师的演唱,行腔冼练、轻盈明快、俏丽活泼、字多腔少,在其代表剧目《花枪缘》中有显著表现。我从这些声音里能推想花木兰的面貌了,还有干练的口音和嗓音。
女孩成长的无限可能性,丰富性, 在我脑海中闪现,永远不会湮灭。花木兰美好的人性特质,不因为战争而湮灭。我仿佛触摸到花木兰令人心颤的气息。
《我是花木兰》用了一个双重的构架,既有古老故事的叙述,也有当今女孩的心语。文本最后的一些文字,是文本的魂:一起从军的铁哥们儿来看她,花木兰悄悄避开,嘱咐弟弟陪他们玩。铁哥们儿未必知道,久战沙场,军功累累的“木兰兄弟”,是个女孩。而在另一条线,当代的小女孩对性别却有不同认定,从中感悟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最近得知,《我是花木兰》即将要在美国,日本,英国出版,我感到自豪。
作品的写作过程是心灵开放的过程,长久以来,我都对于女孩成长非常感兴趣,女性的迁徙中蕴含了很多话题,也能生长出丰富的悲欢离合。
爬格子是忠于独创的,严谨而艰难,也是坚持自我,探索写作的无限可能性的过程,让一种勃勃燃烧的精神内力永远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