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岭的天空》:童年记忆和“孩童的宇宙”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李红叶 2019年11月05日0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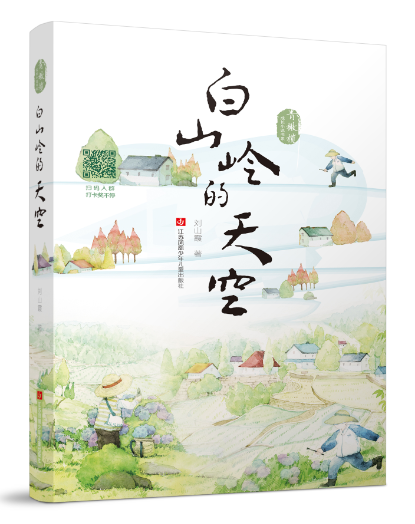
《白山岭的天空》,刘山霞/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26.00元
孩子们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在每个孩子的内心,都存在一个宇宙呢?它以无限的广度和深度而存在着。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充分讨论了童年的“根性”本质,强调童年并不是在完成它的周期后即在我们的身心中死去并干枯的东西,它深藏在我们心中,它是我们的根性,是生命的原型,是活力的宝藏,并向我们传达出一种植物性力量——“在缓慢的书写中,童年的回忆一一舒展开来,静静地呼吸”。我在刘山霞的童年书写中也感受到这样一种“静静的呼吸”。其文字质朴真诚,直抵内心,并传达出一种加斯东·巴什拉所言的植物性力量。
刘山霞将她的写作视为一种自我“疗愈”。她“疗愈”的不只是她自己。任何人在阅读这样真诚而充满生命律动的文字时,都将是一种“疗愈”。当她每天凌晨五时以写作开启她新一天的生活时,她的周遭世界看似如此安静,实则自然万物也陪同她一道醒转,处处是新鲜的生命。她在电脑前静静敲打,“让记忆中的白山岭一点点来到我的文字里”,她体会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当她终于在字行里安顿了她的童年记忆,她忍不住在后记里写道:“我到过很多的地方,看过很多的山山水水,可是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白山岭。”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永远的“白山岭”,念及它,我们看到的,“是童年的自己”。
回忆性童年书写的意义并不止于使流逝的、不可逆转的童年再现——事实上,我们无法重回历史现场,回忆必定是当下与历史对话的结果,并成为一件充满意义追问的事,因此,追问什么、如何追问便成为写作的重要议题。
随着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的入侵,现如今的白山岭早已面目全非,正如刘山霞在小说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曾经热闹的老屋已经萧条得不成样子,阿婆和嗲嗲坟头的草都长成了一座小山,曾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也都纷纷离开”。刘山霞的笔力并未停留在物是人非的慨叹上,她把记忆中的童年独立出来,那个隔着时空而愈发清晰的童年便以令人惊讶的姿态出现在纸面上。从前人事间的脉络经由成年的“我”的抚摸,恰如溪涧卵石,溪水经年流淌,石子们一律变得温润而安静,并散发着淡淡光辉。
刘山霞文字的最大特色便是悲悯情怀,她透过纷繁琐事看到的是人心的柔软处与脆弱处,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人心的柔软处与脆弱处,以及复杂而活跃的生命力,不但在成人身上体现出来,也体现在孩童身上。刘山霞把这一点写得细致而透彻,令人心生感动之余,对生命之悲苦与欣悦及其辩证关系产生更深领悟,也对生活本身产生更深的爱。
小说以孩童秀珍的眼看世界,看白山岭人的各种人事变化和喜怒哀乐,着重写了阿来、俊宝及秀珍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以及与秀珍的生活相交集的麦婶的人生故事。正是这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构成了白山岭记忆的全部。刘山霞想要告诉人们的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不容易的,每一个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困境和苦难,因此善待、谅解和接纳就变得尤其重要。而对于个体的成长而言,她也借由她的小说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成长的路,要相信善良的力量,爱的力量。
刘山霞是一个触摸到孩童生活最深处的人。她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阿来、俊宝尤其是秀珍的内心生活,这是小说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加斯东·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中多次使用“童年的宇宙”一词,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其著作《孩子的宇宙》中一开篇即谈到:“孩子们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在每个孩子的内心,都存在一个宇宙呢?它以无限的广度和深度而存在着。大人们往往被孩子小小的外形所蒙蔽,忘却了这一广阔的宇宙。”两位学者在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指出一个共同的命题:孩子的内心世界之大。我们在刘山霞的笔下看到了一个个敏感幼弱而深富理解力的孩童世界。
孩童的孤独比成人的孤独更隐秘,更持久,尽管它也更易被释放,被疗愈。孩童的感受力如此强大,他置身于人际关系之中时,他又是如此弱小。传统习俗和传统观念往往忽视了一个孩子的精神生活所能够达到的强度。因此,秀珍的哭声无法真正抵达妈妈的耳际;对阿来来说,虽说随着生活谜底的揭开,及身边人尤其是新妈妈的关爱,阿来最终与现实和平相处,并心怀感激,但阿来曾经的无所适从,曾经的挣扎,以及最后他与生活的和解,这一过程却是发生在个体内心深处的事。而不得不接受妈妈改嫁的现实,以及被动、孤立的处境使得俊宝对于新爸爸所做的一切有着更隐藏也更含蓄的领会,因而当亲生爸爸接他到城里上学时,他坚定地选择和妈妈及瘸子葛叔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刘山霞对现实真相的尊重,对个体的人的内心情感的尊重,尤其是对孩童内心世界的尊重。
小说中的秀珍的原型就是作家本人,因此可以理解刘山霞为什么能够把秀珍的心思写得这样真切。秀珍的敏感,秀珍的倔强,秀珍对阿来哥哥的依恋,对阿来和俊宝的同情,对麦婶的由敌对到温柔体贴的情感变化,尤其是对妈妈的情感变化,无不情真意切,无不抵达人性深处。然而,作家的悲悯情怀绝不止于对主人公秀珍的描写,她对另外两个重要的孩童形象阿来和俊宝,都有非同一般的理解力。而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永远是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因此也就看到了作家对于一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所怀有的理解力和感情。秀珍、阿来、和俊宝,连同秀珍大姨(也即阿来的新妈妈)、阿来爹、俊宝妈妈、葛叔(俊宝新爸爸)、麦婶、秀珍妈妈,等等,每一个人都有其自身所处语境下的情感疙瘩,都期待被理解。那些顺生活之流产生的情感纠结,也将顺生活之流抵达释然之彼岸。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善良,是爱,是耐心等待。
秀珍、阿来和俊宝,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体验着缺失感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他们最终的精神安顿和精神成长既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力量,也来自于成人世界的关怀和爱。家庭的残缺,无论是现象意义上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是重大事件。小说中的成人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这种耐心突出地表现在阿来新妈妈对阿来的情感等待及俊宝新爸爸对俊宝的呵护及尊重上。秀珍走近妈妈看似简单却走的是一条更曲折的路。秀珍对妈妈的理解相比较于阿来对新妈妈的接受以及俊宝对新爸爸的接受,也有着更普遍的意义。秀珍的障碍来自于误解,是偶然性的,因为秀珍对自己曾有个哥哥而爸爸妈妈在有了哥哥之后还期待有一个女孩的事实缺乏了解。她从种种迹象中看出,妈妈更爱的是弟弟(她的敏感使得她忽略了弟弟比她更小更需要照顾这一事实),而愈生分壁障愈厚,爸爸又长期不在身边,小小的秀珍因此陷入孤绝之中,她难以倾诉,无法言明,又无可排解。唯有当她了解到更多事实,也接触到更多人事,并能够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她的妈妈时,她那小小的郁结的心方才得以释怀。尤其是当她享受过妈妈不在身边的自由,继而重新期待与妈妈在一起哪怕听妈妈骂她时,她终于体会到母子之情的真正含义,并能够由此而更懂得爱他人,理解他人。啊,孩子内心的宇宙是怎样深邃而浩瀚!刘山霞对于孩子世界的描写以及对孩子与成人之间的互动所表现出的理解力和悲悯之情,的确是童年书写中的一个典范。
长大原是不期然而然的事,长大又是多么可以期待的事。刘山霞想借这个故事告诉孩子们,人来到世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要珍惜爱并爱人;同时告诉孩子们,不要害怕成长的路,一切苦难都会过去,一切误解都会被消除,一切的伤痛都可以被接纳,被原谅。刘山霞用温暖的目光守护着孩子们并激励孩子们向前去。同时她的写作也是一种自我倾诉,童年以它特有的方式给了她无尽的慰藉和力量,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真的离开白山岭了吗?原来无论我走多远,我曾经在白山岭感受过的善良和纯朴,一直都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