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门写作
来源:中国作家网 | 谭健锹 2019年12月23日08: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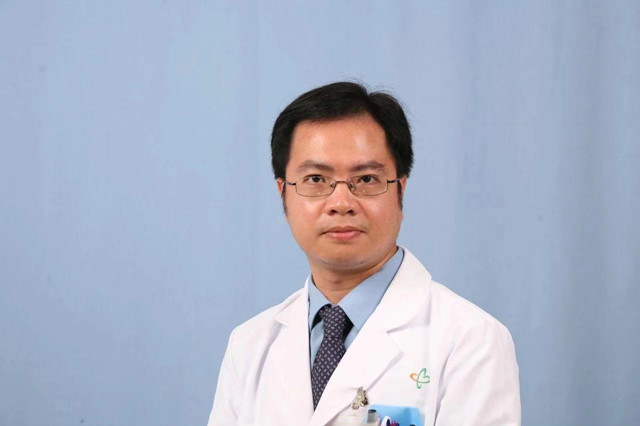
谭健锹,男,生于1981年,广东新会人,现居澳门,中山大学心血管内科硕士,中山大学自考汉语言文学本科。澳门镜湖医院内科医生,《澳门日报》专栏作者,爱好文学与历史,著有作品《炉石塘的日与夜》《病榻上的龙》等。
十年前的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与澳门的缘分越结越深,无法想象自己也能坐在澳门文学这艘大船上驶向深蓝。那时,我刚从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前方彷佛只有一条路。
改变源于十年前的一次盛会。
2008年底,我还在新会人民医院上班,偶然看到信息:
为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澳门举办“澳门之歌”歌词创作大赛,参赛者地域不限,优秀作品将有机会被谱曲传唱!
我心中不是没有文学种子,只是比较幼稚和粗糙。学生时代比较喜欢古诗词,也尝试写过几首歪诗,仅此而已。不过,宋词的韵味一直在我灵魂深处回荡。至于澳门,我是去过两三次的,一些景观和历史还在我脑海中萦绕。
兴致就是这样,像头莽撞的小牛犊,奔起来连老虎都未必拦得住。我凭着对柳永《望海潮》的喜爱,模仿其格式,写了首仿古的作品,把莲花之城的景色与人文历史糅了进去,字数和组段类似原作,可押韵只会用普通话的韵母,当时并不知道,作古体诗词,押韵要压“平水韵”,字与字之间还要讲究平仄关系。就是这样一首“赝品”,却承载了我对澳门最早的美好印象和祝福。
作品发出去了。我权当只是游戏,并未期待有什么收获。医疗工作依旧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偶尔,澳门大三巴门外凭高远望,雪浪共云,妈阁烟漠,松山叶飘,城阙苔驳;漫步街区内,岗顶弦歌,卢园粉蝶,粤海商街,欧陆香榭,这些美妙却与内地似又不似的景观,在我心中的涟漪里荡漾。而《七子之歌》的旋律,就是历史和现实的珠联璧合,这首歌就是澳门之魂!
农历新年刚过,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说作品得了入围奖!主办方还邀请我去澳门参加颁奖典礼和观光。
带着莫名的兴奋,带着春天的盎然气息,我再次来到澳门。原来,获奖的作者来自全球各地,内地选手固然济济一堂,而海外华人也颇为踊跃,有的不远万里从南美赶来。这次聚会,比起兰亭雅聚毫不逊色,而内涵则高远深邃得多。
席间,一位儒雅的女士坐在我的右手边,五十岁上下。她戴着硕大的眼镜,留着一头精干的短发,脸上淡淡的皱纹让我觉得她阅历过人。她关切地问起我来自何处。我说,广东新会。她先是一惊讶,继而又一喜,说自己也祖籍新会,想不到在一个陌生人云集的场合也能轻而易举地碰到乡亲。
“你的广州话讲得真好,一点乡音都听不出。”她夸到。
我心想,我们都是看纯正粤语节目长大的,课堂上的授课不是普通话就是粤语。相反,地方方言是讲得越来越不地道了。或许,这位女士最期待的是那远去的乡音吧。
她递来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汤梅笑,《澳门日报》副刊编辑。
我谨慎地接住,收于怀中。当时我并不知道,收起的居然是一段难以割舍的缘分!那一天,我称呼她“汤女士”,或学澳门人的习惯称之为“汤小姐”。“汤女士”鼓励我多动笔,多来澳门看看,虽言简意赅,她还欢迎我写了合适的作品,可投到《澳门日报》。那时候,我没想过自己还能写什么,除了这些不伦不类的仿古诗歌。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往后的日子即将与澳门同甘共苦,我更不知道的是,她在澳门文坛还有更响亮的名称——林中英,“笑姐”才是文化界人士不管年纪大小,对她的统一尊称!
一年之后,机缘巧合之下让我把工作地点转移到濠江,这里是香山故地,与同是侨乡的新会也很近,却咫尺天涯。或许,他乡的寂寞、无聊,以及对未知前途的恐惧和忧愁,激活了我心中的文学种子。这些种子是父母在我幼小时种下的,他们很早就教我唐诗,我小学三年级就能把许多古典诗歌背诵得滚瓜烂熟,可这种子由于学业分化,又沉睡了十几年,直到际遇改变,才再次有了萌芽的希望。
在初到澳门的那段彷徨日子里,我系统学习了古体诗词的格式规范,尝试创作合格的作品。拙作还真有一两首登到了《澳门日报》的《新园地》版面。一年多后,我喜闻其中一首被收录到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古体诗词组)”。文学创作也跟学医一样,一步一个脚印,艰辛总离不开鼓励。在作品选的发布仪式上,我第二次见到了笑姐,她仍是对文学爱好者千叮万嘱,却忘了我之前与她有过谋面。
此后,我在工作之余渐渐把爱好培植在文学这棵大树上。古体诗词也不再是我唯一抒发情感的渠道,散文写得多起来,之后还尝试过小说和新诗。其实,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但在发之于情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澳门地方虽小,但文学氛围却很浓郁。如果我在内地,也许只能一辈子只能做医生,文学的种子很有可能会凋敝枯萎;而在澳门,这些种子竟终于迎来了晒太阳、吐新芽的命运。虽然我一只手拿笔,另一只手还得拿着手术刀,为谋生而常常彻夜不眠,毕竟在澳门,几乎没有专业作家,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哪怕再笔耕不辍,也得先有一份不至于让自己饿死的固定职业,他们有的来自私企、赌场,有的来自学校、政府部门……但创作的快乐和满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这些年的写作给我一条基本经验,那就是只有融入自己真实情感的作品,才有机会得到认可,凡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篇章,最多只是获得一种虚无的形式美而已。生活永远是艰辛的,磕磕碰碰是小事,波谲云诡的恶浪也不时阻碍着前路,月色无痕,星空有泪,我时常走在岸边,走在树下,走在那些中西合璧的旧居旁,回味着工作与生活发酵出的苦涩,也许这些,才是我的创作之源吧。
种子萌芽后,能否长成树木,除了生活的养分,还需要勤奋的浇水园丁。笑姐,就是这样的“园丁”。
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文学场合见面多了,彼此也逐步加深了了解。我也不时往《澳门日报》投稿,偶有斩获。笑姐从来没有教过我怎么写才好,怎么写才能更容易打动读者和编辑。她大概觉得这是学校老师的职责,她把职责交给现实和或冰冷或火热的社会,让作者自己去发掘去体会去反省。而她最喜欢做的,是嘉许和鼓励,这个做法使她在作者眼中更和蔼可亲,更真挚中肯。
2014年的秋天某日,我忽然接到笑姐的电话,她说期待我在《澳门日报》副刊上承担一个专栏,每周一次,内容主要涉及杏林与历史的趣闻,可用文学给这些“医学散文”加以点缀,详情面谈。
我兴冲冲地来到报社,与笑姐聚了一次,欣然接受这一颇有趣味且有意义的工作。临别时,笑姐手写了两个电邮地址与我。
大概半年后,我在水坑尾偶遇笑姐。她容貌依旧,只是略显疲倦。她说,自己刚从报社荣休了,想改变一下数十年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她还说,希望我继续写下去……
夕阳西下,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然点点头。我知道,她往前走的方向是雀仔园,那是她在散文中无数次书写过的地方,带着她童年的憧憬和梦幻,还有生活的深刻足印。我知道,她的前方永远不会有夕照,因为她的心让她不会衰老。那一年距离我们初次认识,已过了五年,而她实际上已经65岁了!
直到今天,那个专栏我还在写。直到今天,这张写了电邮地址的纸片,我还藏在衣柜的文件袋中。笑姐大概不会说家乡方言,但她无疑是我与文学世界联系的纽带,这早已超出了乡邻、血缘和宗亲的情分。
十年来,在我心中,“澳门之歌”总是不停地唱响,那歌词已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些得奖作品,而是无数澳门人的生活心声,无数像笑姐这样的人,他们的心声——对生活充满着坚韧笃定、对前路深藏着美好期望、对一个个鲜活生命洋溢着珍惜与爱护。
“扬帆十年追梦,听涛声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