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特德·姜 2020年01月21日1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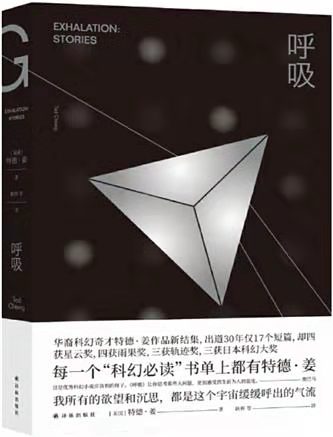
作者:特德·姜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ISBN:9787544779319
呼 吸
空气(还有人称之为氩气)就是生命之源的说法流传已久,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刻下这些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我是如何理解真正的生命之源以及生命最终将如何消亡。这样的结局我们无法避免。
在大部分历史进程中,“我们依靠空气维持生命”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显而易见。我们每天消耗两个充满空气的肺,然后把空肺从胸腔中取出来,再换上充满空气的肺。假如有人不小心让气压降得过低,他就会感到肢体变得沉重,需要补充空气。无法更换新肺导致体内两个肺的空气耗尽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如果不幸真的降临——比如有人被困住了,无法移动,而且旁边也没有人帮助他——空气用完之后几秒钟他就会丧命。
然而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可没有把对于空气的需求看得那么严重。大家觉得,到空气补给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补给站是最主要的社交场所,我们在那里既能补充生命的给养又能获得情感的满足。大家在家里都备有充满空气的肺,可是孤单一人的时候,打开胸腔更换肺似乎成了一件烦心的琐事;但是和大伙一起补充空气却是一种社交活动,一种共同分享的快乐。
假如有人非常忙碌或者不善交际,他只需要在补给站把一对充满空气的肺安装到自己体内,再把空的放在房间的另一边就行了。要是换好肺的人还有些空闲时间的话,他可以把空肺连接到空气配送机上,重新充满,以方便下一个人使用。这个过程很简单,也是一种礼貌的体现。不过最常见的行为显然是在补给站闲逛并享受与人相伴的美好时光,跟朋友或熟人讨论当天的新闻,顺便再把刚刚充满的肺提供给和自己聊天的人。尽管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也许不能称为分享空气,因为配送机仅仅是从深埋地下的储气槽连接出来的管道终端,所以大家都明白我们的空气来自同一个源头——伟大的世界之肺,我们的能量之源,认清这个事实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出一种同甘共苦的友谊。
很多肺会在第二天回到同一个气体补给站,不过大家出门去附近的地区时,也会有很多肺流通到别的补给站。从外观来看,肺都是一样的:光滑的铝质圆柱体,所以人们分辨不出某个特定的肺是一直待在自己家附近还是来自很远的地方。新闻和闲话随着肺在人和地区间传递。虽然我个人很喜欢旅行,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不用离开家就可以了解到远方的新闻,甚至那些来自世界最边缘的新闻。我曾经一路前往世界边缘,亲眼看见坚固的铬墙从地面一直向上延伸,消失在无尽的上空。
我正是在一个气体补给站初闻那些谣言,然后才开始进行调查并最终获得领悟。很简单,事情始于我们社区公告员的一番话。按照传统,每年首日正午,公告员都要朗诵一段很久以前为这样的年度仪式而创作的诗文,这个过程需要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公告员提到,他最近一次朗诵的时候,钟楼在他结束之前就敲响了整点报时的钟声,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还有人说自己刚刚从附近的一个区回来,巧的是那里的公告员也抱怨了同样的事情。
没有人对此过多地进行思考,只把它当作看似正常的简单事实。仅仅过了几天,一个类似的情形再次被提起,又有一位公告员的朗诵与钟楼时间不符。有人认为这种异常情况也许体现出所有钟楼共有的机械缺陷,比较奇怪的是缺陷导致了时钟变快而不是变慢。钟表匠检查了出现问题的钟楼,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缺陷。其实,经过与那些在新年庆典中走时正常的钟楼相比较,人们发现这些钟楼后来一直在准确地计时。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有些蹊跷,但我的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上面,没法更多地思考别的事情。我是一名入行已久的解剖学学者,为了提供后续事件的背景信息,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与这门学科的关系。
因为我们生命力旺盛,致命灾难也不常见,所以死亡很少发生。然而如此的幸运却令解剖学研究难以为继,尤其是很多致命的事故都导致死者遗体受损过于严重,从而不能用于研究。假如充满空气的肺破裂,爆炸的威力足以撕碎我们的金属钛躯体,仿佛那是锡做的一样。过去解剖学家把精力都用来研究四肢,因为这些部分最有可能完整保留下来。一个世纪之前我上第一堂解剖课的时候,讲师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完整的断臂。为了露出里面密集的连杆束和活塞,外壳已被除去。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讲师把那条手臂的动气管连接至挂在墙上的肺——这是他储存在实验室里备用的,然后他就能操纵从手臂残端伸出的操纵连杆了,那只手也断断续续地随之张开与合拢。
从那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将残臂修复的程度,偶尔还能实施断肢再植的手术。同时,我们也开始有能力研究世人的生理学。我也给别人描述过我亲身参与的第一堂解剖课,在描述的同时,我打开自己手臂的外壳,指导学生在我移动手指的时候仔细观察伸缩的连杆。
尽管有了这些发展,在解剖学领域的核心仍然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巨大难题:记忆。虽然我们了解一些大脑的结构,但是由于它极其精密复杂,脑生理学研究的艰难尽人皆知。在一些典型的死亡事故中,颅骨被打破,大脑喷出一股金粉,里面除了少量破碎的细丝和箔片,几乎没留下什么,留下的东西也一点用处都没有。几十年来,关于记忆的主导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所有经历都被刻在了金箔上,脑部破裂时,气体的冲击力撕碎了这些金箔,形成了后来发现的那些微小碎片。解剖学家收集起这些金箔碎片——它们薄得可以透过光线,只不过光的颜色会变绿——花上好些年的努力把它们拼成原样,希望最终能够破译死者临终的经历在金箔上留下的记号。
我不赞同这种所谓的铭刻理论,理由很简单,假如我们的经历真是以这种方式被记录下来,为什么记忆不是完整的 呢?铭刻理论的鼓吹者为遗忘提出了一种解释——他们说随着时间流逝,金箔会从阅读记忆的探针下面移位,最初的金箔最终会完全移出记忆探针的触控范围——可我认为这个解释毫无说服力。不过这一理论所表达的主张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也曾花过很长时间检查显微镜下的金箔碎片。我也曾想象,假如旋转细调旋钮便可清晰地看见符号的轮廓,这将多么令人愉悦啊。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死者本人生前已经遗忘的过去也许会从他尘封已久的记忆中被揭示出来。我们对于以前的记忆仅限于百年之内,而文字记录——我们有自己铭刻的文字记录却不曾记得有过这样的行为——覆盖的时间也只比记忆多几百年。开始用文字记录历史之前我们存在了多久?我们来自哪里?从我们的头脑中就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记忆铭刻理论看上去如此诱人的原因。
我所支持的反对派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的记忆存储在某种媒介中,也许是旋转的齿轮,也许是一系列不同状态的开关,清除记忆和保存记忆一样容易。这种理论表明,我们忘记的一切确实无法恢复,我们的头脑所承载的历史也不比图书馆中记录的那些久远。空气耗尽致死的人更换新肺以后,尽管可以复苏,但却没有了记忆,几乎变成了傻子。这种理论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死亡的冲击以某种方式重置了所有的齿轮或开关。记忆铭刻理论的支持者声称,死亡的冲击只不过使金箔发生了移位。不过没有人愿意为了解决争端而去屠戮生命,即使试验对象是一个傻子。我构想过一个实验,它也许能令我查明最终的真相。不过做这个实验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要三思而后行。了解到更多有关时钟异常的消息之前,我一直在犹豫。
从更远的一个社区传来消息,那里的公告员也发现了同样的状况,在他完成新年朗诵之前响起了正点报时的钟声。令这件事与众不同的是,那座钟楼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装置,它用流进碗里的水银计时。这样的话,时间差异就不能用那种共同的机械缺陷来解释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某个捣蛋鬼耍的恶作剧。我却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它更加悲观,我都不敢说出来,不过它坚定了我的初衷。我要进行我的实验。
我制作的第一件工具很简单:将四块棱镜平行安放在支架上,仔细地调整它们,使它们截面上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顶点位于一个矩形的四角。这样,水平射入一块下层棱镜的光线会向上反射,再经过另外三块棱镜的反射,光线会沿着一个四边形环路回到原点。所以,当我坐下来,使眼睛和第一块棱镜等高时,我就能看到自己的后脑。这具自我观察潜望镜为将来我要做的一切打下了基础。
移动以类似方式排列的操纵杆便可以调整潜望镜的视场。操纵杆的活动半径要比潜望镜大得多,从而实现微调,不过这在设计上还是相当简单的。相比较而言,我分别在这些结构上继续增添的设备要更加精密。我为潜望镜添加了一台双筒显微镜,安放在可以上下左右转动的支架上,还为操纵杆配备了一批可以精确控制的机械手,不过这样描述那些机械杰作实在是有失公允。机械手结合了解剖学家的灵巧和他们钻研身体结构获得的灵感,操作者能够用它们代替自己的双手,完成更加精密复杂的工作。
把这套设备全部组装完毕花去了我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准备工作一旦完成,我就可以将双手放在一套旋钮和操纵杆上,控制一对安放在我脑后的机械手,并用潜望镜观察它们的操作对象。接下来,我就能解剖自己的大脑了。
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听上去十分疯狂,要是我讲给同事听的话,他们一定会极力阻止我。但是我不能让别人冒着受伤害的危险充当我的解剖实验对象,而且既然我打算亲自实施解剖,也就不会满足于在这个过程中仅仅充当别人的实验对象。所以自我解剖是唯一的选择。
我弄来一打充满空气的肺,把它们连在一个汇流管上并安放在工作台的下方。我将坐在旁边进行解剖。为了将其直接连接在我胸腔内的支气管入口,我又安装了一个分配器。这些设备将为我提供可以使用六天的空气。考虑到也许无法在这段时间里完成实验,我约了一位同事在实验结束时来我家做客。不过根据推测,决定我在这段时间里能否完成实验的唯一因素就是我在实验过程中死亡与否。
我首先取下了位于头顶和后脑的大弧度金属外壳,接下来是两块弧度稍小一些的侧面外壳。最后只剩下我的脸,不过它固定在一个约束支架上,因此即使能通过潜望镜观察到后面,我也无法看清脸的内表面。我看到自己的大脑暴露出来,它由十几个部件组成,外面覆着造型精致的外壳。我把潜望镜移到了将大脑一分为二的裂缝跟前,在迫切的渴望中瞥见了脑部件内惊人的机械结构。就算看到的内容不多,我也能断定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具美感的复杂机械,超越了我们制造的一切,它毫无疑问具有非凡的起源。眼前的这一幕令我兴奋得不知所措。我又严格地从美学角度出发,品味了好几分钟,然后才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