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尘埃落定》:从“傻子”的形象说开去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梁海 2020年04月20日08: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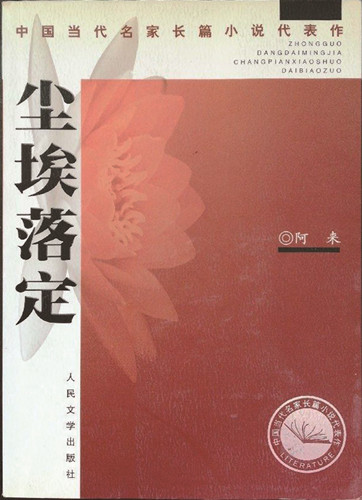
《尘埃落定》
阿来的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于1998年,这部在十几家出版社辗转了4年才得以出版的作品,于2000年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那一年,阿来41岁。《当代》杂志在转载《尘埃落定》时,将其誉为“中国长篇小说中迄今为止写少数民族题材的最佳作品”。《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家族为叙事背景,展现了康巴藏区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溃败毁灭的独特而又凄婉美丽的挽歌”。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整个创作过程时说,他对土司制度的历史做了详尽的考察,“我有七八年时间没写作,就到处走走。阿坝那个地方几万平方公里,乡一级的建制,三四年时间我跑遍了。口传的故事也好,地方性史料也好,都指向当地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到底是什么,要把所有材料弄懂”。显然,无论是《当代》杂志的评价还是阿来自己的陈述,都让我们隐约感觉到,《尘埃落定》是一部力求真实展现康巴藏区的史诗,是“藏族人写藏族人的故事”,作品体现了民族的“宏大叙事”。
然而,《尘埃落定》却并没有带给我们沉重的历史感。文本没有精确的时间点,只有模糊的时间段的叙述:白色汉人对红色汉人的围剿、红色汉人把白色汉人打败了、白色汉人的军队开走了,在开篇部分,我们甚至需要从麦其土司“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去告状”这样的叙述中来获知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在跳跃的时间链中,阿来借历史来完成自足叙事的创作初衷跃然纸上,历史叙事在他的笔下幻化为寓言式的诗性叙事。阿来说:“服饰、建筑、风俗、典章制度,我保证都很真实。但进入到故事领域,就是我的虚构。”这样的诗性叙事不是要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而是要在一个土司家族的毁灭中揭示出面对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相对弱势的藏地所表现出的蕴藏着集体无意识的诗性智慧。
显然,傻子少爷是诗性智慧的承载符号。傻子的一生都在经受着“聪明”与“傻”的拷问。在他眼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聪明人和傻子。如果仅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傻子似乎确是一个傻子,“土司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毛皮药材商买来送给土司的。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但这个傻子又往往能洞察聪明人无法洞察到的东西。他明白,“除了亲生母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我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是我是个聪明的家伙,说不定早就命归黄泉,不能坐在这里,就着一碗茶胡思乱想了”。在种罂粟还是种粮食的问题上,他力排众议,居然和睿智的老土司不谋而合;他比“聪明”的哥哥更懂父亲在边塞建粮仓的深意;在有土司以来的历史上,他第一个把御敌的堡垒变成市场,做出了聪明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就连老土司也产生了困惑,“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对权力有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在一定意义上,傻子的形象本身已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文本反复追问:究竟谁更有智慧?阿来借傻子之口道出了文本中的几个聪明人:“他们不太多,数起来连一只手上的指头都用不完。他们是麦其土司,黄特派员,没有舌头的书记官,再就是这个叔叔了。看,才用了四根指头,还剩下一根,无论如何都扳不下去了。”然而,这些聪明人并不是命运的征服者。老土司引进了鸦片,引发了饥荒,带来了梅毒;聪明的黄特派员竟沦为傻子的师爷;翁波意希是新教的忠实信徒,藐视权贵,视死如归,却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及他视为生命的传播思想的自由;而像“叔叔”那样为民族大义而奔波的人,最终却葬身大海,尸骨无存。尽管,阿来没有在精神、道义上否定这些聪明人,但从“智慧”的角度,他却更加肯定“傻子”的智慧。这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的诗性智慧,潜藏着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带有文化原型的意味。
阿来曾说,傻子的原型就是藏族民间传说中的智者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藏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个智者,像阿凡提。我是第一个通过写书为他画像的,但我喜欢的不是常人看到的他智慧的一面,而是注意到看似笨拙地显示其智慧的地方。阿古顿巴这个形象再一步变异,就成为《尘埃落定》的主角——土司的傻儿子。”早在1986年,阿来就在发表于《西藏文学》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中对其形象做了很大改变。首先是出身。在民间传说中,阿古顿巴的身份并不确定,并往往因其挑战的对手而发生变化。面对暴君,他就是机智的仆人;在愚蠢的领主面前,他则化身为聪慧的奴隶等等。但无论何种身份,阿古顿巴无一例外都是作为被压迫者而存在的,是广大贫苦大众的代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理想和心愿,是藏族民间智慧的结晶。但在阿来笔下,阿古顿巴则化身为领主家的少爷,成为了统治者行列中的一员,同时,整个文本所凸显的也不是其超人智慧,而是他背弃了自己的阶级在流浪中完成的内心自省和精神超越。正如文中最后所写,“黎明时分,阿古顿巴又踏上了浪游的征途。翻过一座长满白桦的山冈,那个因他的智慧而建立起来的庄园就从眼里消失了。清凉的露水使他脚步敏捷起来了”。在阿来笔下,阿古顿巴从一个民间英雄转身成为了一个孤独的智者,他的智慧已超然世俗之外,表现为对人生真谛的洞察和对诗性自由精神的追寻。阿来笔下的阿古顿巴,不是民间故事里扬善惩恶、帮助民众脱离苦难的精神“救世主”,而是放弃了以智慧救赎的责任,最终选择了孤独的远行。远离尘世浪游的阿古顿巴去追寻的是一种大智慧,诗性的智慧,也是能够洞悉生命本真的智慧。阿来对阿古顿巴这个藏民族的民间英雄所做新的解读,赋予了这个文化原型以新的内涵。阿古顿巴以原型的力量集聚着藏民族的最高智慧同时又超越了这一智慧,抵达了一个充满智慧、哲理、人性和自由的境界,一个寓言般的诗意境界。这一点,在《尘埃落定》的傻子形象中得以承继,傻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限感慨:“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
《尘埃落定》创作于1990年代初中期,阿来说:“我是1994年春天开始写的,当时我家窗外有一片白桦林,我情绪的起落也与它一致。写的时候它开始抽芽,然后繁盛,我的故事丰满起来;到了秋天辉煌的时候,故事也到了最高潮;当树叶残缺斑驳时,故事终于尘埃落定了。我写得很投入,当人物命运激荡时,我心潮澎湃。所以说,《尘埃落定》也是我当时情绪状态的一种描述。”而傻子的智慧正是阿来这种写作情绪的镜像呈现。阿来沉浸在“天人合一”的写作状态中直抵生命的真谛,建构了一种关于诗性智慧的寓言,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民族。不难看出,阿来此时的创作已摆脱了像《旧年的血迹》这些早期小说中所流露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视域,他反复提到,“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特别而特别”,“我借用异域、异族题材所要追求和表现的,无非就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尘埃落定》是阿来试图摆脱民族身份桎梏的尝试。其实早在1980年代,阿来就开始大量涉猎拉美文学,如聂鲁达、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作家的作品。阿来认为,这些作家“在本大陆印第安人编年史家这个位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为本大陆的现在和过去而工作,同时展示与全世界的关系。他们大多不是印第安人,但认同拉丁美洲的历史是欧洲文化之外的另一个源头”。由此看来,探究藏地文化与全世界的关系,才是阿来创作《尘埃落定》的初衷。傻子的“傻”源自藏民族的民间智慧,但这种智慧却具有普遍意义,折射出了关于人类终极思考的寓言。
在一定意义上,“傻子”在阿来的文学创作中带有“原型”意味。文学批评家张学昕曾以《朴拙的诗意》为题来研究阿来的小说创作。他指出,“阿来小说的人物形态是‘拙’的,结构形式是‘拙’的,叙述方式是‘拙’的,即使那些掩藏不住的诗性的语言也荡漾着‘拙’意”。“拙”俨然成为阿来的创作中一个流动的内核。当然,流动中的“拙”并非一成不变。《尘埃落定》中,傻子智慧的诗意蕴藏着一种无奈的怅惘,或许正是因为能够“预知未来”,傻子才时常表现出一种“知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态度。他安于妻子的背叛,安于哥哥对他的算计,安于仇人的复仇……“安之若命”的傻子是忧伤的,因为他知道结局无可改变,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局限。毕竟,洞悉生命的真谛并不意味着放弃与命运的抗争,或许这种抗争本身并不明智并不智慧,但却会带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感和精神力量。我想,阿来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云中记》中的祭师阿巴便呈现出了另一种诗性的智慧。文本中的阿巴也是“傻”而“拙”的,但是他的“傻”不同于傻子的“通灵”,他无法预知未来,作为一个祭师他甚至无法与亡灵沟通。然而,当人们被告知云中村不久后将随着地质滑坡在整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在一般人眼里最“傻”的决定:坚守在云中村为亡灵招魂。明知这是一条不归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阿巴让我想到了《神异经》中的“西南大荒之人”,拥有一般凡人无法企及的四个名字:“圣”“哲”“先通”“无不达”。“先通”是天之灵赋,“圣”“哲”则关乎人伦。这就意味着,神性的“先通”与人性之“哲”相融通便可抵达人的最高境界——“圣”。而一旦为“圣”便可“无不达”。这也就是古人所推崇的“圣智”。“圣智”之人怀有宇宙中最高的自然智慧,兼有最为健全的人性和最高尚的品质,总是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美德,是人中之圣。盘古、黄帝、炎帝、神农、大禹便是“圣智”的代表。他们打通了神与人、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在这个意义上,傻子的诗性智慧呈现的是一种“自觉”,而阿巴营造的诗意则是“觉他”。《尘埃落定》在对“傻”的形而上的建构中,将藏地的民族图谱绘制到世界图谱中,而《云中记》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作为作家的阿来,实际上已从民族走向世界,再从世界回到了自我,以充满自信的主体意识去承担了一个优秀作家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