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考古学家夏鼐诞辰110周年 《燕园清华园日记》近日出版 日记甫出 夏鼐的朋友圈亮了
夏鼐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埃及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是为新中国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学术专家。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由叶新教授核校并加注释的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近日出版。本版特刊发叶新教授纪念文章,以表怀念。

夏鼐毕业照
清华的那届毕业生 当以季羡林、吴晗、夏鼐和李嘉言为翘楚
夏鼐1931年夏天从燕京大学社会系转学清华大学,起初在社会学系和生物系、理科和文科之间做选择,最终去了历史学系第六级,1934年夏天毕业。该系本级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是仅有6名毕业生,四男二女,是上届和下届人数的一半。在清华大学文学院1934年的37名本科毕业生中,季羡林所在的外国语文学系人数最多,为21人,占了一半还强。李嘉言所在的中国文学系也有9人,哲学系以3人垫底。而从后来的成就来看,当以季羡林、吴晗、夏鼐和李嘉言四位毕业生为翘楚。二是到毕业时,夏鼐所在的班级全然不是当初进校时的原班人马。其中的夏鼐、吴晗、陈箴、许亚芬、颜承周均是1931年从他校转学而来,而郭秀莹本为历史系第五级,大二时因病休学半年。在夏鼐的《燕园清华园日记》中,只见吴晗、许亚芬两人的有关记录,其他三人不见踪影,可见他与本班同学关系的疏离。
许亚芬的有关记录出现在1934年三四月间去往山西的毕业旅行中。3月26日的记载是:
下午秘书处邀我去谈,要我负责组织历史考察团。报名加入本组10余人,但仅有3人为历史系,2人为蜜斯不能办事,只剩下我一个人,不能不负责,殊为心烦意乱也。
“蜜斯”即“Miss”,小姐之意。在历史系的三人中,有两人为女生,当是同班的郭秀莹、许亚芬两位。前者嫁给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外语系第五级的常风,后改名郭吾真,1950年后双双去山西大学任教。后者嫁给了历史系第五级的师兄杨绍震。在这次毕业之旅中,许亚芬当选为干事,协助夏鼐负责沿途事务。
在夏鼐的大学朋友圈中,以浙江温州同学和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校友为最多,如王栻、王祥第、徐贤修、黄万杰等。同为浙江同乡的吴晗在其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在《燕园清华园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是1932年9月26日,也就是两人转学一年之后:“房间中又搬进一人,为闻人乾君,系数学系研究生,金华人(吴晗同乡)。”
而两人的见面要到11月24日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夏鼐写道:
晚间往见吴春晗君接洽现代史学社事。同学同系已一载余,此次尚为第一次见面。顺便谈到明史及清史之事,谈了一点多钟才回来。他说现在从事的便是明史,明史的史料书籍,据其估计在千种以上,颇可供研究。又说《清朝全史》系但焘延留日学生代译,所以译错处很不少;原书颇佳,尤其是满清未入关以前的那段,至于下册则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Morse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说近人孟心史研究清史,亦颇有心得,《清朝前纪》一书殊可一阅;萧一山之《清代通史》,虽为钜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
此时才23岁的吴晗已经是明史专家,人称“太史公”,深得胡适先生等学界前辈的赏识,而夏鼐尚属籍籍无名之辈。因此在两人的初次见面中,吴晗大谈明清史研究,最后指出清史权威萧一山之《清代通史》的缺陷,夏鼐只能做他的忠实听众。对于为何两人这么晚见面,夏鼐先生在1980年2月发表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说明:
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科。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便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
不在一起上课,各有各的圈子,因此缺少认识的机会。夏鼐12月27日的日记则记载:
傍晚吴晗君来谈现代史学社,劝吾加入,并约我做一篇文章。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练习写文章,既已以史学为终身事业,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胆虚,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今年在校中周刊上发表的二篇文章都用“作民”的笔名,无非也是此故。并且入社费须15元,在目前的经济困难中恐难筹划,换句话说有点舍不得,但是又不能显然拒绝。现在只希望《图书评论》社那篇稿子能够获登,至少可得10余元,再凑合周刊社所得的稿费或可应付。至于稿子的材料拟定“叶水心学案”或“《鸦片战争史》书评”等。等大考后再说。

历史系同学去山西参观途中,左一为夏鼐,右四为郭秀莹,右三为许亚芬
批评吴晗稿件“划分方法未见佳” 吴晗复信,“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
吴晗在11月24日已经提到加入现代史学社之事,一个月后又旧事重提。夏鼐因为经济困难,对此颇为犹豫。但对写史学文章之事则颇感兴趣,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在《清华周刊》发表过文章。到了1933年初期,已就任清华周刊社文史栏主任的夏鼐开始行使审稿职责,对早已成名的吴晗的稿子也敢于和善于做出评价。比如1933年2月26日的日记记载:
阅稿:辰伯(吴晗)《汉代之巫风》,华芷荪《评〈武昌革命真史〉》,大致可采用。辰伯对于西王母故事研究有素,此篇虽以《汉代之巫风》为题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为主。虽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可以采用。华君之书评,专就史识论,说尚中肯,但未见深刻。
虽然这两篇文章都可以采用,但是对吴晗文章的评价是“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汉代之巫风》发表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1期(发行日期是3月15日)。然后是3月15日的日记记载:
阅稿:辰伯(吴晗)《读史杂记》……辰伯君专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条,然非多读书而精读者不能下笔。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自家每逢读书生疑,常检他书以图勘正时,或耗费累日而毫无所得,令人气馁,而偶有所获即大喜若狂。其中甘苦惟身经其境者始能知之,不足为外人道也。惟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校记之编次或依原书,或分种类,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误错。将来成为专书则应该用前法,将此意作成一信以给吴晗君。
夏鼐在此指出吴晗的《读史杂记》的优点是“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并联想到自己的读书体会。但是,他也指出该文的缺点是“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并马上写就一信发给吴晗。第二天就收到吴晗的复信“来示指出弟文编次不当,卓识精见,语语自学问中得出,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鲰生何幸,得拜面鍼”,表示惺惺相惜之意,让夏鼐不禁想起“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典故。虽然吴晗有“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之抬举,但此时尚未发力的夏鼐还是在日记中谦虚地写下“实则我并无此野心”。《读史杂记》发表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1期(发行日期是3月29日)。夏鼐特意在文后写了一整页的“编者按”,开头便提到:
辰伯先生治明史有年,此文虽仅涉及校勘学一方面,数量上仅寥寥数条,然颇多创获。用力之勤,令人拜服。惟篇中将明史之误,分为十项,各立名目,并系以例证;分合编次,似尚可斟酌。鄙意以为本篇将明史之误,依其性质而分类,则性质相似者,应并入一类,性质大同小异者,可并入一纲,而分为二子目,然后各系以例证,以示各种“典型的错误”。
夏鼐不仅指出了其不妥之处,而且接着提供了“四纲九类”的具体分类意见,显示其考虑之周全,最后提到“私意以为如此分类,较原来十项并列,不相统属,似为稍胜。不知辰伯先生亦以为然否?”
然后就是《清华周刊》“文史专号”的组稿和审稿,见1933年4月24日的日记记载:
下午马玉铭君来,询“文史专号”稿件甚罕将如之何。乃往见吴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约其自作之稿,至少2万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没有去上课,便是因为与吴君在合作社中接洽这事。
因为总编辑马玉铭的催促,夏鼐不仅自己要贡献稿件,还要去找吴晗写稿和代为拉稿,极少缺课的他因此还耽误了“西洋近百年史”的上课。到4月27日晚间,则“与马玉铭、吴春晗商酌‘文史专号’稿件排列方法”。到1933年5月9日,《清华周刊》“文史专号”(1933年第39卷第8期)正式出版发行。因为夏鼐审稿不徇私情,凭稿子质量说话,因此得罪了不少投稿的同学,此后也就步吴晗的后尘,不再干下去了。

在太原晋祠参观北魏造像碑
两门功课得了“超” 却被张宗燧批评“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
虽然忙于写作投稿、审稿出刊,偶尔不上课,夏鼐的功课成绩还是很好。见1933年9月11日的日记记载:
教务处将此次考试成绩发表,外交史和史学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仅我一人,得S-者亦仅吴春晗君一人,其余不外N、I、F),中国上古史是S+,中国社会史是N,法文是S-,党义S+,体育S+。
当时清华大学的成绩评定分为“超(E)”、“上(S)”、“中(N)”、“下(I)”、“劣(F)”五级。夏鼐除了中国社会史得的是“中”之外,其他都是“上”以上,外交史和史学方法两门课还得了“超”,而吴晗(编者注:即吴春晗,为吴晗原名)的外交史才得了“上”。这让夏鼐颇为满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教授曾在他的《晋南北朝隋史》考卷上写下大段评语,最后称赞他:“所论甚是,足征读书用心,敬佩敬佩。”
除了成绩不错之外,夏鼐的写作投稿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在1932年第37卷第1期(2月27日刊行)发表译文《言语和中国文学二者起源的比较》(原著)开始,到1934年8月1日在《图书评论》第二卷第12期发表关于《中国外交史》的书评为止,夏鼐大学本科期间总计发表了16篇文章,其中《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发表在当时顶级外交界学术刊物《外交月刊》上。另外,他在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下写就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修改后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2期上,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等并列,与他享有同等待遇的是同级中文系李嘉言的《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现》。
人常道: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只顾埋头学问的夏鼐迎来了一位好友的“当头棒喝”。他在1934年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晚上,小张忽同我谈起说:“鼐!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我遇见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谈起历史系的高材生,都仅知吴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会到教授处谈谈,与同学多接触,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这也许与你将来的前途有碍,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学者,也多少应该讲究些交际的手段。名过其实原属非是,但至少要名实相符。然而你的名声却远不及你的真实学问,我劝你要改换生活,不要关起门来读书。”这孩子今天忽板起正经脸孔说老人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这类话。我自己岂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岂不感得改正自己弱点的必要!然而十余年来的生活养成了我的惯性,虽欲改变而不可得。违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觉啼笑皆非。我的前途是黑暗的,我的过去生活是钻牛角尖,非碰钉不可。
“小张”即张宗燧,乃大名鼎鼎的张东荪先生之子,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15岁就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学清华大学物理系,23岁即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因浙江同乡之故,他在校时与夏鼐往来甚多,所谓“旁观者清”。他十分看重夏鼐的学术实力,把夏鼐与吴晗并称为“历史系的高材生”,但是认为夏鼐的缺点在于苦守书斋,不知“公关”,“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名实严重不符,对其前途大大不利。而吴晗与之相比,除了公认的学术能力之外,办事能力强,人脉十分广泛,以一介学生身份充分参与历史学术界的各种活动,获得了绝佳的学术研究机会。比如夏鼐1933年3月31日的日记曾记载:
至吴春晗处,送还前次所借之《尚书研究》一书。他说燕京哈佛委员会今年4月开会,以决定续办燕京国学研究所与否,若能续办,将着手编辑“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吴君拟担承《明史》一部分,欲以2年工夫为之。
与夏鼐写书评之类的小文章相比,才大三的吴晗能参与的都是“编制‘二十四史人名索引’”这样的大项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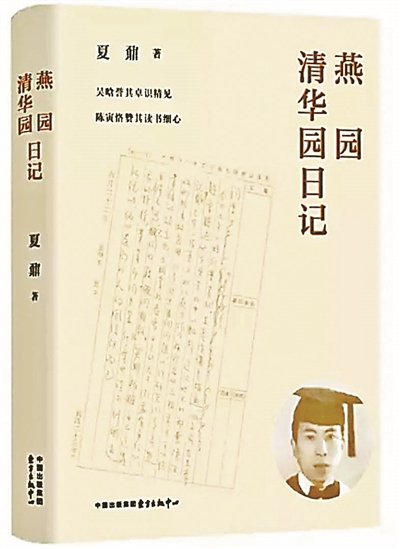
《燕园清华园日记》
加入现代史学社、历史学会 并参与发起史学研究会的工作
虽然夏鼐不知如何或者说不愿改变现状,但是张宗燧的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实际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此之前他也做过一些努力,比如他在1933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历史学会开会。刘崇鋐报告游英法的经历,拜访名家,参观故迹及图书馆、博物院。蒋廷黻时局报告,以为中央无心反攻,惟日人或将借口天津驻兵违反辛丑条约而积极进扰平津;世界大战之发生与否,须观欧美方面之国际形势,仅有远东现下局面似不能即引起大战。用茶点后选举,许某以8票为总务干事,蒋师以6票为庶务干事,吴晗及我各以4票为候补。9时许散会。
历史学会本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组织的学术团体,创建于1928年,师生均可参加。 “许某”即夏鼐的同班女同学许亚芬。夏鼐此称似乎有轻视之意,因为蒋廷黻教授只以6票当选庶务干事,他和吴晗才有4票,还只是候补庶务干事。
除了与吴晗一起加入现代史学社、历史学会之外,夏鼐还参与发起史学研究会的工作。夏鼐在1934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有“晚间至吴春晗君房中,与吴君及梁方仲君商酌组织史学社事”之语。同年5月20日的日记记载:
进城开会。上午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发起人10人(汤象龙,吴春晗,罗尔纲,朱庆永,谷霁光,孙毓棠,梁方仲,刘隽,罗玉东,夏鼐),除孙毓棠在津未来外,其余皆已到会,商酌会章及进行方针。下午继续讨论,至3时许始毕,定名为史学研究会,推选汤象龙为主席,约定下月17日再行大会,乃散会。
夏鼐位列10位发起人之列,任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汤象龙被推为主席。对应“约定下月17日再行大会”,他6月17日的日记记有“进城参与史学研究会,决定出版刊物”之语。此时的夏鼐已经到达既有学术实力,又有学术圈子的新境界了。
本想治学中国近代史 阴差阳错进了考古学领域
不过,此时的夏鼐已经到了毕业之期,是继续研究还是马上就业,成为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他在1934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与刘古谛、张宗燧、宁有澜、董文立同赴燕京,应陈凤书之邀,聚餐于燕京东门外餐馆,大家都是光华附中同班毕业的,侥幸的能够再叙一处,现在毕业后,更不知后会何时了!宁君已决定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陈君下学期毕业后拟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刘君拟赴日本庆应大学,张君正在预备考留美,反顾自己的前途,顿生渺茫之感。
同是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的校友,其他人都有美好的未来规划,此时的夏鼐则有前途渺茫之感。而此时已留校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的吴晗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见1934年7月29日的日记:
吴晗君来,谓广西桂林专修师范欲聘一文史指导,月薪160元,欲邀余去。余欲继续求学,乃婉却之,然吴君盛意殊可感也。
每月160元大洋的薪资是清华大学助教的两倍,但是夏鼐已经决然选择求学之路,先是报考本系研究生被录取,后又高中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前途顿生一片光明。因此有了1934年10月2日两人的一番谈话:
今天留美考试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果然获取,前几天的传言证实了。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下午去找吴晗君谈谈,他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世史,今日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我想同他商榷今后的计划,他说最好还是找刘崇先生谈去。晚间在王栻君房间谈话到10时余始回来。又写了几封信。拍了一个电报给家里,虽只“留美获中”4字,但是家人接到后,不知要怎样欢喜呢!
夏鼐本想治学中国近代史,阴差阳错地进了考古学领域,并最终奠定了他的学术道路,被尊为中国“埃及学”之父。也许这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成就了他和吴晗在史学领域并峙的格局。
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首批61名学部委员中,清华大学文学院第六级(1934年)占了三位:吴晗、夏鼐、季羡林。其中在历史系6名同学中就占了两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系毕业生的培养质量最佳。走笔至此,笔者耳边仿佛响起了吴晗当年对夏鼐所说的话:
“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