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奖作品《月亮的女人》: 从一个房间开始,以一个世界结束

阿曼女作家朱赫·哈尔西获2019年布克国际文学奖
阿曼女作家朱赫·哈尔西(Jokha Alarthi,1978-)凭其作品《月亮的女人》(此处为阿拉伯语书名直译。其英译本书名为Celestial Bodies,译者为Marilyn Booth)获2019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这是阿拉伯语作品首次荣获该奖,一时间文学界的目光聚焦到长期处于世界舞台边缘的海湾小国阿曼,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温和的文化氛围使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独树一帜。
《月亮的女人》的阿拉伯语原版早在2010年便已出版,小说通过阿曼小村庄“阿瓦费”一家三姐妹的家庭关系、爱情故事和人生经历,反映了阿曼社会从殖民时代结束后至今百余年来的演变过程。描绘了被历史洪流裹挟前行的众生群像。《纽约时报》评论员认为,《月亮的女人》本身是一座宝库,是一团由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和家族发展轨迹构成的混沌,它建立在秘密的引力之上。朱赫本人在采访中承认了对“代际小说”的兴趣,她有意塑造众多人物,从不同视角叙述事件以反映纷繁庞杂的现实,用一个个孤立的声音拼凑出一段完整的历史,这是一件“有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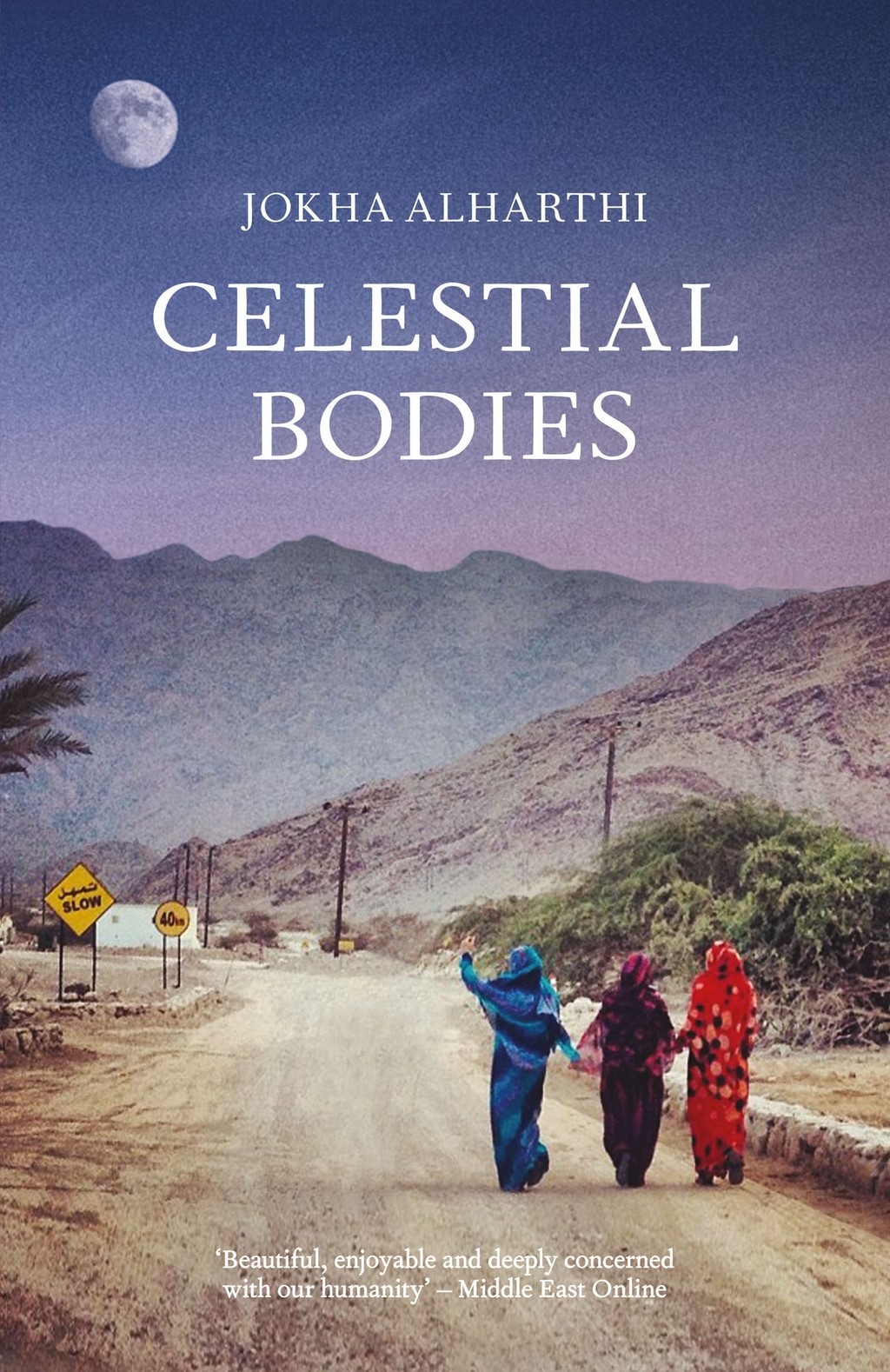
《月亮的女人》英译版
旧时代的挽歌
“当桑戈尔出生在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时,赛义德·本·苏尔坦 正与英国签署第二项禁奴贸易条约。在1845年达成的协议中,赛义德同意终止其在非洲和亚洲统治地区的奴隶贸易,英国海军船队有权在阿曼领海以及整个阿拉伯湾和印度洋截停阿曼船只进行搜查,并扣押和没收任何违反协议的船只。”
小说中最早的故事始于19世纪末奴隶制下的阿曼。女奴扎莉法的爷爷、出生于肯尼亚的桑戈尔在贩奴船只上死里逃生的故事读来触目惊心,但这仅是奴隶制暴露出的冰山一角。扎莉法被富甲一方的阿曼商人苏莱曼买下时的价格甚至不及半袋大米,而她却对这个“打开了她的身体和心灵”的男人痴情了一生。他给予了她公开的情妇地位,让她不必像其他奴隶一样过于操劳,却也曾因一次“大争吵”而将她强行嫁给另一个奴隶,仿佛她是一株可以随时被嫁接到任何植物上的枝干。这种畸形的爱情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却是奴隶制社会中的必然产物,甚至在当时还是令其他奴隶羡慕的处境。毕竟与扎莉法相比,她母亲安卡布苔16岁便被软禁侵犯、独自生产的经历更为悲惨可怕。
然而,无论多么“浪漫”的主奴爱情故事,终究掩盖不住奴隶制嗜血的本质,更比不上人性对尊严的渴望。时代的脚步轰隆而过,靠奴隶贸易发家的苏莱曼垂垂老矣,当年老病弱的他躺在病床上,叫嚣着把扎莉法的儿子桑吉尔锁起来时,桑吉尔正携家带口远走高飞。一切都宛如一个可爱的隐喻,旧时代再也无力阻挡怀揣梦想的新一辈奔向远方和自由的步伐。
评审团主席、英国历史学家贝坦尼·休斯说,这部小说展示了“精巧的艺术和我们共同历史中令人不安的方面”,同时又用巧妙的风格“消除了关于种族、奴隶制和性别的陈词滥调”。批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小说不在少数,然而《月亮的女人》在记叙历史的同时,并没有将历史生搬硬套,或者政治正确地塞进小说中,而是赋予了它人性的因素,为我们展现了普通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当亲情、爱情与普世价值观面临冲突时,又有谁能凛然评判对错?作为一名有使命感、正义感的作家,朱赫对历史中常被忽略的边缘人抱有深深的关切,她曾说:“传统媒体和教科书出于各种原因——我认为站不住脚的原因,企图忽略阿曼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但作家意识到,对睁开眼睛看历史的恐惧并不能让人产生安全感。因此,他敢于点亮手中的灯,在一个又一个长廊里漫步,它的光亮将永存,而另一盏灯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照亮历史的黑暗。”
要消解宏大叙事,不代表全盘抛弃宏大叙事,作家反对的是以宏大为代表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警惕个体被群体、微小被宏大绑架的危险。所谓的家国、命运、主流、历史,一定要融入到小人物的生活中去谈论才有价值,朱赫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让对历史的解说喧宾夺主地抢走应该聚集在“人”身上的目光。
时代的更迭令人猝不及防。战争中惨败的伊萨流亡埃及,却仍难忘抛弃他的故土,背负着“移民者”这个称号宛如背负沉重的命运,但他的艺术家儿子哈利德却不解他为何眼含热泪地吟诵阿曼革命诗人阿布·穆斯林·巴哈莱尼的诗歌,甚至对他的革新思想不屑一顾,“毕竟,谁会来买这些书呢?”伊萨的负隅顽抗在一个和平年代显得不合时宜,所谓“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阿卜杜拉还恪守着“不能谈论食物”的家规,而外面的新新世界已然铺天盖地遍布着人们张大嘴品尝美食的广告,他的儿子萨利姆及其同龄人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麦当劳里对食物评头论足、挑三拣四。当苏莱曼和“可怜人”马尼恩还坚守着“阿瓦费是我们的家乡”的信念,他们的后辈正争先恐后地涌向五光十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马斯喀特……
朱赫的祖父是阿曼最后一批古典诗人,也是朱赫在文学上的启蒙者。童年的朱赫在祖父的沙龙里抓住了旧时代的尾巴,并将之真实地还原在纸上。新千年带着新的风向和新的迷茫吞噬了一切,但它将把人们引向何方还未可知。尽管今天的阿曼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坚船利炮的殖民岁月,但放眼望去,马斯喀特的酒店旅馆纷纷挂起“此处只说英语”的标识以彰显其高端定位,谁又能说以文化侵袭为手段的一种新型殖民主义没有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氛围中兴起?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们无需再担心被一场洪水淹死,但钢筋水泥的现代化城市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无论好坏,昨日世界已然故去,每一个古老的国度都需背负自己厚重的历史继续前行。朱赫以诗意的笔触,将百余年来的种种变化凝练而真实地通过小人物的生活呈现出来,为落幕的时代做了一部深情的传记。在她笔下,新旧两个世界的转换有一种诗意而神奇的美感,而伴随着这种转变的,是老一辈人的逝去与年轻一代的崛起。也许社会变革注定在老一代对新一代的震惊与不满中完成,每一代人在上一代眼中都是“垮掉的一代”,但也正是这些“垮掉的一代”们,让文明和文化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破旧立新,继往开来。
朱赫在《月亮的女人》里采用了典型的意识流写作手法,时间的跨度伴随着破碎的情节,一如人们飘萍般的命运。仅229页的小说中出现了多达三十几个人物,且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得到了一定的述说,让人很难分清究竟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作者仿佛意图为我们描摹一幅时代转型中的群像,而非以单个人物作为典型,一言以蔽之地将所有人的经历微缩于其中。这无形中给阅读增加了些许难度,复调性的多声部叙事让无数“你”、“我”和“他”交杂在一起,稍有疏忽的读者很容易迷失在多声部叙事的海洋中和跳跃突变的时空里。然而,正是语流的交错和断裂,让读者得以与作者的思绪、人物的命运一道翱翔空中,俯瞰阿曼乃至阿拉伯的苍茫兴衰,在位于彼岸的文化中瞥见别一番洞天。
月亮般的女人们
“沉醉在她那蝴蝶牌黑色缝纫机旁的玛雅,同样沉醉在爱情中。”
小说开篇与《木兰辞》的“唧唧复唧唧”异曲同工,待字闺中的女儿心事稚嫩而美好。从书名不难看出《月亮的女人》的主体人物是一群神奇的女性,而这显然与朱赫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在一群女人中间长大。她们中有人强大、耐心、无私,具有奉献精神,也有人脆弱。每个女人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不相同。我看到她们在爱,在恨,在做饭,在纺织,在生儿育女……”
小说中的女性性格迥异,但她们的故事同样迷人。在她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些朱赫本人的影子,玛雅的沉静、阿斯玛的好学、郝莱的倔强……似乎作者将自己的灵魂分成许多部分,装进了不同女人体内,女性的脆弱与坚强、失望与憧憬,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长久以来,我们对于阿拉伯女性的想象,往往是戴着面纱头巾、顺从地坐在丈夫身后一言不发的家庭妇女。然而,朱赫通过《月亮的女人》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塑造了一个个坚毅勇敢的女性。“在阿曼历史中,我们有女学者、女法学家,女战士和军队的女领导人,还有成千上万无声的女人在田野、房屋、牧场和学校里用默默劳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她们与男性比肩而立,其力量感与果断干练的劲头不逊色分毫,甚至可以说她们对人生和家庭有着更清晰明确的掌控。
玛雅与丈夫阿卜杜拉同样生活在家长的控制下,但两人的选择截然不同。尽管母亲萨里玛的管教相当严格,玛雅却始终用自己“内在的世界”对抗“外在的世界”,努力逃离母亲的掌控规划自己的人生。而阿卜杜拉虽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富商,但在玛雅眼中他永远是“用成人的大衣伪装自己”的小男孩,视获得父亲的认可为毕生使命。同样的,在阿斯玛与哈立德的婚姻中,阿斯玛看似是较为弱势的一方,但与哈立德那时而热情如火时而寂静如冰的性格相比,她更善于掌控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并运用这种能力摆脱了丈夫对她的控制,“不再在丈夫的天体内运转”,而成为独一无二的“天体”。
小说中最值得一提的女子纳吉娅,更是展示了独属于女性的风采与魅力。成长在贝都因部落的纳吉娅因其美丽的面庞而被称为“月亮”,这动人的名字包含着作者对她的偏爱与欣赏。“月亮”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和永不言弃的强大意志。她不满学堂的种种束缚而早早退学,却凭借着强大的生意头脑发家致富。和她无能的父亲、病弱的弟弟、乃至逃避扭捏的情夫阿赞恩相比,纳吉娅从始至终的率性而为、英姿侠气更让人钦佩。她在追求爱情时比任何人都敢于直视自己的内心,却又不屑于成为爱情的奴仆。“月亮才不会接受他人发号施令,我不是为了侍奉男人、听命于男人而被创造出来的……他会偷走我身份的合法性,切断我和弟弟、女伴们的联系,他有时说不要出门,有时规定不要穿这件衣服,有时让你过来,有时让你走开……不不不,阿赞恩将会是我的,但我不属于他。”铿锵有力的话语无异于女性的独立宣言,毕竟一个女人可能是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但绝不是某人的奴隶,而更重要的是,她永远应当忠于自己。这样的女子热情奔放、勇敢倔强,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为了达到目的会想方设法,果敢坚决。精明、现实而强干的性格让她如同风一般,南来北往却无迹可寻。然而,朱赫给了她一个扑朔迷离的结局,贝都因的大漠黄沙失去了光芒四射的月亮。这也证明了女性追求自由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她面对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家庭或个体,甚至来自于整个社会。无论如何,“月亮”并非毫无瑕疵的满月,但她不羁洒脱、追求自我的勇气将照耀一个又一个女性在成见、打压的荆棘中无畏前行。
随着信息的流通和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女性被现实逐出对乌托邦式婚姻乐园的想象。当伊本·哈兹米在《鸽子项圈》中畅想的那种灵肉合一的爱情神话被打破,女性真正的庇护所究竟在何方?如同伍尔夫在《达洛维太太》里借克拉丽莎之口说出,“人都有一种尊严、一种独处的愿望,就算在夫妻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朱赫在《月亮的女人》中隐约地指出了一条道路,大概“复乐园”就孕育在每个女性强大而独立的心灵中。你有你的天体,我有我的轨迹,没有人必须绕着他人运转,但我们可以偶然地相交,这便是最好的关系。
从房间到世界
“世界变得昏暗,我听到汽车发动驶远的声音。伦敦坐在方向盘后,穆罕默德在她怀中。我突然觉得他像一条鱼。我走向汹涌的大海,直至海浪淹没胸口。当我张开双臂时,穆罕默德像鱼一样溜走了。我衣衫未湿地回到了陆地上。”
小说在压抑而超现实的场景中走向尾声,这样的结尾让人意犹未尽。浩大天地中还有许多故事没有说完,不知何日能再相会,有些故事在作者心里,而更多的则在读者心里。朱赫说,“事实上我没有完成这本小说,我放弃了,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是一项无法完成的工程……在某一刻放弃成为了拯救作品的选择,它让小说从我的场域走向读者”。正是因为作者的故意放弃,读者才无法放弃对作品的猜测和解读,而这何尝不是小说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也许比一部小说更让人激动的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它包含着人世间的万千可能性。
小说以房间里的玛雅沉醉在爱情与缝纫中开头,以阿卜杜拉将儿子抛弃在海中结尾,夹在其间的是阿曼的百年浮沉。因此,贝坦尼·休斯评价道,《月亮的女人》是一本“从一个房间开始,以一个世界结束的作品”。
而朱赫写作《月亮的女人》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从房间到世界”。“二十多岁时的我是一名外籍学生,用一种我不喜欢的语言(英语)攻读博士学位,也是一个孤独女孩的母亲。写作拯救了我。我带着异乡人的脸庞、异乡人的话语行走在街头,看到成千上万的故事与我同行,我邀请它们与我一起在霜寒中共饮咖啡。圣诞彩灯在窗外摇曳,积雪覆盖屋檐,唤起了我关于沙漠和烈士祖先灵魂的记忆……邻居邀请我去她明亮的屋子里喝下午茶,我脑子里却想着姑妈那刷了深色墙漆、壁龛上摆满古董器皿的房间。在写作中,我爱上我的角色,与我的漂泊和解。”
诞生于爱丁堡一个小房间里的《月亮的女人》,最终走向了全球亿万读者,诞生于孤独中的文字,最终疗愈了写作者孤独的心。也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一本本小说犹如一个个世界,人们漫步其中,流连忘返。而透过朱赫搭建的世界,人们得以望向一直被边缘化的海湾小国阿曼,得以倾听边缘人的声音。在日益强调多元对话的时代,我们愈发意识到,再微小的国家、再微小的个体亦有其尊严和价值,亦有发声的权利和必要,而再微弱的声音,亦有“从房间到世界”的力量。
细读小说,字里行间总是透着一丝孤独。阿赞恩在贝都因篝火晚会的袅袅余烟中心心念念的仍是他夭折的幼子,扎莉法在热闹的婚礼过后感慨的是不饶人的岁月,而萨里玛在女儿出嫁的喜庆时刻感慨自己闹剧般的荒唐婚姻。大概每个人的人生都总有那么一些不完满,外人看来的和睦夫妻可能同床异梦,而矫健舞娘则为病痛所累辗转难眠。这不就是人物们褪去主角光环后最真实的样子,不就是我们需要应对的真实生活吗?种种琐事,百味人生,但不为琐事纠结困扰的人,也无法为琐事开怀大笑。我们是否能与朱赫一道,与过往、孤独和流浪的自我和好,让精神回到家园。
写作是一个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的过程。阿斯玛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两个灵魂与肉体紧密贴合的人。阿赞恩说,生灵即使在互相联系时也是分离的。阿卜杜拉安慰离婚的女儿伦敦,爱情不再了但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医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了灵魂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有一份孤独,让它在自己的宇宙中有徜徉的空间。而孤独并不意味着孤立无援,心灵之间的共鸣与回音仍可响彻天际。只要在自己的房间中深深地挖洞,终有一天我们体内的声音会流淌过长长的通道,与其他的声音汇合。到那时,我们将一同聆听这多声部的灵魂奏鸣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