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看不见的手”,被你们夸大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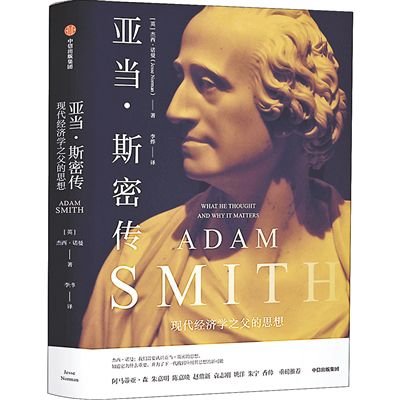
主题:《亚当·斯密传》新书分享会
时间:2021年3月19日晚7:00至9:00
地点:单向空间·大悦城店
嘉宾:朱嘉明 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办:中信出版集团
为什么大家对亚当·斯密
有那么多的误解
主持人:亚当·斯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即便大家不了解他的生平,也多半听说过这几个词——“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劳动分工。亚当·斯密被一部分批评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的鼓吹者,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动者,是不平等和个人私利的辩护人。但是在《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这本书中,作者告诉大家这其实是对亚当·斯密的一种误解。
朱嘉明:亚当·斯密是1723年出生,1790年去世的。1723年在中国发生了什么?雍正继位。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他生平的绝大多数时间对应中国的清朝雍正、乾隆年代。亚当·斯密死后5年,中国进入嘉庆年代。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从清朝雍正年间到乾隆年间,在英国有一个苏格兰人叫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这本书。这样我们会想一个更深的问题,在18世纪的世界背景下,在中国有没有人会像亚当·斯密,或者像和亚当·斯密同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休谟那样,来考虑各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回到今天的主题——“在焦虑时代重遇启蒙”。为什么我们处在一个焦虑时代?在这个焦虑时代,为什么需要启蒙?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另外一个可以对比的事实,亚当·斯密在1759年写了《道德情操论》,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青壮年,35岁。35岁之后,他又写了《国富论》。
那么亚当·斯密所处的是否是焦虑时代?在我看来,那也是一个焦虑时代。正由于那样的焦虑状态下,所以才有在18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讲理性,讲人如何摆脱各种各样外在的精神桎梏,如何用理性来解决在焦虑时代的所有困境。
这样就可以引出第三个问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他生前没有发表的法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他对天体的研究,所有这些东西,他的经济学或者他对伦理道德的思考,都属于理性主义的表现。“看不见的手”是非理性的,但其思想恰恰是基于理性的前提,他在启蒙主义思潮的背景下,探讨经济问题。
我总结一下以上讲的观点,第一个是与中国做横向的对比。第二个是在18世纪,从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一直到发表《国富论》,亚当·斯密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多次修改,这反映了他实际上始终没有放弃他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他遵循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状态和经济特征。
那么后面我们还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观点中,为什么大家对亚当·斯密有那么多的误解?为什么这个误解在中国显得那么严重?为什么严重的误解造成了值得重视的后果?
何怀宏:在今天这个时代回顾200多年前,当时开启的一个时代对我们今天的时代造成了深刻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亚当·斯密。我很怀念也很喜欢、欣赏那个时代,只要看看亚当·斯密的通信集,就可以了解到,在18世纪初,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当时激烈的战争与社会动荡很少,经济贸易发展得很好,知识分子的交流很密切。尤其是18世纪的苏格兰还发生了启蒙运动,出现了包括亚当·斯密、休谟、哈奇森、弗格森等一批人。那个时候的苏格兰有足够的和平与安宁,在那个时代,休谟和亚当·斯密结下了友谊,休谟的哲学对亚当·斯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充满希望的,也比较单纯。
《亚当·斯密传》这本书,我感觉它中规中矩,它肯定了亚当·斯密提到的商业社会市场,这是它的中心议题,但也论及了另外的方面,比如说政府的作用,还有平等的问题。
经济体系需要被一个
更大的“社会道德”所控制
主持人:我们一直有这种疑惑,为什么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大行其道,被推到非常高的位置,而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的理念,在今天处于边缘?
朱嘉明:亚当·斯密的思想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首先是《道德情操论》,第二是经济学,第三是法学。人们对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印象,常常以他最突出的成就作为标准。但事实上,他没被关注的东西,甚至比其他同行更加了不起。亚当·斯密就是这样的人。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最激烈批判的是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它说有一个蜜蜂的王国,国王是大坏蛋,其他的蜜蜂也都是大坏蛋。每个人都贪婪、自私、卑鄙无耻,每个人都在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结果蜜蜂王国繁荣昌盛。后来有一天国王良心发现,说这样不行,我们现在要讲讲道德,讲讲所谓的节俭,讲讲所谓的朴素。于是大家都要压抑自己的贪婪,于是这个蜜蜂王国就崩溃了,从繁荣走向萧条,从萧条走向衰落。
这在当时的英国是争论不休的。是不是因为私人的恶德能导致公益的结果,就承认恶德?如果世界所有的公益都要基于贪婪、自私、无耻,来实现构成客观上的繁荣,那么这样的成本是不是绝大多数人能够承受的?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只有参加恶德的游戏,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我的立场是否定这个结论。 亚当·斯密对所有问题的讨论,也是基于他对恶德的否定,基于他不承认恶德的集合、恶德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个正义和公益的后果。这是本质问题。
从这样的基础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他是怎么来看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体系是嵌入到社会体系中的,所以经济需要被一个更大的形态所控制,这个形态是社会,这个形态的底色是道德。当你实施所有经济行为的时候,有一个底线是不能够触犯的,就是良知。你的利益不能在损人的基础上实现,恶德在经济行为中必须被扼制,所以市场不应该是放任的。
我为什么为《亚当·斯密传》这本书写序,我为什么对这本书这样肯定?道理很简单,这本书告诉我们,亚当·斯密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经济学之父”,他支持商业社会,他看到了商业社会的积极一面,但他同时对商人做非常不客气的批评;他主张自由贸易,但他坚决反对奴隶贸易,这都是他。他的《国富论》大篇幅地讲教育,讲对贫民的教育将使整个社会受益。他讲了国家、公益社会、公共产品,所有这些问题本身是关于如何面对贫富差别,关于穷人或者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如何改变他们的无助。这是亚当·斯密关心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在修改最后一版《道德情操论》时,他还加了一章《论嫌贫爱富、贵尊贱卑的倾向所导致的道德情操之腐败》。那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短,他死的时候还没有我现在岁数大。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他垂垂老矣的时候,他想的是道德腐败,他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看不见的手”,在他的整个著作中几乎不占一席之位,但是这一点却被庸俗化和绝对地放大。
当代的焦虑来源于
“怎么学习都跟不上时代”
朱嘉明: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讨论亚当·斯密时代,就是18世纪后半叶的焦虑,那个时候的焦虑和今天的焦虑到底有哪些差别?我们今天的启蒙,和那个时候亚当·斯密包括康德加入的启蒙,到底有哪些差别?差别非常明显。
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从农耕社会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在亚当·斯密死了之后,才有狂飙性的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商业社会,是重商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伦敦遍地是垃圾,到处是污水,泰晤士河脏得一塌糊涂,到处是雾霾。在那样的时代,人们焦虑是不是能活下去的问题。
当时,所有大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资本正在影响整个英国的走向。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所以他首先写的是《道德情操论》,呼吁人们把同情心放在首位,强调同情心是一切道德的前提和本原。但是他觉得不够,在这个社会,我们怎样用道德来解释经济问题呢?于是他写了《国富论》,他强调法律。《国富论》的本质是怎么样建立道德的基础和秩序,而不是放任自由,不是通过所谓的市场经济把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曼德维尔的蜜蜂王国,用恶德最后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平等和幸福。
回到今天,我们是从后工业社会向数字经济、向信息化改变,这个社会的焦虑不是绝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问题,而是所有人被科学、被技术、被一切迅速的改变所推动的时代,是一个怎样学习都跟不上的时代,所以大家焦虑。这是另外一个焦虑。在这样的焦虑下,到底靠什么?我认为现在只能靠理性。不靠理性,靠浪漫主义?靠民粹主义?都不行。至少它们都有巨大的缺陷。
理性无非是强调这几个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理性的,我们需要沟通,我们互相信任,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新的标准,要诉诸一些秩序,这是理性。不这样怎么办?没有理性,疫情怎么控制?这次疫情就是一次证明,证明了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理性。第二个是科学。你可以说科学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个世界被科学改变,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把我们不断带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要接受科学。第三,我们要有人文关怀,要有人文主义。
只有这样,每一个人的孤独才能够得到相当的改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会理解亚当·斯密和我们原来听说的是不一样的。
二百多年前那场启蒙运动
有三大局限
主持人:非常想听何老师作为一个哲学家分享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更正确地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理解亚当·斯密提出来的这样一些理论?
何怀宏:我有一些观点跟很多人可能不一样。我觉得200多年的启蒙,一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伟大的成就,比如说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中所写的那样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仅仅靠启蒙,或者是进步至此的启蒙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启蒙没有解决欲望的问题,甚至对它推波助澜。任何社会,包括古代辉煌的雅典、伟大的罗马,它们都从节制的中道走向到欲望的放纵,结果都毁灭了。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现代主要的欲望——物质的欲望和身体的欲望,好像已经成为主流。但批评物欲和消费主义不能只是怪罪于市场,也不宜过度批判。
我们所关心的,这里其实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的感觉,包括亚当·斯密在内,我们可以感到一种对许多人的同情,对他们追求财富,或者说好的物质生活的一种相当的同情。而市场,相对于管制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来说,是最能实现这种致富愿望的手段。西方反感物欲的学者往往都是到批判市场、批判资本为止。但是后面是什么呢?大多数人更希望的是什么?他要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段,他们也不想损人利己,但是他们会希望物质生活不断增长,想要一天比一天好的物质生活。
许多启蒙学者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觉得只要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精神社会,走向艺术或者其他的方向。我们看到这种结果了吗?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地希望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欲望得到满足。人类的历史,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就是奢侈品不断变为必需品的历史。启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人性的认识有所不足,没有解决欲望节制的问题。
第二,启蒙没有解决团结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包括政治社会,包括美国、欧洲、西方的内部都有分裂乃至对抗。不是逐渐平缓,反而是越演越烈。
第三,最重要的,启蒙没有解决启蒙本身的难题。启蒙的含义是什么?用康德的话说是公开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看到民粹主义,或者是反智主义盛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我觉得和启蒙单一方向的进步主义有关,今天也依然如此。所以我们也许需要调整启蒙的方向和节奏,也要看到启蒙本身所包含的蒙昧,尤其是对人性的蒙昧。
“启蒙”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启发和照亮蒙昧。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启明星”,在黎明的时候首先出现在天空,开启光明。所以我们到底是在照亮蒙昧还是开启新的蒙昧?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一向反对高调,无论是社会的高调,还是道德的高调。我也不太相信人的无限可完善性。
我觉得亚当·斯密还是相当低调的,他有底线。包括他所说的,他觉得应当自立、自爱,他并非倡导损人利己,也不倡导自私。他对普通人所追求的,包括物质的追求也有相当的宽容、理解,也知道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亚当·斯密意识到,市场本身也有一种道德性,可以反对强制、干预,但是任由道德走向高调的话,那肯定不能实现。人不像动物,人还有精神生活,但现代社会看来很难变成一个像希腊、罗马那样伟大或辉煌的社会。
区块链等新技术
可以成为解决焦虑问题的新手段
提问1:老师好,我今天来,因为我自己也处在特别焦虑的时间段。最近正想要转行,获得一些成长,所以我一直在各种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会很迷失自己,就觉得这种焦虑会打乱我本身的方向。这样迷茫的阶段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朱嘉明:我把问题简单化。首先我现在也很焦虑,咱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只是我的焦虑和你的焦虑不一样。假如说我要争取工作到90岁,现在还有20年,我怎么安排这20年呢?我会焦虑吗?你想你20年后变成中年妇女了,那时会怎么样?每个人的焦虑都有差别。
第一,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是焦虑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是在这个时代,同时发生的东西,比如说科学、人文、社会、政治、经济,每天都发生大量的问题,而且大量的问题在今天体现成一个现象,就是无休止大规模的信息爆炸。每一个人都被信息包围、控制、垄断。你不断接受信息、分析信息、理解信息,处在完全不对称的时代。你不知道还不行,而知道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所以信息使焦虑严重化。
第三,更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焦虑和你对焦虑的克服都会互相传染。你传染你的父母,你们父母再影响你,你传染给周围的人,这就变成一个共振现象。如果反观20世纪的焦虑、19世纪的焦虑和现在的焦虑,如果写人类焦虑史,现在的焦虑是最有挑战的焦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讲理性,讲18世纪的理性和18世纪的启蒙,当时它诉诸精英,通过精英来解决社会在那个焦虑时代该怎么办的问题。今天,我认为精英时代迅速地过去了,这个时代需要大家自组织,一起来想办法解决我们所有人面临的焦虑问题。
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一直支持区块链,支持数字经济,我现在真的支持NFC、NFT。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解决焦虑的一种手段。我们现在要靠新的办法来化解一个时代的焦虑,通过理性、科学的办法来寻找解决我们时代焦虑的方法。
提问2:关于区块链和NFT这样的新兴技术有助于帮助人缓解焦虑,能不能展开谈谈。
朱嘉明:展开是展开不了了。我想说大家仔细想想,焦虑和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孤独、变化。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最大焦虑,是在信息爆炸的情况下,每个人其实是被信息割裂的,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孤岛。在被边缘和被孤岛化的过程中,人们期望得到所谓的温暖,希望自己的价值被别人承认,希望被别人尊重。
那么实现这些东西,在今天这样80亿人口的人类社会,现在有一种工具,就是区块链。区块链可以让你实现自组织。今天NFT可以实现自我表现,让别人去承认你的价值。这些东西不是解决焦虑的灵丹妙药,但是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产生一个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在21世纪这个时代,我们比不上康德,但是我们想点办法自娱自乐也是一个今天的启蒙运动。
提问3:想问朱老师一个问题,除了通过一本书籍的分享,是否有更多、更积极、系统性的努力是可以复制的?
朱嘉明:首先第一条,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别说一本书,一千本书都解决不了人们普遍的焦虑。我并不认为在焦虑时代有单一的办法来解决普遍性、蔓延性的焦虑。
但是为什么《亚当·斯密传》这本书很有意义呢?亚当·斯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符号,这个历史符号有巨大的冲击性。冲击性在于什么呢?亚当·斯密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没读过亚当·斯密,也没有认真读亚当·斯密。这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亚当·斯密本身多么重要,而是亚当·斯密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现象太重要。
改变这种亚当·斯密被误读、被误导的现象,背后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包括我们怎么看待人性,看待消费主义,看待物质主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严格来说是借题发挥,但是历史总是需要借到一些问题来把很多问题串联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