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为什么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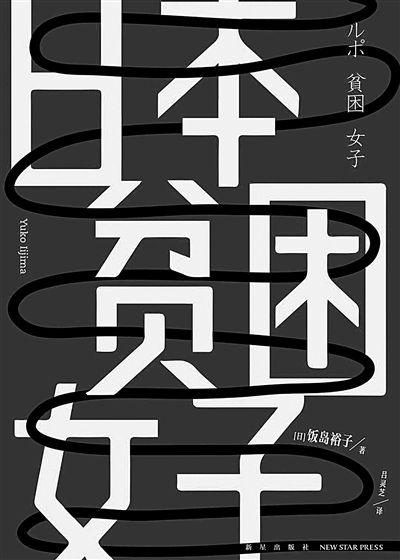
“上大学后我才发现,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没用,女性会因为外貌和身材被别人指指点点。有的女性可以仅仅因为漂亮可爱就广受欢迎。上高中时,我还坚信人只要努力一定有回报,很久之后才明白过来,原来世界并非如此。”
已42岁的川口澄子这样说。
在《日本贫困女子》(饭岛裕子著,新星出版社)中,川口澄子的情况不算太差。她擅长英语,在大学当了10年非正式雇佣(书中有见习生、合同工、临时工、日工等多种职业分类,待遇不同,作者统称为非正式雇佣),一度收入不错。
在日本,非正式雇佣意味着随时可能失业。21世纪以来,20—40岁的就业者中,1/3属非正式雇佣。其中,42%的女性如此,远多于男性(28%)。她们平均年收入147.5万日元(约8.6万元人民币),只及男性非正式雇佣(222万日元,约12.9万人民币)的2/3。
一旦成为非正式雇佣,便很难再成为正式工。“非正式雇佣—失业—为省钱与父母合住—自我迷失—找更差的非正式雇佣—再失业”成为一条标准的向下通道。
其结果是:日本女性依然要靠婚姻改变命运。
川口澄子的月薪不足12万日元(约7000元人民币),“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成家……我现在没有一样能让自己踏实的东西,太痛苦了”,但她只能“假装自己在享受独身生活”。不论是官方统计,还是社会救助,都不将她视为贫困者。
社会为何忽视贫困女子
在日本,“女性贫困”是一个很少被提起的议题。
一方面,女性贫困率“并不是最近几年突然上升的,而是20年前就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她们的贫困一直被视为个人问题,而非社会结构问题。
表面看,日本女性可与父母同住,大大减少支出,而在文化上,男性绝不可如此。女性似乎享受了“优待”,但也掩盖了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迂回的。因屡屡失业,27岁的小谷由纪长期忍受父母的唠叨,精神趋于崩溃,她不得不搬到网咖、漫咖、KTV去住,“存款花完之后,还睡过公园”。
在日本,单身女性在街上停留时间略长,会遭遇男人骚扰,许多贫困女子只好“想开了”,从此在自我谴责、恐惧中度日,直到找到下一个非正式雇佣的工作。可非正式雇佣的收入太少,工作又很辛苦,一些贫困女子偶尔会想念“想开了”的日子。
很多女性没意识到自己贫困——住在父母家,暂时衣食无忧。可一旦父母去世,她们立刻陷入困境(甚至有人饿死),代价是忍受亲人的冷漠、语言暴力等。即使父母完全接纳,宅女们也会因长期无缘社会,产生社交恐惧症等。
作者特别使用了“关系贫困”一词——她们目前生活无忧,貌似自立,甚至可以拥有奢侈品,但在社会性上,已落入赤贫。
条条大路通向女子贫困
陷入贫困的女性,多以辍学为始。
一旦辍学,便很难再与社会建立联系,随之丧失自信,进而失去外出的勇气,落入越来越孤立的恶性循环。日本文化对女性辍学较宽容,认为是“新娘修习期”,少有人探究为什么她们不愿继续学业——部分女孩源于家庭贫穷;此外曾在学校遭霸凌,自我被彻底推倒。
霸凌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有的女孩初中遭遇霸凌,短大(短期大学,近似中国的大专)时才辍学。此时已远离霸凌者,亦无法追责。
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经济腾飞,女性就业前景看好。1995年,日本双职工家庭数量首次超过传统的“男主外”家庭,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中存在结构性的缺陷:
其一,女性只有拥有高学历,才有职场机会。OL(办公室女郎)受追捧,辍学女孩却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高学历=好工作”引发女性的“军备竞赛”,考上大学本科的女生一度超过男生。
其二,当时日本女性单身率不足2%,“结婚后就辞职”是常态,男女之间竞争相对较小。
1985年,日本通过《男女雇佣均等法》,主张男女就业机会均等,俨然是“文明一大步”。可随着女性单身率的迅速增加,许多女性不再退出职场,此外IT业发展,企业对办公室文员的需求骤减,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女性就业形势迅速恶化。
比如书中写到的草柳明子,原本是端“铁饭碗”的公务员,因女性升迁极难,她先后四次被调换部门,每次调换,都要花很长时间适应新工作。最后,她被安排到水道科,需要经常外出,因不熟悉情况,她饱受同事指责,不久,罹患“心因性反应”——巨大压力下的精神损害。
病假结束后,草柳明子依然难适应新工作,申请调回原部门,又被驳回。在部门领导逼迫下,她只好辞职。没有正式工作,只好接受非正式雇佣。几次求职失败,她申请了精神残疾人证明,得到就业照顾——在一家超市工作了5年。虽然月薪仅11万元(约6500元人民币),她却极为珍惜。
在采访中作者发现,草柳明子常听不清问题,一旦明白问题是什么,回答极具条理性。可见,她不是能力差、智商低,而是太紧张。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出现了许多“女人当男人用”的黑心企业,大多数贫困女子在职场中遭遇霸凌,使她们很难在职场中充分发挥。
难以挣脱的三重枷锁
日本职业女性背负了三重枷锁,即:文化枷锁、社会枷锁和制度枷锁。
在文化上,日本女性从诞生第一天起,就被定义为家庭成员,而非独立个体。
有的日本议员甚至公开宣称:“女人就是生育机器”。女性被看成“特殊的人”,被加以各种“区别对待”,却被离奇地解释成:这是对她们的“关爱”。不论女性在职场中怎样的成功,都会被无视。日本女性平均工资远低于男性,在男人们看来,纯属天经地义。
在社会上,职场霸凌、家庭暴力被视为“教育”的一部分,得到容忍。
日本女性是非正式雇佣的“重灾区”,一到可以转为正式工的年限,就意味着被解聘。政府试图介入,但对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只能建议和警告,无法处罚。
因经济低迷,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因收入不足,只愿同居,不愿结婚,致使单亲妈妈的数量增加。单亲妈妈承担着职场与育儿的双重压力,日本却未建立匹配的社会支持体系。如果单亲妈妈对孩子缺乏耐心,难免引起社会风暴,成为千夫所指。总之,孩子是日本的未来,单亲妈妈则什么也不是。
男性可以用暴力结束同居关系,女性却很难这么做,一旦被抛弃,她们往往陷入贫困。
在制度上,受“整体有缺陷,却问责个体”的思路影响,长期无法达成解决方案。
贫困女子本是制度困境的结果,但女性们自己不敢主张,男性们又选择性无视,导致问题积重难返。从本书访谈可见,大多数贫困女子因长期加班,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受损,可她们喊累,却遭指责:还是没融入到工作中,应该多反省自己。为什么男员工就不抱怨呢?
男员工不抱怨,因为他们的妻子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两个人打一个人,职场女性怎么可能赢?
“一亿总活跃”
问题的关键,源于日本政治的道德自嗨情结。
日本通过《男女雇佣均等法》的1985年,还出台了《劳动者派遣法》,打开了非正式雇佣的闸门,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大大削减。如果说,前者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愿景,还算“进步”的话,后者则为“同工不同酬”打开方便之门,将前者的努力清零。
在日本,同样是女性,正式工与非正式雇佣之间差异巨大,前者有孕期照顾、丰厚收入和稳定工作,后者则毫无保障,却比正式工承担更多工作。
如此拧巴,体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分裂。
现代国家基于契约形成,但日本政客执着于传统,热衷垄断道德解释权。于是,在虚幻的“男女平等”的泡沫下,贫困女子成为牺牲品。
随着越来越多的贫困女子不愿生育,日本连续出现11年人口负增长。于是,日本又推出“一亿总活跃”的育儿支持计划,在结婚、生育、子女教育等给予补贴。时任官房长官的菅义伟表示:“希望妈妈们以积极生育的意愿为国家做贡献。”在中小学课本中,加入鼓励生育的内容。
制造这类“现代迷信”,无非是想把女性留在“工作—结婚—辞职—生儿—抚养孩子”的、传统的人生路线上,潜台词是:只承认家庭,不承认个体。
于是,超20%的单身女子将继续作为牺牲品,她们的贫困与孤独,因为没被看到,就被当成不存在。道德的天空下,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他都算歧途。这意味着:在走出中世纪之路上,日本还需更多跋涉。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看到问题、重视问题,是回归理性,多想解决方案,少套道德辞令。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日本贫困女子》虽是小书,所指却是大问题。



